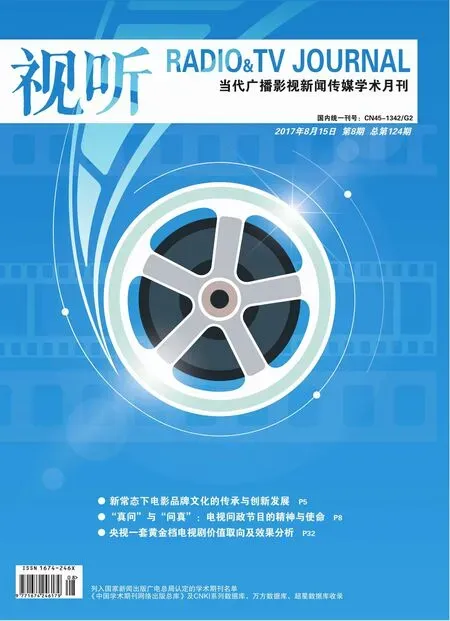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中的倫理失范
□ 姚君
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中的倫理失范
□ 姚君
進入網絡時代,以微信公眾號、客戶端等代表的新媒體平臺替代雜志、報紙成為受眾的首選對象。新媒體平臺的迅猛發展給我們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各種失范問題和亂象,而這些亂象背后都牽涉到了互聯網倫理。本文從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的現狀入手,從內容生產者、受眾及公共領域的角度揭示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倫理失范的原因和影響,最后從技術、商業、社會三方面探討規范策略。
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倫理失范
2017年3月,微信對其平臺下的公眾號“原創”標識進行了規則修改。如果有公眾號抄襲原創文章,并在原創文章推送之前搶發但不標注原創,那么原創文章在推送時,就會出現“溫馨提示”,文章的版權就會被侵占。這一規則體現出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平臺競相爭奪內容生產者。而首發權在傳統媒體時代就已經是記者和媒體搶奪的重點,隨著內容2.0時代的到來,首發權依然是各大新媒體平臺生存的核心。熾熱的平臺競爭,催生與技術聯合下媒體服務的越線,信息泄露、侵犯隱私、版權侵害、信息污染等失范現象到處泛濫。面對此態勢,除了網信辦硬性規則治理之外,我們還應該關切道德倫理的輔助治理功能,以期通過系統化工程,達到標本兼治的目標。
一、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運營的現狀
在泛娛樂化的時代,新媒體平臺的消費主力軍是80后、90后,移動互聯網的強勢覆蓋,消弭了紙端和PC端對消費場景的特定要求。從受眾需求角度來看,閱聽障礙和儀式感逐漸喪失,適合任何場合下自由選擇閱讀的內容為主;從受眾接受習慣來講,時政社會信息逐漸減少,更多地轉向生活服務信息和文娛信息。在此背景下入駐新媒體平臺的內容生產者推送的文章可分為兩種。
(一)內容生產的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以社會突發事件為依托、輸出價值觀、產生情感共鳴的文章。輕悅化閱讀時代的不少文章觀點偏頗,言論情緒化,但其觀點能引發共鳴,注重和用戶之間的互動感和對話感,很容易吸引到一部分黏性粉絲,成為用戶訂閱的動機之一。用戶通過閱讀文章實現日常生活與社會的連接,找到價值歸屬。
第二種是知識增量的文章,分為內容分類型、知識導購型的文章。在內容分類方面,內容生產者多是某一領域的專業人士,圍繞某一關鍵詞展開權威性解答形成了一個知識網絡,以知識科普為目的。用戶根據愛好訂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答疑解惑、追本溯源的效果,同時現成、穩定的知識幫助用戶不必花費時間和腦力;在知識導購型方面,內容生產者多是專業時尚雜志的編輯和網絡買手,圍繞某一關鍵詞整理匯總推薦的物品,替用戶發現好貨,用戶通過訂閱提高對生活商品的甄別能力,這一類文章多與電商平臺合作,為產品進行適當的包裝,替用戶節省時間,替用戶減少選擇成本,收到良好的商業連鎖效益。
(二)內容生產的盈利方式
新媒體平臺通過五花八門的補貼政策網羅優質內容生產者入駐。以微信為例,內容生產者開通公眾號后其收益欄包括流量主、原創補貼、互動收益、結算中心和線下收益。流量主既是閱讀量和訂閱量,文章發布后的點擊流量通過大數據統計能產生衍生收益。原創補貼指的是對入駐該平臺的原創內容生產者的補貼資金。互動收益是以朋友圈分享文章通過朋友關系減少流通成本或者平臺推薦獲得更多的流量獲得收益。結算中心是指每篇文章結尾處附帶的贊賞功能,用戶對于支持的文章可以現金打賞,金額自選。這種“寫作—激勵反饋”機制是內容變現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目的是鼓勵更多的優質原創內容生產。微信平臺對于贊賞不收取費用,也不采取分成模式,所有收入歸內容生產者所得。線下收益多出現在知識增量的文章,用戶可自由選擇購買這一類文章所推薦的物品、出版的書籍,為內容生產者在線下帶來創收。五項收益中以流量主為核心,新媒體平臺根據創作活躍度、用戶認可度、內容質量度、運營健康度這四個維度對內容生產者進行評定,對高評定的賬號內容進行更多推薦,觸及更多的用戶以及更多的廣告分成,最終反映在流量上。
二、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的倫理問題
(一)個人信息泄露
流量是內容生產者生存的關鍵,流量的發生源是數以億計的用戶,因此爭奪更多的用戶成為移動新媒體時代平臺發展的動力。用戶在注冊平臺時必須提供或綁定個人信息,用戶在使用平臺時會留下搜索、訪問記錄。這些數據都被抓取記錄在案,可以提供社會輿情的監測,有利于平臺形成有效的輿情應對方案;還可以間接獲取用戶的興趣點及變化情況,有利于平臺的精準營銷和廣告投放,同時也對投放效果形成有效監測、跟蹤和反饋。用戶提供個人信息是基于對平臺和網絡空間的信任,也是基于社交的需要,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用戶卻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甚至出現個人信息被黑客盜取、買賣、詐騙的事件。
(二)公共領域異化
信息爆炸時代,用戶與媒介之間的連接不再是被動的承受而是主動的選擇,新媒體的技術賦權以及相對寬松的管制環境使傳統意義下的公共領域發生改變。以微信公眾號為例,用戶自主訂閱的公眾號在公共領域的三個維度上——結構、表征和互動——均具備明顯另類公共領域,公眾號為獲得注意力經濟下直接的點擊率“反饋”,弱化文章主旨,突出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取向,持續闡述迎合用戶即刻心理狀態的觀點,建立與主流媒體差異化的話語模式。用戶樂于參與其中,使得新媒體內容生產比傳統媒體更深地受制于眼球效應和轟動效應而難以自拔,這些關注與被關注而形成的另類公共領域正如一個包羅萬象的強連接社群,一切皆有可能成為內容。
(三)信任危機
信任是當下社會非常需要的,不僅僅局限在用戶對一種商品的信任上,還會表現在對一種價值觀的信任。當內容生產者擁有大量的黏性用戶,推送的文章廣為傳播,成為廣告商競相爭奪的新寵,自然就成了當下的信任擔當。理應珍惜這份信任的生產者卻將用戶置身于密集的信息轟炸和放大的驚嘆情緒中,片面追求點擊量,自由選擇內容的呈現方式,甚至對內容進行篡改,從而使信息污染成為了內容生產中普遍失范的現象。這是指信息環境處于失衡的現象、信息存貯無序化現象、負信息現象、信息的異化現象、非生態化現象。①人們被眾多未經證實、不知真假的內容裹挾著,稍微欠缺理性判斷和分析能力就很容易被情緒左右,成為被生產者利用信任來牟利的工具。尤其是在發生有一定爭議性和含混性的事件時,無論是內容生產者還是內容消費者,都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了對固化立場與刻板印象的重復上,事實更加難以追尋,一次次輿情反轉的背后,公眾信任遭到破壞,比如《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所引發的現象級的朋友圈刷屏轉發、爭議、求證,到最后的反轉。此類事件的發生不僅危害著網絡傳播環境,更帶來沖擊主流社會道德的風險。
三、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倫理失范的原因
(一)互聯網倫理邊界模糊
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提到,“從印刷場景到電子場景,新技術肯定會打破電視的一統天下,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再將觀眾清楚地按照傳統的年齡、性別、宗教、階層和教育進行歸類。電子信息資源的增加不會使我們返回到印刷媒介的分隔系統,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可能輕易地接觸任何資源。新的亞群體可能會出現,但是他們的差異、穩定性和可識別性都較低。”互聯網以其強大的時空重組、信息傳播和關系連接能力構建了一個迄今為止最為廣闊的表達、行動空間,改變著傳播環境和社會文化。不同的微信公眾號擁有不同的用戶,地域邊界變得模糊不清,在這種時空邊界模糊的場景中,億萬民眾獲得了空前的表達、交往機會,甚至可以發起虛擬與現實協同的社會行動。社會交往從線下到線上的轉變并沒有一個相應的倫理規范去匹配,從而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互聯網倫理問題。
(二)“信息繭房”的制約
凱斯·桑坦斯在《信息烏托邦》中提到了“信息繭房”的概念,說的是因為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是全方位的,人們會習慣性地將自己包裹在由興趣引導的信息中,從而進入了“回音室”。桑斯坦認為,“信息繭房”以“個人日報”的形式呈現,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信息的劇增,公眾可隨意選擇想關注的話題,可依據喜好定制報紙、雜志,每個人都可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個人日報”。當個人被禁錮在自我建構的信息脈絡中,個人生活必然變得程序化、定式化。②互聯網服務消除了用戶的興趣屏障,興趣的精準化連接帶來注意力的精準化消費。在這樣的語境下,內容生產者獲取注意力和用戶獲取興趣的成本對等,同一種價值觀的輸出帶來用戶對自身價值肯定。然而,長此以往,用戶與社群之外的世界的交流變得更加片面,思維更加狹隘,甚至更加極化。
四、自媒體平臺內容生產的倫理規制策略
(一)技術倫理規制
數字技術時代,內容的輸出帶有高度的靶向性。在內容必須精準地送達特定用戶的行業規則影響下,新媒體平臺執著于利用大數據技術,以消費者不能控制的方式,甚至是不可寬恕的方式進行挖掘和分享。自媒體平臺應設法了解驅使用戶愿意選擇某一內容的動機,對用戶感興趣的內容進行分類、標簽和分發。“信息技術改變了舊的倫理問題出現的語境并且給舊的問題加入了有趣的新花樣。”③但技術終究只是一種手段,需要人去合理利用和倫理規制,需要人去做專業的判斷和指導。
(二)商業倫理規制
互聯網時代,曾經屬于傳統媒體的權利落到了新媒體的運營者手里,新媒體平臺實現了自我賦權的同時理應承擔起保護用戶信息以及凈化網絡環境的作用。首先,內容生產者無限多元化,內容產品無限豐富,平臺應對內容有合理的分類和品控,滿足不同目標用戶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其次,各種利益主體在平臺匯聚,無處不在的軟性廣告和營銷觸犯著用戶的倫理底線,平臺應對內容生產者的資質、內容生產的途徑進行持續監督,與內容生產者共享流量價值、品牌價值、商業價值的同時,為更多的平臺用戶提供高品質的內容,或者是甄別出更多優質的內容,不斷提升用戶體驗。從本質上講,商業倫理即是一種職業道德,具有職業道德的屬性;同時又是一種社會道德,具有社會道德的本質屬性。④
(三)版權保護規制
在當下內容2.0的黃金時代,投身內容創作的人如雨后春筍,而致力于內容耕耘的專注者十分稀缺,行業內出現平臺太多、內容不夠的現狀。平臺爭奪首發權的過程中卻忽視了對原創作者的版權保護。現階段,我國版權保護環境惡劣,網絡版權保護更是舉步維艱,反饋期長、證據缺失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平臺應出臺更多有針對性的資金扶持政策,鼓勵優質和原創內容的同時保護內容生產者的權益。用戶應提升自身媒介素養,自覺規避過度娛樂和無價值的文章,發現規模復制的抄襲作品應立即向平臺舉報。
五、結語
社會化新媒體瓦解了傳統媒體的壟斷優勢,傳播格局的變化使原本大眾媒體所依賴的政府監管不再成為唯一的選擇。內容創作大爆發的時代,倫理這種從社會角度的治理方式更應該引起關注。作為內容生產的消費者,內容生產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精神生活和選擇權。不論是新媒體平臺、內容生產者還是用戶都需要各司其職,提升自身篩選和刪除信息的能力,形成與內容時代相對應的認知秩序。
注釋:
①夏日,琚興.近十年來我國信息污染研究綜述[J].現代情報,2011(8).
②梁鋒.信息繭房[J].新聞前哨,2013(1).
③[美]湯姆·福雷斯特,佩里·莫里森.計算機倫理學:計算機中的警示與倫理困境[M].陸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
④紀良綱.商業倫理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2.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