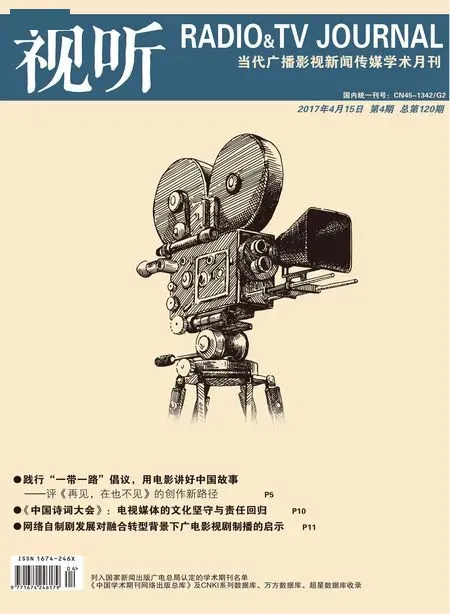臺灣電影發展中的情懷藝術與作者論體現
□周倩
臺灣電影發展中的情懷藝術與作者論體現
□周倩
在臺灣電影中,優美柔情的音樂是對情懷的升華,精巧的剪輯設計是對情懷的鋪墊,精致的場景安排是對情懷的渲染,精美的鏡頭語言是對情懷的呈現。情感可能就是臺灣電影人最終想要闡述的精微主題。在突出情感敘事的基礎上,作者論的體現更顯獨具一格。當然,也正是因為在這種社會不斷商業化的洪流里,那些遵循個人主義,用情懷敘事的電影導演才會更加出類拔萃。
臺灣電影;美學體現;情懷藝術;作者論;商業電影
從工業時代的巔峰滑落后,臺灣的城市工業化激情便開始消退,逐漸開始了后現代社會的轉型。臺灣本土人民似乎對日常生活的品質更加關注,更傾向于享受微小而確實的幸福。這樣一片詩情畫意且又八面玲瓏融匯喧囂文化的土地能夠給予藝術很好的滋養。洛夫、痖弦、余光中、周夢蝶的詩歌,吳濁流、白先勇、陳映真、陳若曦的小說以及侯孝賢、楊德昌等電影導演創作出的具有鮮明臺灣氣息的臺灣電影,都是對臺灣本土滋養藝術發展的例證。
在電影不斷發展的浪潮里,臺灣影像創作者們用清新的敘事方式和精致的鏡頭語言將具有臺灣味道的文學與臺灣市井生活相融合,再通過聲畫呈現的方式在琳瑯滿目的商業電影文化圈中演繹著臺灣情懷。這樣的情懷則是對美學與人性關系的繼續探討,是大眾傳播時代擬態環境下的一份安然,更是眾多熱愛臺灣這片故土的創作者們對于生活的一種反思與記錄。
一、臺灣電影的美學體現:情懷藝術
柏拉圖在早期探究美學時認為“美是難的”。隨著美學在各類藝術中的不斷深刻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通過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在目的的引導下,充分調動自己的本質力量加工對象。”①在這種美學與人性關系相統一的大背景下,作為第七藝術,電影憑借聲畫影像打破時空生命線的特點,開始展現藝術情懷。用影像記錄時代及社會的發展,在電影美學里映射政治、融合地域、聯系經濟、表現文化。
對于臺灣電影的美學概括,可以用“情懷美學”來概括。“情懷”原本是表達感情的抽象名詞,在這用來形容以臺灣為圓心區域化的電影美學體現和表現電影風格的手段。臺灣電影導演擅長用情懷來吸引觀眾,臺灣電影也容易用情懷制造噱頭。但需要說明的是,情懷不是只有臺灣電影才具有的特殊屬性,它鮮明地活躍在所有電影中,只是談及情懷,臺灣電影更別具一格。
2000年開始,臺灣的新銳導演就更傾向于根據自己的成長經歷敘述青春主題,如《不能說的秘密》《海角七號》《星空》等臺灣青春電影都屢屢創下票房新高,《藍色大門》更是堪稱近年來臺灣青春電影中的標桿。臺灣導演侯孝賢在接受采訪時感慨:“電影的形式早已用盡,最重要的還是內容。”如侯孝賢在影片中游刃有余的風格化敘事:最本土的,最沉痛的,最植根時代的,最照亮都市的,最能講述鄉愁悲喜的,最黑色的,最荒誕的,最能體現精神困境的……這些看似不和諧的元素實際上都精彩奪目,多維度的表情達意都能吸引觀眾接近、迷戀與討論。當然,臺灣多數電影工作者均寄厚望于這股情懷的“復興浪潮”,包括觀眾在內的電影藝術熱愛者們都深切地希望臺灣電影的情懷不只是曇花一現,而是讓臺灣電影產業能夠就此站穩腳步并持續發展的開端。
平淡的生活細節在不同導演不同風格的演繹下變得有滋有味,令觀眾意猶未盡。情懷像是一種符號,在臺灣電影中根深蒂固,耐人尋味。白居易所說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臺灣電影中有所體現:優美柔情的音樂是對情懷的升華,精巧的剪輯設計是對情懷的鋪墊,精致的場景安排是對情懷的渲染,精美的鏡頭語言是對情懷的呈現。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臺灣電影人最終想要闡述的精微主題,它可能是愛情,或許是親情,也許還是友情,總之,終究難逃于“情”。
二、臺灣電影的新浪潮:從作者論②開始的新格局
對臺灣電影發展種種跡象進行觀察,能夠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已經站在了它獨具特色的轉折點上。臺灣電影往往著重于強調導演的風格,注重講述臺灣歷史,并崇尚以電影情懷作為宣傳藍本。一方面,這種特色讓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朱延平等導演取得一定成就。但另一方面,因為此類型藝術電影專注表情達意,致使娛樂性較差,商業價值還有待估量。盡管大部分觀眾偏愛所謂的個性化與樸素化的表情達意,但能令個體著迷的部分,仍然是在從其他類型的電影中所獲取的觀影經驗、視覺沖擊以及對影像的理解習慣和成長背景。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在他的導演手記里這樣寫道:“導演不但是用來表達技巧,而且還是反映人生的工具。”
第七藝術自然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可以是一種彰顯創作者個性的表達形式,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但在文化經濟發展的商業怪圈中,電影藝術迫于生存壓力,越來越趨向于成為商業表達的附屬品。它受生產與消費定律的支配,有了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活躍在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里。在藝術與經濟難以并駕齊驅時,臺灣電影就開始了商業化發展的新革命。
臺灣電影的真正發展始于1982年。由臺灣導演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和張毅聯合導演的影片《光陰的故事》在敘事方法、藝術技巧上打破了傳統臺灣電影的舊風格,成為臺灣電影新浪潮的先聲。在此之后,愈來愈強烈的臺灣電影風格開始進入觀眾的視野,沖擊著受眾的情感體驗。就像萬仁、曾狀祥、侯孝賢合拍的《兒子的大玩偶》、陳坤厚的《小畢的故事》、侯孝賢的《風柜來的人》、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等臺灣電影均改編自臺灣鄉土文學,強烈的現實感、鮮明的社會問題、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清新的美學風格都令臺灣電影烙上了獨特的風格標簽,自成體系。電影《賽德克巴萊》號稱臺灣版《勇敢的心》,講述了日軍占領臺灣后,兩個族群在臺灣山區爆發沖突進而交戰的故事。雖然該影片在大陸受到了一定的爭議,但從中也能看出臺灣的精神所在,臺灣人的情懷所致。臺灣導演張作驥在《黑暗之光》里講述了平凡女孩在逆境的緊逼下,用幻想來稀釋生活的悲哀。他用獨特的超現實主義手法,賦予電影優雅的哀傷與浪漫。毋庸置疑,以上電影的產生都與當時臺灣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影片敘事與生活事件的高度契合使得臺灣電影的敘事情懷更加深刻和哲理化。可見,臺灣導演的先覺意識以及他們對臺灣文化的把控,對促進臺灣電影體系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結語
達德利·安德魯曾用傷感的筆觸寫道:“導演即作者,社會和文化的日益世俗化、商業化、平庸化,解構了電影導演對于藝術的標志認識。”當然,也正是因為在這種社會不斷商業化的洪流里,那些遵循個人主義,用情懷敘事的電影導演才會更加出類拔萃。臺灣電影的新浪潮從作者論開始,呈現出新的格局。如彼得·沃倫在《電影的符號與意義》中強調的那樣:“作者論并不僅限于宣稱導演為一部影片的主要作者,它還意味著進行辨析的工作,要發掘那些全然被忽視了的作者。”由此可知,在電影藝術與商業經濟密不可分的當下,“電影作者”和“作者電影”雖成為一種“商業”廣告和“藝術”的招牌,但好在臺灣電影在演變過程中沒有遺棄它,沒有放棄用樸實的情感講述影片創作者們對于臺灣這片故土的熱愛。由此可見,臺灣電影的新浪潮也不失為對故土有情思的創作者們遵從本心的本意創作。
注釋:
①[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楊遠嬰.電影概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 422.
(作者單位:廈門理工學院數字創意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