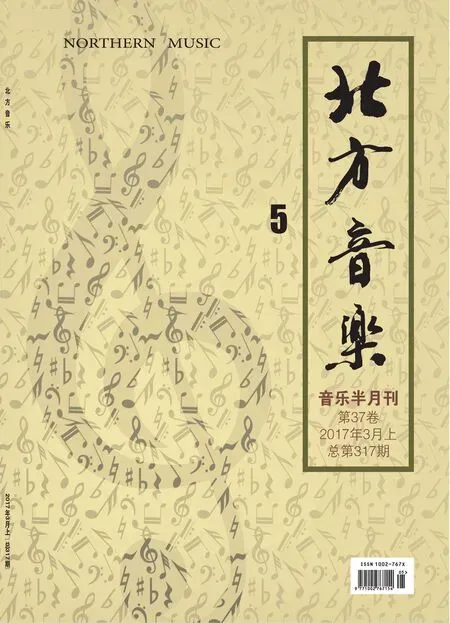門德爾松《春之歌》(OP.62之6)的結構特點
藍潔瑩
(廣東海洋大學寸金學院,廣東 湛江 524094)
門德爾松《春之歌》(OP.62之6)的結構特點
藍潔瑩
(廣東海洋大學寸金學院,廣東 湛江 524094)
門德爾松是浪漫主義音樂時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譽為“抒情風景畫大師”。一生中創作了大量各種體裁的作品,尤其是他獨創的“無詞歌”鋼琴曲集,對于標題音樂和鋼琴作品的結構發展都有著巨大的啟示價值。其中,作品《春之歌》(OP.62之6)以其淳樸、動聽的旋律、簡潔的音樂語言與嚴謹的結構為人們熟知。本文以《春之歌》為例,探究作品的結構特點。
門德爾松;春之歌;結構特點
雅科布·路德維希·費利克斯·門德爾松·巴托爾迪(德文: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是浪漫主義時期德國著名的作曲家、指揮家。作品集《無詞歌》是其鋼琴創作的代表作之一,共49首,結構短小、精致,旋律如歌唱般優美而流暢。其中,《春之歌》(OP.62之6)以其別致而典雅的旋律最為人們所熟知,作品描繪的是一幅春意盎然、生機勃勃的畫卷,音樂淳樸且富有詩意,充滿著積極向上的情感,流淌出對生命無限的熱愛。
從主題旋律上的分析,不難發現,《春之歌》的結構為再現單三部曲式(A-B-A1),但是在門德爾松的筆下被賦予更深刻的內涵(此點后議)。樂曲一開始就在高聲部呈現出優美而富于歌唱性的主題,分解和弦式的琶音音型如同潺潺流水由此至終貫穿在中間的聲部,低聲部以八度的音程呈線條型的低音與高聲部旋律相互呼應。A段(1——15小節)由兩個同首異尾的平行樂句構成平行樂段,樂句結構為8+7,非方整性結構。主題句旋律以音階式的級進與小跨度的跳進交替組合而成,樂曲開端的第2小節就由半音階的推進出現樂段的第一次旋律高點,然后結合大附點的節奏型迂回下行,節奏上富于彈性和推動力,猶如春天萬物復蘇,生機勃勃的景象。在和聲調性上,主調為A大調,旋律在第15小節由ii—V7—I作原調的終止,為收攏性樂段。B段(16——35小節)由兩個對比樂句組成的對比樂段,樂句結構為12+8,非方整性結構。B段的旋律是A段主題材料的引申發展,在原本A段上行的主題材料變為下行,在情緒上,表現出與A段截然不同的風格,如果說,A段描繪的是春天萬物生機勃勃的激情,那么B段則描繪的是春天的柔情與委婉。B段在27小節轉到了主調的屬調E大調上,屬調所帶來的不穩定與主調形成鮮明的對比。B段在35小節完滿終止后是一個14小節的連接,前4小節是對B段作一個補充終止,從39小節開始,通過一系列的轉調模進引出再現部分,調性布局為:#f——A——b——D——A,相比較于A、B段,在和聲調性上,此處的連接為作品豐富了色彩上的變化。再現段A1為動力再現,A1段的第二樂句通過截取B段材料變化發展實現了A1段的擴充,A、B段的音樂材料在再現段A1段得到了統一。全曲完整的曲式結構圖如下:
表面上看,《春之歌》的結構為再現單三部曲式,但實際上,作曲家對該部作品的結構設計遠沒有那么簡單,而是隱藏了更深刻的結構邏輯。首先,作為單三部的展開段B段一開始的調性仍然為

原調A大調,并沒有與A段產生調性上的對比,這并不是單三部曲式的典型;其次,展開段B段的35小節在E大調上作該樂段的完滿終止,這種封閉式的展開段在再現單三部曲式中也并非典型;再者,仔細觀察發現,B段的c句是E大調,而A1段再現中的c1句回到了主調A大調,這恰恰體現的是曲式結構中的奏鳴原則——調性附和。因此,《春之歌》的結構上還體現了無展開部奏鳴曲式的特點:
從圖中可以看到,呈示部以雙主題形式呈示,調性分別是A大調及其屬調E大調,兩個主題的調性在呈示部中對置而在再現部中得到統一,體現出奏鳴曲式的兩大特征。全曲只用一種音樂材料發展而成,簡潔而集中,呈示部主、副部的兩個主題的矛盾對比并不強烈,結構較為規整,缺少繼續展開的動力,因而省略了展開部,直接再現,使樂曲由始至終連成一體。這部短小的鋼琴作品,音樂語言清新典雅,和聲簡練,結構嚴謹,體現了再現原則與奏鳴原則相結合的組合,以奏鳴曲式的思維原則作為音樂發展的邏輯,同時保留了再現三部曲式大致的結構,門德爾松將兩種曲式結構融合在一起的創作,使《春之歌》(OP.62之6)這部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更為豐富,更具內涵。

[1]高佳佳.門德爾松《無言歌》曲式結構研究[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4(04).
[2]高佳佳.門德爾松-無詞歌分析與演奏[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7.
[3]呂威霖.“小身材蘊含大智慧”——解析鋼琴小品門德爾松《春之歌》之藝術特征[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院學報),2015(03).
J61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