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意義闡釋的有效性
李臣
(江蘇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江蘇 徐州 221116)
作品意義闡釋的有效性
李臣
(江蘇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江蘇 徐州 221116)
一千個(gè)讀者并非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讀者對(duì)作品的解讀也并不是都是有效的。對(duì)作品意義的有效性解讀必須限定在一定的邊界之內(nèi),不能對(duì)作品意義進(jìn)行無(wú)限闡釋,這樣就需要對(duì)作品意義進(jìn)行有效闡釋。有效闡釋作品意義需要遵從連貫性標(biāo)準(zhǔn)、需要錨定作品主要意圖,對(duì)作品意義的有效闡釋不意味著讀者之死,也需要實(shí)現(xiàn)讀者與作品、讀者與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
作品意義;闡釋;有效性
“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一千個(gè)讀者是否就真的就會(huì)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文學(xué)的作品意義具有延宕性,是不是作品意義具有延宕性,對(duì)作品就可以進(jìn)行無(wú)限闡釋?是不是所有對(duì)作品的闡釋都是有效、合理的?顯而易見(jiàn),并非所有對(duì)作品的闡釋都是有效的。既然并非所有對(duì)作品的闡釋都是有效的,那么,如何對(duì)作品進(jìn)行有效闡釋。
1 一千個(gè)哈姆雷特的出現(xiàn):闡釋的多元性
一千個(gè)讀者是否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在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過(guò)程中是否所有的哈姆雷特都是合理的、有效的?這個(gè)問(wèn)題也是以闡釋文本意義作為主要目標(biāo)的闡釋學(xué)批評(píng)所遇到的一個(gè)問(wèn)題,這個(gè)問(wèn)題既是一個(gè)理論難題,也是一個(gè)實(shí)踐難題。或者“借用美國(guó)文藝?yán)碚摷液障5谋扔鳎簿褪请[藏在文本深處的具有不透明性和不確定性的意義的‘灰姑娘’,需要通過(guò)讀者、批評(píng)者的意義闡釋也就是需要穿上一雙合適的和漂亮的‘水晶鞋’把自己彰顯出來(lái)。”[1]在判斷一千個(gè)哈姆雷特是否有效之前,需要明確哈姆雷特出現(xiàn)的位置。
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出現(xiàn)的位置就是讀者、批評(píng)者對(duì)文本意義進(jìn)行多元闡釋的地方。作品意義不是一個(gè)有形的可裸露在外的實(shí)體,作品是一種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形式,就類似于音樂(lè)符號(hào),每個(gè)音符所代表的內(nèi)容都需要得到合理、有效的解釋。對(duì)于文本意義的闡釋,需要明確文本的主要意圖,從一定意義上說(shuō),作品的主要意圖即為作者意圖,對(duì)作品本身意義的闡釋,主要分析這些作品明確表達(dá)出來(lái)的意義或者是作品隱含地所表達(dá)出來(lái)的意義,因而作者意圖可以分為作者的明確意與作者的隱含意。
1.1 對(duì)作品明確義的闡釋
作者的明確意義,顧名思義,就是作者明確在作品中流于字面的,易于捕捉的意圖,胡塞爾把見(jiàn)之于字面的意圖稱之為“內(nèi)容”。在這里,“內(nèi)容”不僅僅指的是“理性內(nèi)容”,也包含了對(duì)這種意圖的多方面,如認(rèn)識(shí)的、情感的、語(yǔ)音的、寫(xiě)作的、甚至是視覺(jué)方面的,這些方面都可以通過(guò)語(yǔ)言手段傳達(dá)出來(lái)。作品中作者的明確意義易于把握,在通常情況下不難味大多數(shù)讀者所接受,對(duì)作者明確意義的闡釋一般不會(huì)出現(xiàn)分歧。
1.2 對(duì)作品隱含義的闡釋
作品的隱含含義也可以視為作者的“意圖”,這些隱含意義常常隱藏在作品之中,它們以一種層次的形式出現(xiàn),這種層次就是一個(gè)典型的期待和可能性的系統(tǒng)。這種層次源自于明確意識(shí)中的明確的意義,是對(duì)整體的不明確的把握,也是上下文的一個(gè)重要方面。作者不能清楚地意識(shí)到這一層次中國(guó)的多樣的有代表性的附屬意義,“要想斷定作者當(dāng)時(shí)所思考著的是他的意思的哪個(gè)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值得稱道的事,但至關(guān)重要的是判明作為作者總體‘意圖’的這一‘層次’,因?yàn)橹挥薪柚谶@一層次或者對(duì)總體的把握,闡釋者才能把那些屬于作品意義的重要而正確的組成部分與那些不屬于作品意義的部分區(qū)分開(kāi)來(lái)。”[2]423因此,相較于易于被讀者接受的作者明確義,作品的隱含意義往往不容易為讀者接受,而對(duì)作品隱含意義的闡釋“問(wèn)題往往出在判定不明顯的或‘沒(méi)有明說(shuō)’的含義就不那么輕而易舉了。這種含義可以是我的本義的一部分,也可能不屬于本義。這正是闡釋者往往需要指導(dǎo)原則的地方。”[2]421因此,此時(shí)對(duì)作品隱含義的闡釋就可能是多元的,若在一定指導(dǎo)原則的指導(dǎo)下進(jìn)行的闡釋就會(huì)是合理的,有效的,超過(guò)一定的邊界的闡釋就可能會(huì)造成過(guò)度闡釋、誤讀或者強(qiáng)制闡釋。
1.3 對(duì)作品意義的當(dāng)下性闡釋
作品的意義具有生成性,闡釋者不可能能在一時(shí)一地完全窮盡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因此,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賦予作品意義新的內(nèi)涵,對(duì)作品意義的當(dāng)下性闡釋,也是出現(xiàn)眾多哈姆雷特的原因之一,亦即出現(xiàn)闡釋的多元化。形而上學(xué)的一個(gè)教條認(rèn)為“作品也是一個(gè)有生命的實(shí)體,被現(xiàn)代理論家用來(lái)表達(dá)這樣一種設(shè)想,即作品意義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而起變化。”[3]雖然這個(gè)教條不能給予全部肯定,它忽視對(duì)作品的批評(píng)存在一種永久的有效性的闡釋,但卻指出了作品目前所指的重要性。如對(duì)《紅樓夢(mèng)》的闡釋,從對(duì)紅樓夢(mèng)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分析,延伸到對(duì)紅夢(mèng)次要人物的分析,從對(duì)紅樓夢(mèng)純文學(xué)的闡釋,到用生態(tài)美學(xué)、建筑學(xué)、中醫(yī)學(xué)等多角度、多方位闡釋《紅樓夢(mèng)》。這種理論認(rèn)為,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不在作品意義本身,而在于不同時(shí)代的變化著的讀者。這與韋勒克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當(dāng)讀者、批評(píng)家和藝術(shù)界的同僚們談時(shí)”,作品的意義也是各不相同的。[2]414弗瑞濟(jì)卻認(rèn)為“作品的意義依然如故,只是作品的所指轉(zhuǎn)移了。也可以說(shuō)特定時(shí)代的讀者容易誤解特定的作品。”如果讓讀者的世界觀來(lái)評(píng)定作品的意義,那么,作品不僅有了變化莫測(cè)的意義,而且很有可能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種意義。對(duì)作品意義的當(dāng)下性闡釋,有可能會(huì)產(chǎn)生誤讀,但對(duì)作品意義的解讀需要包容歧義的存在。
對(duì)文本的有效闡釋要考慮到闡釋的邊界,這個(gè)邊界是具體的,也是歷史的。批評(píng)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文本有自己的自在意蘊(yùn),也有闡釋這生成的意義,應(yīng)該追求二者的有機(jī)結(jié)合,批評(píng)家需要對(duì)闡釋進(jìn)行創(chuàng)新。闡釋要對(duì)邊界內(nèi)的意義進(jìn)行闡釋。
2 有效的哈姆雷特:文本意義闡釋有效性的標(biāo)準(zhǔn)
對(duì)同一作品意義的解讀往往會(huì)有不同的闡釋,那么,什么樣的闡釋才是有效的?對(duì)作品意義有效闡釋的標(biāo)準(zhǔn)什么?隨著西方結(jié)構(gòu)主義思潮的出現(xiàn),闡釋的不確定性被張揚(yáng)、夸大,闡釋的無(wú)限可能性帶來(lái)了意義闡釋的混亂和危機(jī)。這就需要找出防止作品意義被無(wú)限性闡釋的標(biāo)準(zhǔn)。
2.1 連貫性標(biāo)準(zhǔn)
作品的含義需要通過(guò)作品的上下文來(lái)決定,讀者推延作品的意義也需要在作品上下文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因此有效的闡釋作品意義必須要符合文本的連貫性,連貫性是闡釋作品的最明顯、最普遍的標(biāo)準(zhǔn)。以連貫性作為有效性闡釋的標(biāo)準(zhǔn)不僅要關(guān)注作品內(nèi)部的邏輯連貫性,又要關(guān)注相關(guān)文本闡釋之間的連貫性。艾柯也曾指出推斷作品意圖“唯一的方法是將其驗(yàn)之于本文的內(nèi)在連貫性整體。對(duì)一個(gè)本文某一部分的闡釋如果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證實(shí)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則應(yīng)舍棄”[3]78。
一、依靠作品內(nèi)部的連貫性。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讀者要以文本為依托,不能脫離文本去尋找文本之外的神秘意義,文本本身具有自律性和確定性、有作品意義不依賴讀者為轉(zhuǎn)移的自我規(guī)定性和內(nèi)在邏輯性。“本文不只是一個(gè)用以判斷詮釋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詮釋在論證自己合法性的過(guò)程中,逐漸建立起來(lái)的一個(gè)客體”。[3]78文本的內(nèi)在邏輯控制著對(duì)文本的解讀。二、依靠相關(guān)文本之間的連貫性。讀者依靠相關(guān)文本之間的連貫性闡釋作品意義就要把作品的文化歷史語(yǔ)境作為參照,作品與作品之間并不是毫無(wú)聯(lián)系的,每個(g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會(huì)受到歷史文化語(yǔ)境的影響。一定的文化歷史語(yǔ)境會(huì)產(chǎn)生一批符合時(shí)代氣息的作品,不僅作者的創(chuàng)造力會(huì)受到他所處的社會(huì)話語(yǔ)體系的影響,作者的意圖也會(huì)受到文本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外在聯(lián)系的制約。所以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要以作品的連貫性為基本準(zhǔn)則。
2.2 錨定作品主要意圖
對(duì)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多元闡釋,需在承認(rèn)該作品作者的本來(lái)意圖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尊重文本,尊重作者,這就提出了另一條對(duì)作品意義有效闡釋的標(biāo)準(zhǔn),即闡釋作品意義需要以錨定作品主要意圖為標(biāo)準(zhǔn)。讀者對(duì)文本進(jìn)行有效闡釋,需要錨定作品的主要意圖,與主要意圖的相關(guān)闡釋的可以視為合理闡釋,否則,就是無(wú)效闡釋。
“作品原義,作為‘意欲對(duì)象’是永恒不變的,也就是說(shuō),不同的‘意欲活動(dòng)’可以對(duì)它進(jìn)行再造,而在再造過(guò)程中,它都保持其自身的統(tǒng)一性。作品原義是作者的‘意欲對(duì)象’可供共同領(lǐng)會(huì)的“內(nèi)容”。既然這種意義是永恒不變而又有賴于人們的理解,那么它就可以通過(guò)不同主體的精神活動(dòng)加以再造。”[2]421讀者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過(guò)程中可以依定自己的主體精神活動(dòng),在尊重作者的原義,在遵照作品主要意圖的基礎(chǔ)上對(duì)作品意義進(jìn)行有效闡釋。有效的解讀作品必然不會(huì)脫離文章本身,作品的主要意圖作為作品的意義的本源,也不會(huì)對(duì)讀者的自由發(fā)揮形成阻礙。但是錨定作品主要意圖,圍繞主要意圖進(jìn)行相關(guān)闡釋的具體界限確實(shí)不容易界定的,在這里暫且存而不論。
3 闡釋的有效性是否意味著讀者之死
“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并非所有的哈姆雷特都是有效的,作品的內(nèi)在含義是由作品本身規(guī)定的,不受讀者意圖的影響,但對(duì)作品意義的有效闡釋并不意味著讀者之死。文本是開(kāi)放性的,文本的在接受美學(xué)看來(lái),對(duì)作品進(jìn)行闡釋,讀者需要與作品進(jìn)行對(duì)話,讀者與讀者進(jìn)行對(duì)話,這樣可能實(shí)現(xiàn)作品的可寫(xiě)性。
3.1 讀者與作品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將文學(xué)分為四個(gè)要素:世界、作家、文本、讀者,有體驗(yàn)、創(chuàng)作、接受三個(gè)過(guò)程。雖然在四要素中,文本占有主要地位,但讀者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況且闡釋學(xué)最直接研究的就是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在對(duì)作品進(jìn)行有效闡釋的同時(shí)就更加不能宣布讀者之死。隨著文學(xué)研究中心的轉(zhuǎn)移,讀者的作用更被放在了一個(gè)更高的階層。文學(xué)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都有不確定性,字里行間留有空白,這些空白為讀者留下了闡釋空間。“讀者出于個(gè)人的體驗(yàn)和期待視野完全有可能去通過(guò)自己的閱讀填補(bǔ)這些空白,從而建構(gòu)出新的意義,最終使得‘文本’成為‘作品’。”[4]伊瑟爾也注重讀者的作用,他認(rèn)為如果沒(méi)有讀者在閱讀過(guò)程中的這種能動(dòng)的接受作用,一部作品的意義是不完整的。作品的意義需要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對(duì)話才能實(shí)現(xiàn),讀者閱讀和接受了文本,還對(duì)文本進(jìn)行二次創(chuàng)作。文本闡釋活動(dòng)不僅是認(rèn)知活動(dòng),還是讀者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通過(guò)讀者與作品之間的對(duì)話,讀者可以建構(gòu)出新的意義,使文本成為作品。讀者與作品的對(duì)話是一種面對(duì)面的交流,作品不是作為中介而存在而是參與對(duì)話的主體。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會(huì)吸引眾多讀者進(jìn)行闡釋,作品意義處于不斷增值之中。優(yōu)秀的作品能夠影響讀者的思維,可以拓寬讀者的視野。在這種對(duì)話視野中,作品的意義已經(jīng)不再是原來(lái)的文本世界,也不是讀者任意闡發(fā)的世界,而是文本世界與讀者世界的融合。
3.2 讀者與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
當(dāng)代社會(huì),批評(píng)比較發(fā)達(dá),文本作為一個(gè)開(kāi)放的空間,它的意義永遠(yuǎn)不可能被窮盡,闡釋者會(huì)對(duì)文本有不同的理解,這些不同的理解促使文本意義不斷創(chuàng)生。文學(xué)批評(píng)影響闡釋者對(duì)作品的解讀。在闡釋活動(dòng)中,闡釋者屬于讀者群體的一份子,解讀作品需要讀者與作者進(jìn)行對(duì)話、讀者與文本進(jìn)行對(duì)話,也需要讀者與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闡釋者在于作品對(duì)話的過(guò)程中,他對(duì)作品的理解、闡釋或多或少地收到了前輩讀者對(duì)該作品闡釋的影響,尤其是具有社會(huì)影響力的批評(píng)家對(duì)作品的解讀影響力更大,這也就形成了讀者與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讀者與讀者之間對(duì)話并不是后起的,孔子在《論語(yǔ)》中就曾提及“詩(shī)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shī)可以群”就是指對(duì)作品的解讀需要讀者與讀者之間進(jìn)行交流。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往往會(huì)產(chǎn)生共鳴、分歧,會(huì)出現(xiàn)理解的差異,這些分歧、差異是作品意義生成的關(guān)鍵點(diǎn),能夠是作品意義處在不斷的生成過(guò)程中,不斷建構(gòu)作品意義,這樣可以增進(jìn)讀者對(duì)作品的理解,這樣就在無(wú)形中推動(dòng)了文學(xué)作品的傳播。闡釋者作為一類特殊的“讀者”,只有闡釋者的解讀被納入讀者之間的對(duì)話中,闡釋的內(nèi)容才能夠最大程度地獲得讀者的認(rèn)可。由此看來(lái),讀者之間進(jìn)行對(duì)話是實(shí)現(xiàn)有效闡釋的重要途徑。
作品是由語(yǔ)言編織起來(lái)的,對(duì)每個(gè)作品意義的闡釋,并非就是“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對(duì)作品意義的闡釋可以有很多種,但并非所有的闡釋都是有效的,作品意義的有效闡釋?xiě)?yīng)以作品的中心意或者是作者所要表達(dá)的中心意圖為中心,錨定作者意圖去探尋作品的延宕意義,而意義延宕的解讀并不意味著對(duì)意義進(jìn)行無(wú)限延伸。
[1]劉思謙.意義闡釋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問(wèn)題[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41(6):1.
[2]胡經(jīng),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jì)文論選(第三卷)[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9.
[3]艾柯.詮釋與過(guò)度詮釋[M].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1997.
[4]王寧.闡釋的有效性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倫理學(xué)[J].求是學(xué)刊,2015,(9):121.
責(zé)任編輯:周哲良
I06
A
1672-2094(2017)02-0046-03
2017-02-25
李 臣(1992-),女,江蘇徐州人,江蘇師范大學(xué)文藝學(xué)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guó)美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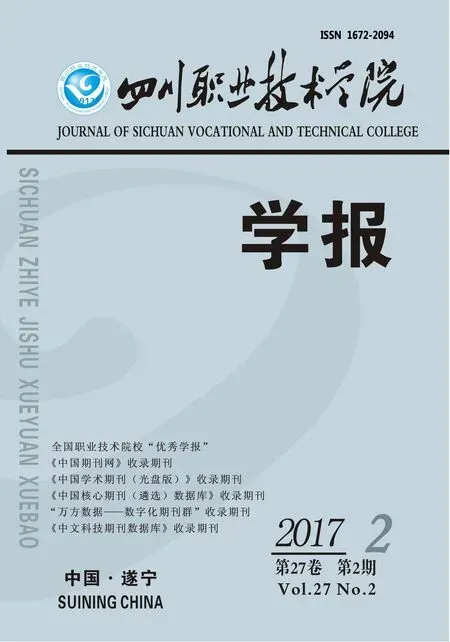 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2期
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2期
- 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于CSS 盒模型的浮動(dòng)布局
- 偶聯(lián)劑對(duì)玻璃纖維增強(qiáng)環(huán)氧樹(shù)脂復(fù)合材料力學(xué)性能的影響
- 《水污染控制技術(shù)實(shí)訓(xùn)》的實(shí)施與考評(píng)
- “以學(xué)生為中心”理念下高職微課教學(xué)設(shè)計(jì)研究
——以《網(wǎng)絡(luò)營(yíng)銷基礎(chǔ)》課程為例 - 在《畫(huà)法幾何》課程教學(xué)中運(yùn)用MOOC的效果評(píng)價(jià)分析
- 高職建筑設(shè)備類專業(yè)課程項(xiàng)目化教學(xué)整體設(shè)計(jì)探究
——以《建筑給水排水工程》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