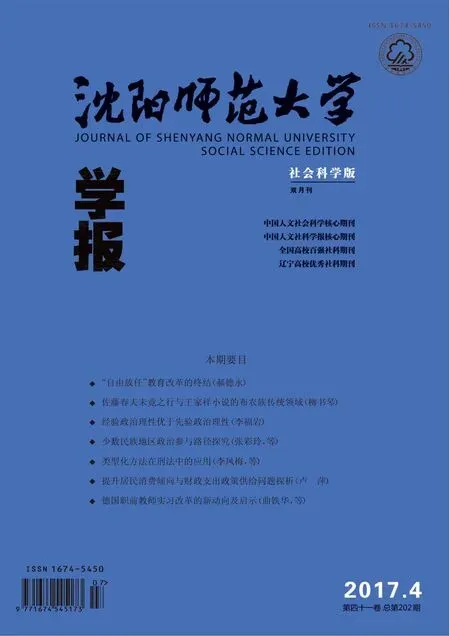整合晚清民國文學(xué):需要關(guān)注臺灣的學(xué)科化臺灣文學(xué)研究
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xué)·臺灣文學(xué)研究專題·
整合晚清民國文學(xué):需要關(guān)注臺灣的學(xué)科化臺灣文學(xué)研究
主持人語:這一專題中的兩篇論文來自臺灣,是臺灣文學(xué)學(xué)科專業(yè)人員的日據(jù)時期臺灣及臺灣文學(xué)研究的悉心之作。
20世紀(jì)20年代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臺灣殖民地之旅,成就了他而后十余年的隨筆《霧社》等臺灣題材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對日本本土作家和在臺日本人作家的臺灣書寫產(chǎn)生重大影響,也引發(fā)對臺灣殖民地觀光的興趣。其中的殖民主義批判元素到20世紀(jì)70年代開始引起注意。臺灣新一代學(xué)者有深入的批判性辯證研究,如邱雅芳的《殖民地的隱喻:以佐藤春夫的臺灣旅行書寫為中心》(2006年)、朱惠足的《黃種人帝國的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臺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xiàn)》(2012年)等。收入本專題的柳書琴的新論《佐藤春夫未竟之行與王家祥小說的布農(nóng)族傳統(tǒng)領(lǐng)域》提出,由于受氣候、環(huán)境等條件的制約,佐藤的臺灣蕃地之旅,只完成了日本人類學(xué)家森丑之助為他設(shè)計的南北兩翼考察路線中的北翼部分,因而與主要分布在南翼路線上的鄒族和布農(nóng)族失之交臂。當(dāng)代作家王家祥的臺灣歷史奇幻小說系列之一《關(guān)于拉馬達(dá)仙仙與拉荷阿雷》,回應(yīng)了帝國時期的佐藤文本的缺失,豐富了臺灣的原住民民族史。柳書琴文章的后殖民視角最富于啟發(fā)性,有可能引發(fā)眾說紛紜的后續(xù)討論,其指向之一或許是認(rèn)知有可能截然相反的殖民文學(xué)場研究中的殖民命名方法問題。楊智景的《日據(jù)時期新聞小說〈金色夜叉〉在臺灣的傳播與接受》,考索這部日本暢銷書的生產(chǎn)史、文本屬性,以及它經(jīng)由小說、演劇、歌謠、電影等多種體裁形式進(jìn)入臺灣的傳播史,并引進(jìn)朝鮮殖民地作家趙重桓的《金色夜叉》朝鮮語改寫本《長恨夢》(1913年),與臺灣徐坤泉的深受《金色夜叉》影響的《可愛的仇人》作橫向比較,展現(xiàn)人們面對金錢與愛情、物質(zhì)與心靈、背棄與誠信抉擇時的內(nèi)在矛盾。受限于篇幅,文章無法一一囊括《金色夜叉》與日據(jù)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精神層面、大眾娛樂層面間互動的諸多重要面向等。不過瑕不掩瑜,兩篇文章拓展了臺灣日據(jù)時期殖民主義文學(xué)在殖民地傳播史的研究,對于大陸學(xué)界全面、客觀認(rèn)識臺灣的臺灣文學(xué)研究狀況,以及反思大陸的“滿洲國”、內(nèi)地淪陷區(qū)文學(xué)研究現(xiàn)狀,也大有裨益。
文學(xué)史書寫是兩岸學(xué)界近年來持續(xù)關(guān)注的話題之一。兩岸都有文學(xué)史焦慮,但焦慮的方向相反。大陸的焦慮是空泛雷同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出版的太多。臺灣的臺灣通史類臺灣文學(xué)史鳳毛麟角,且存在歧義。不過,在中國淪陷區(qū)區(qū)域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由于臺灣的臺灣文學(xué)研究在20世紀(jì)90年代進(jìn)入學(xué)科學(xué)院化體制之內(nèi),臺灣的臺灣日據(jù)時期文學(xué)研究有了長足發(fā)展,遠(yuǎn)比大陸的“滿洲國”、內(nèi)地淪陷區(qū)文學(xué)研究深入、全面。臺灣殖民期文學(xué)史,同大陸的日本占領(lǐng)區(qū)一樣,不是簡單化的附逆/反日二元對立,而是充滿了重層多維的跨域“模糊的地帶”,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這筆在時間上大體與中國晚清、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相重疊的精神資源遺產(chǎn),不是日本的文化殖民留痕,而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充分注意到這一點,晚清民國文學(xué)史中的臺灣敘述,就會有意無意放大與大陸緊密相連的臺灣漢語新文學(xué),忽略現(xiàn)代臺灣人的詩詞創(chuàng)作、方言創(chuàng)作、日文創(chuàng)作及原住民文學(xué)。我曾在《臺灣文學(xué)研究及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影響》(《文藝爭鳴》2012年9期)一文中略有鋪陳,這里不贅述。從本期發(fā)表兩位臺灣學(xué)者的出色文章中,我們也可略見一斑。因而我愿意在這里加以推薦。
特約主持人:張 泉(北京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