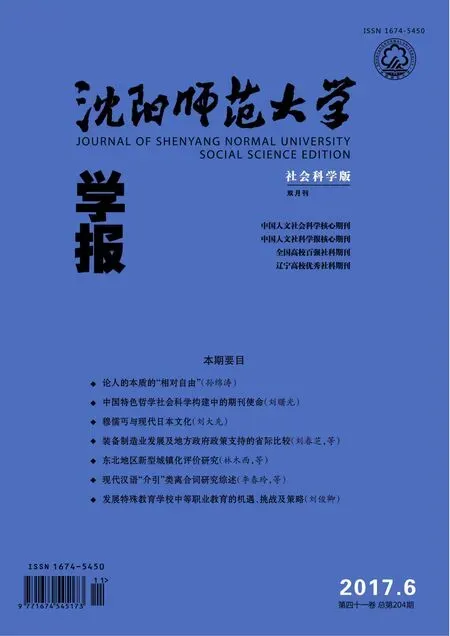大學學報的定位、功能及其實現
邢志人
大學學報的定位、功能及其實現
邢志人*
在中國,大學學報自其誕生之時起,就是高校展示科研成果的窗口、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譬如,被公認為中國最早的大學學報——1906年創刊的《東吳月報》(創刊號名為《學桴》),其辦刊宗旨即“表學堂之內容,與當代學界交換知識”。其后,無論是民國早期的《清華學報》(1915年創刊)、《復旦學報》(1917年創刊)、《北京大學月刊》(1919年創刊)等大學學報,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創辦的眾多高校期刊,都以此為基調。作為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部,更是通過其規章——《高等學校學報管理辦法》(1998),將大學學報界定為“高等學校主辦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學成果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是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園地”。無疑,大學學報是大學的組成部分,其功能如大學的圖書館,不可或缺。當然,從更深層意義上看,大學學報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師生的學術園地,它的存在和樣態也彰顯了學術自由之精神風貌。
事實上,學報的輻射作用遠遠超出大學學術成果的園地和學術交流窗口這樣的范圍,與大學的功能密切相關。傳統意義上的大學,以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為主要功能,近來國家又賦予其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使命。且不說作為高校科學研究成果刊發的載體,大學學報直接為大學的科研服務,僅就另三項功能而言,學報也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以培養人才這一高校的首要任務為例,青年教師的成長及博士、碩士的養成,無不通過發表科研成果來體現,而學報是其學術成果發表的首選地,許多學者、大家也都坦承是學報扶助他(她)走上科學研究之路的;同樣,許多科研成果通過學報的發表得以呈現出來,獲得政府認可或者國家專利,抑或被政府有關部門或企業事業單位采納,進而服務于社會。至于文化傳承與創新,包括大學學報在內的高校學術期刊更是顯性的承載者、傳導者。如果把大學比作一座座文化寶庫,那么大學學報無疑是這些寶庫中的絢麗瑰寶。
以上是就總體、普遍意義而言。應當承認,由于大學的類型不同,所承載的辦學任務側重點不同,各大學學報發揮作用的領域和程度也有所差異。按通常的劃分標準,中國的大學可分為綜合類、偏專業類(如理工、文科、醫藥、農林、師范等)與高職高專類,其學報可分為綜合性與專業性兩大類,其中,綜合性學報又可分為自然科學學報、工程技術學報與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等。很顯然,理工科學報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加突出一些,而文科學報除了這三大功能之外,在文化傳承與創新方面表現得更為充分,甚至被賦予了意識形態色彩。若按照新的評價標準,中國的大學又被劃分為研究型大學、研究教學型或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等,其學報所展現的理論性層次或應用性程度也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大學的研究能力越強,學報的學術性就越強,反之亦然。因此,無視學校和學報的類型及特色,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來衡量評價大學學報是不客觀也是不準確的。同樣,指責大學學報“小、散、弱、差”甚至于制造沒有學術含量的“學術垃圾”,也是偏頗的。原因在于,相對于國際上流行的集約化、集團化的期刊經營模式,大學學報依附于大學而存在,正如中國的大學一樣,小、散、弱現象不可避免,恰需要主管部門和主辦單位更多地加以引導和大力扶持。至于多產“學術垃圾”,這與當下的學術評價尤其學術生態有關。試想,大學趨同,其學報難免“千刊一面”;選題不多,特別是所謂熱點問題過于集中,文章難免“千篇一律”。實際上,不是學報制造“垃圾”,而是作者在評職、晉級、學位、課題等高壓環境下制造“垃圾”,學報只是這些成果的刊載體。本質上說,是既有的科研成果量化管理和使用的體制、機制使然。因此,對大學學報的評價,首先要看它是否完成了主辦者賦予它作為該大學學報的基本任務(本職工作),看它是否完成了大學學報本應具有的功能作用(賦予職責),而不是只看它刊發文章的被引情況(期刊影響因子)。
當然,提升大學學報的影響力和美譽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網絡信息時代“傳播產生力量”,這也有助于大學學報功能更好地實現。至于如何提升,當是仁智各見。筆者以為,凡社會存在物都有其正反面,大學學報也如此,故可以從降低化解其消極因素和激活提高其積極因素兩個側面同時加以考量。現實地看,以下影響大學學報質量及影響力的因素值得學報人關注:一是大學的辦學層次與特色決定其學報的層次和特色。道理很簡單,學報是大學的組成部分;層次高的大學,大師多、科研強、經費也足,如原來的985、現在的“雙一流”建設大學,其學報稿件優、經費足、編輯力量也強;其他學報并不具備這樣的資源優勢,若想發展好,除非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并且得找到N個提升捷徑。二是大學尤其是校領導的重視程度以及編輯團隊的努力程度,可以拉升學報的存在水平。事實證明,對于一般高校而言,校領導越重視,其學報發展越好、影響力越大。當然,主編或總編(主任)的理念、視野和擔當,以及編輯的整體素養與團隊合作狀態等,都時刻決定著學報的發展態勢。這意味著,辦報人主觀能動性發揮得好,可以使處于一般水平的學報爭得上游。三是學報的發展受制于期刊評價,如何適應是一門學問。傳統的期刊評價主要靠讀者特別是學者的普遍認可,編輯部常常通過擴大期刊發行量(訂閱數)和被轉摘量來實現影響力,而互聯網數字化時代主要通過影響因子計量統計結果而排名,發行量、載文量甚至轉摘量都不再是期刊影響力的決定成分,文章被引(率)成為核心硬指標。在此背景下,專業期刊受到學界(學科群)重視,綜合學報特別是文科綜合學報本來就存在兼顧多學科(欄目)的劣勢,加之受大學本身排名的影響,如果不采取有效辦法,在期刊評價中通常難以走上高端。四是困境并非不能突破,但路徑選擇更重要。在不改變現有期刊評價的格局下,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主辦的學術期刊仍然處于優勢地位。對于更多的一般性大學學報而言,爭取優質稿源、刊發好文章,仍是提高影響因子的首選之策,所謂“內容為王”。其中,尤以編輯策劃選題、組約名家稿件為基本,同時擴大校外作者發文的比重,避免學報真的成為本校教師科研成果的“自留地”。當然,這需要責任編輯不懈的努力和優厚的稿酬予以保障。還有,想辦法增進讀者、作者對學報的了解、關注和引用,這也是非常關鍵的。
*邢志人系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秘書長、遼寧省高校學報研究會理事長、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主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