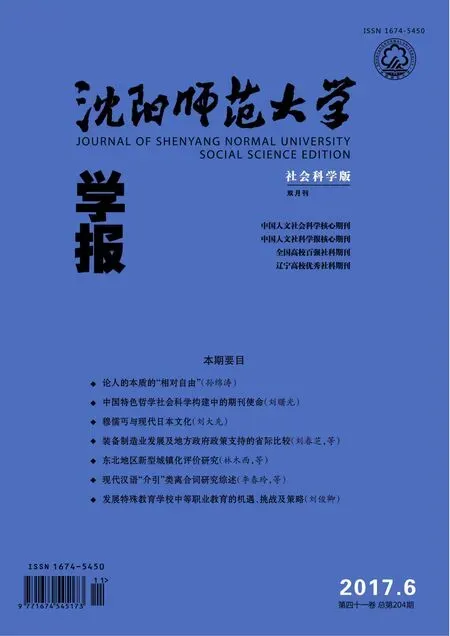偽滿洲國與假親屬關系
——以穆儒丐《新婚別》為個案的考察
羅鵬
(美國杜克大學 亞洲與中東研究系,美國 北卡 27708)
偽滿洲國與假親屬關系
——以穆儒丐《新婚別》為個案的考察
羅鵬
(美國杜克大學 亞洲與中東研究系,美國 北卡 27708)
滿族作家穆儒丐于1942年發表在《麒麟》上的短篇小說《新婚別》不僅探索了婚姻真假的問題,而且涉及軍隊甚至國家的結構與本體論問題,是一篇長期被忽略又值得深入探究的作品。具體說,小說描寫文英與鳳姑的“虛禮假面子”婚姻可以作為當時偽滿洲國社會/政治狀況的一種比喻,包含了家庭、軍隊與國家的思想矛盾,特別值得分析的是典禮與信念對這些社會結構的創作所起到的作用。
穆儒丐;《新婚別》;國家;典禮
“我們是結婚,不是講虛禮假面子的”[1],這句話是滿族作家穆儒丐于1942年發表于“滿洲雜志社”新辦的文學期刊《麒麟》的中篇小說《新婚別》中的主人公趙文英結婚前說給未婚妻鳳姑的話,意在強調他們是為結婚過日子,而不是“講虛禮假面子”的程序。然而細讀小說,卻發現整部小說都充斥著“虛禮”與“假面子”。文英因為經濟條件和漂泊的狀態本不想結婚,且婚后他須立即離家,絕無有婚后生活。因此,小說描寫的不是夫妻的婚姻生活,反而是該婚姻所依靠的一些“虛禮”與“假面子”及其帶來的后果。
一
細分析文英不想結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更忠誠于軍隊。他于宣統三年(1910年)入了隊,四年后收到母親來信,勸他趕快告假回家,以便辦成婚事。不過文英“不但無意于結婚,連家里的事幾乎都不敢說不敢想。”[1]2他擔心自己沒錢,很難養活一個家庭,所以覺得自己暫時最好不結婚。但軍隊領導勸他趕快回家,說道:“告假結婚,也不是沒有前列,何必發愁呢?”[1]3于是,文英同意了回家辦婚事,不過他只能請15天假,其中包括在路上時間,所以他一到家就必須盡快解決婚事,然后立即回軍隊。因此,穆儒丐小說主要描寫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后文英的妻子與母親之間的關系。換言之,文英結婚是由于一些傳統禮教跟面子因素,而小說強調是這些因素的后果。
雖然小說描寫的主要是一些小家庭情節,卻也包含更廣闊的意義。具體地說,小說所探索的婚姻真假問題,還涉及軍隊甚至國家的結構與本體論問題。比如說,軍隊與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是什么關系?國家與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理想是什么關系?此外,《新婚別》的故事雖發生在民國初期,但同時也可投射到20世紀40年代的偽滿洲國歷史,并且間接地反映偽滿洲國背后的一些政治狀況:比如,所謂的偽滿洲國”中的“國”字與“偽”字有何意?
文英的未婚妻鳳姑是個孤兒,寄住在叔嬸家,過得頗不如意。因此,鳳姑得知文英要回家娶她,自己就無比快樂。但鳳姑無法理解,為何文英不能在家多住一段時間,而必須立即回軍隊。鳳姑問文英為何非要當兵不可,為何不退隊和她一起生活。有趣的是,文英的回答,強調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他與軍隊的一種充滿自相矛盾的感情關系。他說,他剛入隊時,本覺得他打錯了主意,覺得軍隊不適合他,但后來發現一師人“都有志愿”,于是慢慢接受了這種新的生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文英與軍隊的關系類似于包辦婚姻,婚后慢慢地習慣了對方。反諷的是,這個比喻性的“包辦婚姻”后來直接影響了文英跟鳳姑真正的“包辦婚姻”。他不能夠(或者不愿意)跟新娘住在一起,是因為他非要立即回到他另外一個“新娘”——軍隊的懷抱。
此外,軍隊本身在這段時期也經歷了一種巨大的改變。小說第一段就說明:
趙文英之被選入禁衛軍,是在宣統三年,那時全軍已然毫無遺憾的組織完竣……同時革命志士,排清先鋒,別軍的一位將領藍天蔚,也想與武昌呼應,于演戲中,欲以實彈解決禁衛軍,也不知道是事機不密,也不知道是主義的沖突,到底未能實行,禁衛軍連夜撤回北京師[1]4。
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文英由原來的支持清朝禁衛軍轉為支持替代清朝的民國政府,因此,他忠誠的對象主要是軍隊本身,而不是軍隊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如果把軍隊看成是一個婚姻的比喻,這種比喻性婚姻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它的“家族”(即軍隊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理想),反而在于其“婚姻體制”(即軍隊系統)本身。在這里,政治理想變成一種副作用而已,是軍隊本身的體制。
這樣看來,文英與軍隊的關系在一方面類似于一種傳統的包辦婚姻,但在另一方面類似于一種新時代的“自由戀愛”婚姻。一方面,像包辦婚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樣,文英與軍隊所代表的政治理想的關系是依情況而定的;不過另一方面,像一種所謂的自由戀愛中的愛情關系一樣,文英為了參軍就自愿地離開家并且沒完全符合母親的要求。無論如何,結果都是文英忠誠于其對象本身(即軍隊、婚姻),而并不是忠誠于其所代表的政治或家族理想。
文英對婚姻的十分矛盾的看法也反映在他對“定禮”與“財禮”兩種傳統習慣的態度。到了結婚的時候,養活鳳姑的叔叔嬸娘向文英家要了一筆“定禮”錢,敘述者強調那時候在北方定禮已經被看成是一種落后的習俗:
在北京,無論城里城外,往外聘女兒,就沒有一家向男方要錢的,無論家境怎樣寒,全以嫁女要錢,是一件可恥的事。“財禮”兩個字,在北京人大都很渺茫,一點觀念也沒有,不怎么姑娘叫賠錢貨呢。除了真窮得沒了絡兒,把女兒給人作小,那當然得提錢,甚至要求養老,但是那是婚姻上的變則,也許根本提不到婚姻,一半皆以為舊式婚姻,全是買賣婚姻,可謂錢到家,還得重行檢討[1]23。
反諷的是,鳳姑的叔叔就是一個“地道北京人”,但他還是堅持要一筆錢當作定禮和財禮,而文英家不得不同意。文英把錢給鳳姑的親戚這一舉動,強調了婚姻所包含的經濟意義,使“新娘”帶上了一種商品化的含義。
雖然文英在強調自己婚姻并不是一種“講虛禮”,可他后來接受的是所謂的“定禮”與“財禮”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虛禮”的表現。再說,當作一種典禮的婚禮本來就是一種“虛禮”,因為所有的典禮就有一種“虛假”的意義。典禮本身就是一種表演,不過這種表演可以創造真實的后果。
二
此外,文英決定跟鳳姑結婚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孝順母親。他的母親一直想要一個孫子,又因年紀大,也需要有人在家里陪她。因此,文英希望鳳姑會代替他照看母親:“只要她(鳳姑)賢惠,到底能替我孝順您。”[1]11文英這段話一面強調他對母親孝順,一面又說明他希望鳳姑替他盡孝。即,文英希望鳳姑會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擔本來屬于他孝順的責任。結果,孝順從倫理理想概念轉型“商品化”,而變成一種可以傳遞于交換的物品。
總而言之,文英雖然向鳳姑強調他們“不是講虛禮假面子的”,但實際上,從文英接受鳳姑叔叔對“財禮”的要求,到他后來讓鳳姑替他盡到對母親孝順的責任,文英與鳳姑的婚姻依靠的完全是一些“虛禮”的習俗。同時,文英與鳳姑的婚姻雖然不能說完全是靠“假面子”,但婚姻還是從頭到尾都反應一些與面子有關的要求。不過小說還說明該婚姻對鳳姑來講還是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影響了她的道德觀和身份認同。
成婚以后,鳳姑哭著勸文英退伍,讓他留在家里與她一起生活,文英的反應十分有趣。敘述者解釋說,“這時候文英,把剛被鳳姑的眼淚所軟化的柔腸,復興強化起來,軍人!軍人!軍人在模仿寶玉太可笑了”[1]27。在此,文英發現自己對鳳姑的感情開始被浪漫化了,必須提醒自己一個軍人不許有《紅樓夢》所代表的情感。當然,文英在否認自己與賈寶玉相同的過程中,作者同時也是在提醒讀者《新婚別》與《紅樓夢》這樣類似于言情小說的作品是多么相似。并且,像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一樣:“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2]。《新婚別》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也基于讀者的眼光,而不完全在于文學文本本身。
《新婚別》提到《紅樓夢》這一段很像吳趼人1906年的小說《恨海》中的一個細節。《恨海》中,仲藹的未婚妻雖然拋棄了他,然后去上海當妓女,不過仲藹一直保持對她的“忠”。過了很久,有一天仲藹的同事帶他去上海的一家妓院,仲藹就開始嘲笑他們:“世人每每看了《紅樓》,便自命為寶玉。世人都做了寶玉,世上卻沒有許多蘅蕪君、瀟湘妃子”[3]。后來他又加了一句,說“寶玉何嘗施得其當?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若要施得其當,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間”[3]228。《新婚別》與《恨海》的男主人公都以《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為婚姻中的一種反標準。但是兩者中間也有重要的區別。《恨海》中的仲藹覺得《紅樓夢》所代表的浪漫感情應該保留在(男人與妻妾之間的關系)“婚姻”內,而《新婚別》中的文英卻想說服自己類似的感情必須排斥到(軍隊的比喻性的)“婚姻”以外。但兩部作品的男主人公都認為對現代婚姻而言,賈寶玉所代表的浪漫感情都是“假”的,而且是必須被排斥的。
《新婚別》與《恨海》兩部作品有許多相似之處。兩部小說不僅都用《紅樓夢》討論一些婚姻與愛情的問題,而且小說情節都發生在十分接近的歷史階段。《恨海》描寫的是發生在1901年義和團運動時期背后的一些情節,而《新婚別》主要描寫的是一些發生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后的一些情節,而且兩部小說都用失敗的婚姻來反映當時中國的政治轉變。一方面,情節中婚姻的失敗直接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的混亂:每次都是因為叛亂或大戰,阻止了試圖結婚的雙方(《恨海》)或導致雙方婚后無法在一起(《新婚別》)。此外,兩部作品中的愛人都有一方表現出比較理想的態度。比如說,在《恨海》中,仲藹的未婚妻雖然拋棄他去賣身,仲藹對她還是一直保持一種純潔忠誠的態度。就是說,新娘雖然頹廢,新郎還是理想化。而在《新婚別》中,被理想化的不是新郎(文英),反而是被拋棄的新娘(鳳姑)。文英回軍隊以后,鳳姑就十分辛苦地試圖養活自己及她的婆婆,甚至有一段時間鳳姑不得不去城里賣身。但跟《恨海》剛好相反,這里鳳姑的賣身行為所表現的不是她的道德墮落,反而是她的極端孝順及忠誠,說明她愿意犧牲自己,為了扶養自己的婆婆——即從未和她一起生活的丈夫的母親。
這里十分反諷的是,雖然文英與鳳姑剛結婚的時候,鳳姑的親戚要求“定禮”與“財禮”錢反映了一種比較保守的態度,但婚后鳳姑不得不賣身卻是出于她對婚姻理想的忠誠態度。兩者都是非常典型的把女人商品化的過程,不過小說中兩種作法的作用與意義剛好相反。前者強調傳統婚姻所依靠的一種經濟關系,而后者指的是當作新娘的鳳姑自我商品化以便實行一些傳統倫理理想及一些當前生存的需要。
三
《新婚別》雖然發表于民國初期,但文本偶爾會提醒我們其“理想讀者”并不是生活在以小說作為歷史背景的晚清/民國初的人,而是生活在穆儒丐寫作時的偽滿洲國的讀者。比如說,小說開頭描寫文英如何從支持清朝的禁衛軍轉為支持替代清朝的民國政府時,還寫道:
……可是自此以后,革命排清的風潮,蜜也似的甜,醴也似的濃,醉著人們的心,濟著人的口,“不推倒清人的政府,國家萬不能富強,人們也萬不能自由的!”真的嗎?那就用不著問[1]4-5!
“真的嗎?”一句,雖然這里不清楚疑問的對象是誰,但再往下有類似的疑問句,而其(想象中的)對方更加清楚:
……老百姓!真不知你們燒了什么高香,但是它們沒放棄嗎?……放是放了?青年的先生們也許想象不出來,我告訴你們吧,它們雙方所放的機槍子彈……[1]5
在這里,描寫晚清到民國的轉變時,敘述者提醒我們該文本的理想讀者本來就是40年代偽滿洲國的青年人,并且還暗示這些歷史情況對“當代”讀者也許會顯得比較陌生。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作者關心的不僅是這些晚清/民國的歷史狀況,而且是偽滿洲國的社會/政治背景。
具體說,小說描寫文英與鳳姑的“虛禮假面子”婚姻可以作為當時偽滿洲國社會/政治狀況的一種比喻。像文英與鳳姑的婚姻一樣,偽滿洲國也是在一種“虛禮”和“假面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單位。雖然偽滿洲國表面上是一種獨立的國家,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假國而已——一種模仿獨立國家的日本殖民地。不過,就像文英與鳳姑一旦結了婚雙方都開始把婚姻看成是一種真實的關系一樣,類似的,雖然從某種政治或法律的角度來講偽滿洲國不過是一種“偽造”的國家而已(即,偽滿洲國),但是對所有屬于該國家的人民而言,這個社會/政治結構還是有現實的功能跟意義。
再說,在這一方面,偽滿洲國跟其他國家也有些共同之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推出所有的現代國家都依靠一種“想象的”基礎,并且這種基礎在某種程度總是借用人們對家庭與家族的理解作為一種思想背景。不過安德森也強調所有現代國家雖然都依靠一種想象的基礎,不過對屬于該國家的人們來講,這些國家都有一種完全現實的存在。換言之,像一個傳統的婚姻與家庭本來是依靠婚禮及其他的“虛禮”性典禮造成的,模仿一種大家庭的家國也是依靠許多本質上的“虛假”的政治典禮造成的。
在《典禮理論,典禮做法》一本書中,凱瑟琳·貝爾說明許多對典禮的理論都認為典禮的“內在邏輯”在于一種“對思想與做法的分化與再聚合”[4]。她的結論是雖然人家經常以為典禮會創造一種共同信念,她卻認為“典禮活動并不促進信仰或者確信,反而典禮做法允許很多不同的理解,而只要求參與者接受做法在形式上的合一”[4]186。這樣看來,典禮就像魯迅眼中的《紅樓夢》一樣,不同讀者會在同一個文本找到不同的意義。
就像魯迅對《紅樓夢》與貝爾對典禮一樣,安德森認為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國家的存在不基于大家對它有一種共同的信念跟理解,而剛好相反,是基于國家本來就是一種空白的結構,允許大家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換言之,國家的核心不在于它所代表的思想或者概念,反而在于表面上的形勢——只要大家能夠對其形勢保持一種共同的認同,他們就能夠投給它許多不同的信念與概念。斯拉沃熱·齊澤克則就利用拉克勞和墨菲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的想法,進一步地認為社會或國家不僅是空白的結構(他們說明“社會不存在”),而且認為其核心其實是一些基本的思想敵對與不一致性,而與其有關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剛好是在掩飾這些不一致性,掩飾“社會不存在”的事實,掩飾人家對它的認同的必然失敗。
這樣看來,《新婚別》暗示了偽滿洲國不僅是一種蓄力并且偽造的社會結構,而且作為故事背景的清朝及民國——再加上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一些包含內在的思想敵對與不一致性的“虛禮假面子”的后果,而且托給這些社會結構一種現實意義剛好是這些內在矛盾所引起的社會意識形態系統。按照這樣看來,國家與軍隊的模型并不是典型的家族,反而是一套假親屬關系——人家模仿親屬關系以便建立或者鞏固一些新的社會關系。
[1]穆儒丐.新婚別[M]//詹麗.偽滿洲國通俗作品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25.
[2]魯迅.絳洞花主:小引[M]//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177.
[3]吳趼人.恨海[M]//張振鈞.中國大眾小說大系:近代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228.
[4]Bell,Catherine.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6.
Manchuria and Fictive Kinship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Post-Wedding Separation by Mu Rugai
Carlos Rojas
(Institute of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Duke University of USA,Durham North Carolina 27708)
The short story Post-Wedding Separation by Manchu author Mu Rugai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Qilin in 1942 explores not o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 and fake marriage,but also structural and ont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military and even the nation.In particular,the story’s description of the “empty ritual and false face”marriage between the protagonists Wenying and Fenggu can be taken as a metaphor for the socio-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ontemporary state of Manchukuo,and specifically its reliance on a set of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t the familial,military,and national level.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ole that ritual and belief play in constituting this sort of social structure.
Mu Rugai;Post-Wedding Separation;nation;ceremony
I206.6
A
1674-5450(2017)06-0051-04
2017-09-07
羅鵬,美國人,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責任編輯:詹 麗 責任校對:張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