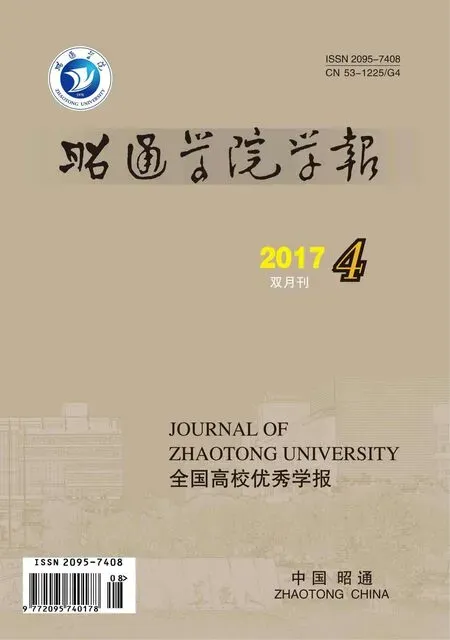柏格理筆下的近代西南婦女形象研究
金榮慧
(貴州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烏蒙論壇
柏格理筆下的近代西南婦女形象研究
金榮慧
(貴州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傳教士柏格理遠渡重洋來到中國西南地區傳播基督福音,在和花苗與漢族婦女的近距離接觸中,形成了喜愛與批判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而造成這種反差極大的書寫策略與認知態度的原因,與柏格理傳教士身份定位、文化屬性及敘述者身份緊密相關。
苗族婦女; 漢族婦女; 書寫策略; 文化場域
以英籍傳教士塞繆爾·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為代表的西方入華循道會士,對中國近代西南地區的宗教與文化教育影響極大。柏格理把人生中的28年歲月貢獻給了中國西南地區,一直恭承踐履“為基督征服世界”的傳教使命。在中國的前17 年,輾轉于云南境內,主要以漢族為傳播對象;后11 年,則跋涉于滇黔川交接地帶,扎根于苗族之中。柏格理記錄了在華傳教的艱難歷險,書寫了西南各村落的風俗習慣與當地的風土人情。除柏格理外,還有其同輩和追隨者記錄了在中國西南傳教的生活點滴。而通過研讀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國》、王樹德《石門坎與花苗》以及甘鐸理編輯《柏格理日記》,則可洞見柏格理筆下漢族婦女與苗、彝族婦女形象有著明顯差異。造成這種反差態度的根由何在?筆者主要借助于形象學理論與方法,從傳教士們的身份與使命及文化場域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淺析。
一、形象書寫面相述略
柏格理在記錄傳教生活中遇到的漢族婦女與苗、彝族婦女時,經常采用反襯對比關照法進行書寫,即常將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在服飾、處事、習性置于同一敘事時空和文化語境下加以述說。柏格理對兩者形象的描述使用了具有濃烈感情色彩的詞語,形成了兩個極端。兩相對比,柏格理的情感傾向顯得十分鮮明。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服飾與纏腳方面。柏格理描寫了在鄉村集市上的一景,“身穿膨脹似囊褲子的漢族小腳婦女縱然是鄉場里眾多女子中的一道風景線,但是他們跛來跛去的不自然的扭捏動作,與行走快當、徑直向前、身姿優美的山里婦女比起來就令人感到不舒服,山里的女人根本不屑于纏起她們的雙足,她們真是邁出婦女勝利的步伐……更為漂亮和舒適的是自然伸展的五個腳趾,顯示出沒有人為畸形的蹤跡。”[1]196他們喜愛苗、彝族婦女自然健康的天足,而批判纏著畸形腳的漢族婦女。傳教士們完全不能接受這種傷害自身肉體健康的行為,因為“裹足期間,肉常常腐爛,腳底大面積壞死,有時候腳趾會一個個掉下”[2]。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柏格理對自然腳的欣賞和對小腳的厭惡,更多的是一種對人的尊重和悲憫,充滿了同情和愛。柏格理推崇有著和英國婦女一樣大腳的穿著長裙的苗、彝族。他認為她們的服飾是一種山水相融合的美。而“通常穿戴著美麗的繡花鞋、裹著高度著色的綁腿、穿著繡有精美花邊的濃艷驚人的綢褲”的漢族婦女的精美的裝扮則被他們嘲諷為“試圖創造她們的較低檔次的最大吸引力”[1]226。
第二,在性格與為人處世方面。柏格理喜愛苗、彝族婦女的大方與直率,對漢族婦女的羞怯與忸怩作態感到相當不適。他這樣描寫與彝族姑娘的相處:“她們不時笑起來,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呈現迷人的笑容……這里的婦女率直、大方,令人感到愉快,她們沒有那種伴以虛偽羞怯的做作。”[1]236彝族婦女在和男子相處的過程中讓人感到舒適而友好。但是“這些諾蘇婦女與英國女性一樣,完全可以盡情說笑,并在談笑風生中顯現出何等之快活”[1]245,而和漢族婦女交談則給人一種難受的氛圍,她們在有男子在場的情況下總是把臉側向一邊或者不講話。“雖然貧窮、不太節儉、不愿意斗爭,但他們純樸、慷慨、誠實、可愛。”[3]這在柏格理看來,正是漢族婦女缺少的。然而漢族婦女長期忍受家庭專制,“婦女的德行總以不健談不饒舌為上,又不是東家西家的亂闖閑逛,又不宜在街頭路側昂首觀看異性。”[4]不可能和外男大聲說笑了。
第三,反對性別歧視。西方傳教士對于漢人婦女買賣女孩等泯滅良心行為極其厭惡。基督徒們倡導男女平等,因為無論男女,在基督耶穌那里都成為“一”。柏格理在日記中記載,“一個做母親的把她十幾歲的小姑娘賣給了一位大約60歲的老頭子。……姑娘很怕她的母親,只好憤然自殺。趕到太晚,已沒救了。”[5]他描寫到“在這里充斥著溺嬰行為、買賣女孩從事傷風敗俗行業的勾當”[1]363。基督徒反對殺嬰行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遵從上帝的“不可殺人”這條訓誡,而且這種做法違反了基督教強調生命神圣性的信仰。較之漢地漢民中慣常的溺女嬰形象,苗、彝婦女是不會這樣對待無辜的生命的。
二、形象建構策略
事實上,中國婦女并不完全是柏格理日記中所記載的丑惡的形象,為什么柏格理會進行這樣一種抬高貶低的書寫方式?筆者認為柏格理已然的傳教士身份定位、文化屬性及敘述者身份影響了他自我確認的書寫策略。
柏格理在描寫漢族婦女與苗彝婦女形象時所用的詞匯與語調有著鮮明的差異。漢族婦女的“扭捏動作”“畸形”“虛偽羞怯”與苗、彝婦女的“身姿優美”、“漂亮和舒適”、“率直大方”形成了兩個極端的對照。其中的好惡態度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用這些美好的詞句夸贊苗、彝婦女時,我們發現柏格理下意識地把她們和英國婦女做對比,如上文的不纏足的婦女是“邁出婦女勝利的步伐”,英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提高了婦女地位,是婦女的勝利。柏格理這樣描述了彝族婦女第一次見到他們時的情形,“當他們看清我不是漢人,又聽到我們英國女人都具有一雙天生的大腳,像諾蘇女子一樣穿著裙子,不似漢族女人那般纏足與穿褲子,他們立即對我有了好感。”[1]196甚至說到彝、漢婦女在有男人在場的表現,都強調了諾蘇婦女與英國女性一樣,會盡情地談笑風生。這就是柏格理喜愛苗、彝族婦女的原因,因為他們和英國人在某些地方是相似的。不管是對苗、彝族婦女的抬高還是對漢族婦女的貶低,都是和傳教士們的身份和他們的文化優越感息息相關的。“貶低、褻瀆或者否定他人的生活和習俗,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確定自己的優越感,即自我確認。所謂的自我確認是歐洲白人認為他們有責任將歐洲的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通常是以‘文明、人性、科學和進步為名的集體主體反復強調其價值,從而獲得權力與主導地位。’”[6]借漢學家費正清之言,19世紀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根據《圣經》的宗教教義和美國建國之父們的政治原則,堅信(美國的)道德和文化的價值,甚至經常相信這種道德與價值的優越性。”[7]柏格理是為西方文化而驕傲的,是以英國文化的優越感來描述他們眼中的中國婦女的,評判的標準是以英國文化為尺度的,而這種自我確認是和傳教士的使命相結合的。英國傳教士東渡而來就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的福音,這就是他們的任務與使命。不管是對漢族婦女的貶詞,還是對苗、彝族婦女的褒獎,都是對英國文化優越感的一種彰顯。漢族婦女的陋俗與怯懦,正是基督教需要拯救的對象,而對苗、彝族婦女和漢族婦女兩相對比的勝利,正是說明他們有被傳教的希望,柏格理在中國的前17年主要在云南的漢人地區傳教,但是收獲幾無。而在石門坎花苗地區卻收獲了大量信徒。正是基于柏格理在苗彝地區所受到的支持與愛戴,讓他們得到了心理上的認同,自然能獲得更多的偏愛。因此柏格理在心理上自然是更傾向于苗彝婦女。正因如此,柏格理在面對苗族“宿寨房”這一陋習時也沒有像指責漢人的生性多疑那樣懷疑苗、彝族道德倫理的低俗。這樣兩相對比的表述是藏在柏格理的個人化的敘述之下的。
除此之外,柏格理的著述作為敘事作品,我們仍需考慮敘述技巧以及敘述者和閱讀者的關系。在敘事文中,由于講述者的觀察角度不同,同一故事在不同的人眼里將會大異其趣。“敘事者在材料的取舍、組構過程乃至語氣的運用上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故事的面貌和色彩。”[8]柏格理作為故事的講述者,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個人化的敘述下帶有極強的情感色彩。由于是柏格理根據親身經歷而記述,他們既是故事的敘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描寫了他們的所見所聞及其感受。如果根據視角的劃分類型,柏格理采用的當然是內聚焦的視角,通過“我”的感受去看、去聽,記述的事件是“我”接觸的外部消息以及自己內心產生的活動。由于敘述者及作者清楚地給讀者展示了他周邊的環境,并且表露了自己的內心想法,這樣的一種表述方式拉近了讀者和人物的距離,使讀者產生一種可信感和親切感,使讀者能夠容易接受故事的真實性。但是這樣的表達方式,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敘事者“我”對于其他人物則是旁聽者,任憑接觸去猜度他們的思想感情。而他們作為故事的敘事者,作為遠方的異鄉人,他們的知識、經歷、身份以及卷入到事件的程度而對故事的描述有所偏頗,盡管他們本人沒有意識到。
至于這些文字的讀者對象,肯定不是中國人而是傳教士們的英國同胞。柏格理筆下的中國人形象是有損的,不管是中國漢人的“陰險狡詐”還是中國政府官員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本書肯定是不能得到漢族人民的接受,反而會引起漢族人民對傳教士的排斥。所以此書的讀者只能是英國人民。傳教士被派來中國,必須對傳教情況進行匯報。正如1817年新教傳教士創辦的《印中搜尋》“是為了使倫敦會在東方的傳教士們了解關于歐洲和亞洲的各類消息,讓他們相互了解各地的傳教動態,為她們提供互相溝通的媒介,并使人們了解各地‘異教徒’的情況”[9]。如同《印中搜尋》的讀者對象是英國和歐洲各界人士,各地的傳教士以及各殖民地的英國人那樣,柏格理著述的閱讀者同樣是英國同胞等西方人士。這些傳教士們親身經歷而書寫的作品,成為英國知識界與社會群眾了解中國的重要資料來源,所以其書寫要切近英國人的接受和趣味。與此同時,傳教士們的書寫不得不說是有意博取英國民眾對其傳教的認可與支持。柏格理來華目的是十分清楚明確的,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基督信徒。然而19世紀的中國國內普遍把“傳教士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聯系在一起,并且“傳教士與西方在中國的商業擴張”也有極大的關聯。[10]傳教士在中國很不受歡迎,人們仍然對其傳教目的十分懷疑。柏格理在漢人地區的傳教可以說是失敗的,也因如此,柏格理才會從云南轉移到石門坎。他不可能大肆渲染自己在漢人地區傳教的無所作為,更不可能贊美漢人文化博大與先進,贊美漢人的值得稱贊的品性,這樣會顯得基督教在中國無用武之地。而在石門坎地區,傳教士確實做了諸多貢獻,也受到了苗彝人民的歡迎,凸顯了基督教的價值與作用,傳教士方能在中國繼續傳教。
由以上可得知,柏格理對中國漢族婦女形象的書寫是一種片面的解讀。柏格理看到的更多是無知順從的、愚昧的甚至兇殘的婦女形象,這和柏格理的書寫策略及讀者對象息息相關。但是賽珍珠浸潤體感于中土文化三十年之久,其筆下的中國農村婦女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形象,賽珍珠筆下的阿蘭就是勤勞純樸、虔誠信仰、善良堅強、勇于反抗的中國農村婦女。193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給賽珍珠《大地》等作品的授獎評語就是“她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史詩般的描述,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豐富的”[11]。可見,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漢族婦女同樣有純樸堅強的。
三、不同形象塑造的背后成因
柏格理為什么會采用這種抬高貶低的自我確認的書寫策略?像所有形象學意義上的形象塑造一樣,柏格理對中國西南婦女印象也源于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自覺意識或潛意識中。巴柔教授曾說:“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虛弱的。”[12]“他者形象如同一種次要語言,平行于我所說的話語,與其共存。”[12]柏格理正是處在“自我”的位置來審視“他者”。在對中國西南婦女的塑造中,他描述了一種文化現實,并且通過這一描述,說明了他們置身在其間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空間。而他者的形象也傳遞了我自己的形象,在言說他者時,通過否定他者來言說自我。因此異國形象的美好與丑惡則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者文化。
柏格理與中國西南婦女處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中國與英國有著不同的文化語境。文化語境主要指言語行為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由既有的社會體制、綿延的文化積淀與活態的民族生態等方面建構而成。柏格理所屬的英國文化場與漢民族文化場是兩個極具反差性的文化場。而以作為主體的漢民族與邊緣苗族的文化場又有極大差別。柏格理傳道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宣道對象生活的文化語境。顯然,邊緣苗族是符合在英國的,更容易成為上帝的信徒。傳教士們對于漢人婦女與苗族婦女的感情與態度顯然是和對方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密切相關,對于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漢民族文化場域自然是排斥的。傳教士通過否定漢文化而言說了英國文化。柏格理更多地是對儒文化的否定。漢民族文化以儒家思想占主導,“普通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審美情趣、風俗習慣等亦多以儒學觀念作為內涵。”[13]儒家有一整套完整的倫理規范與道德秩序體系,而其中又有豐富而系統的女性倫理思想。柏格理筆下的這些漢族婦女的行為舉止正體現了儒家婦女觀。中國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基本倫理格局。女性在外在內都沒有話語權。而且在家庭這樣的小社會里,對于女性的為人處世有著諸多要求。女子必須遵守“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在這一系列的道德規范的基礎上,形成了“男女授受不親”甚至極端的女子“從一而終”的貞操觀,民間稟信女子應該“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女子只能一切聽命于男子。柏格理筆下的漢族婦女就是處在此種儒家婦女觀的倫理秩序中,銘記男女大妨的漢族女子因而是忸怩、羞澀地面對外男。而歷來被傳教士批判的纏足也是女子為了迎合北宋以來男性以“三寸金蓮”為女性美的審美觀。儒家婦女觀規定了女子的行為舉止,所以柏格理筆下的漢族婦女是懦弱的、無知的、順從的,面對抽鴉片的丈夫她們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自殺。控制著婦女行為的倫理綱常是男權社會制定的,儒家婦女觀是儒文化的一部分,柏格理對漢族婦女的批判實際上是對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排斥。他們批判漢族婦女的矛頭背后是直指整個漢文化的。柏格理進入中國的目的就是傳教,而面對一套對人們產生根深蒂固影響的儒家思想學說,柏格理等傳揚的基督教文化無論如何也無法撼動它的核心地位,在云南17年的傳教失敗就是憑證。他們試圖瓦解中國傳統符號體系而代之以基督教符號體系,他們要實現中國的基督教化,“使整個國家基督教化的含義,不僅是爭取信徒,還要消減異邦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倫理滲透到整個社會結構中去。”[14]71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是兩種不同的異質文化,他們不能同化,那就只有消解。所以正如王以芳在《論美國傳教士對中國晚清社會的“文明化”虛構》中所說的“在美國傳教士構建的基督教符號體系中,他們首先將中國納入到‘文明化’的反面位置‘野蠻化’上,構建了一種‘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中國形象。當這種形象獲得廣泛認可的時候,對于中國的改造就獲得了道德感和正當性。”[14]71柏格理同樣是如此。他們筆下的漢族婦女是病態的,是野蠻落后的漢文化的代表。而苗族婦女卻是和英國婦女一樣可以大步走路,和男人大方談笑。柏格理在描寫苗族婦女的女性形象時,明確地顯示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感,確立了英國婦女是被解放的女性的示范——自信、大方、追求男女平等。無論是對漢族婦女的批判還是對苗族婦女的喜愛都是在為了表現西方文化的優越感——是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他們通過表達儒文化的不合理存在而確定基督教文化的正當性與普適性,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文化,強調以基督教文化救中國的目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外,由于苗族同胞不僅和英國婦女在性格與穿著上有相似之處,柏格理有把苗族婦女“歸化”為可以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對象,他們在石門坎的傳教非常成功,對苗族婦女自然更加喜愛。據艾莉森·劉易絲教授所說,以昭通為基地的英國圣經基督教的傳教士群體中,有些人就是來自英國的少數民族和山區。“柏格理家族即屬英國的少數民族之一,并與中國西部苗族都有一段相似的被迫向西南方向遷徙的經歷。”[15]他們同樣也是下層階級出身,如此便奠定了心里認同的感情基礎。不得不說,傳教士們對苗族婦女的喜愛是融入了書寫者自身的情感在內的。這是一種民族際遇和文化身份的認同感。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柏格理對中國人民的關懷與憐憫同樣是真心實意的,是出于人道主義的人性關懷。他們看到了中國婦女低下的從屬地位,同情不幸的受折磨的傳統婦女,他們更加歡喜能在中國看到解放人性的苗彝同胞的人的權利的彰顯,更加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以人為本的觀念帶入中國,解救不幸的人們。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柏格理對漢族婦女與苗族婦女的不同態度,不僅僅是傳教士單純的愛與惡,他們的這種書寫策略與認知態度更多地是融合了傳教士的文化身份與來華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確實部分地揭示了漢民族存在的惡習乃至孽根性。但是柏格理由于身份與文化屬性等原因而對作為“他者”的中國形象的描寫有所偏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中國民眾不幸的同情與救助,他們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與作為人的天性的關懷在書中依然清晰可見。
[1]柏格理. 在未知的中國[A]. 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
[2](美)阿爾文·J.施密特. 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M]. 汪曉丹,趙巍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1.
[3]王樹德. 石門坎與花苗[A].//柏格理. 在未知的中國.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394.
[4]林語堂. 吾國與吾民[M]. 華齡出版社,1995,143.
[5]甘鐸理. 柏格理日記[A].//柏格理. 在未知的中國.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634.
[6]張文瑜. 英國領事夫人筆下的新疆形象與書寫策略[J]. 中國比較文學,2015(2):188.
[7]王以芳. 19世紀媒介形態下的美國來華傳教士群體建構的中國形象與美國形象研究[D]. 山東大學,2013:69.
[8]胡亞敏. 敘事學[M].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9.
[9]吳義雄. 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M].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441.
[10]董延壽. 基督新教在河南的傳播與發展研究(1883-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8.
[11]1938年諾貝爾文學頒獎詞//史上最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及頒獎詞(1901至2015)[EB/OL]. 語文學科網,(2015-12-19).http://www.zxxk.com/soft/4862112.html
[12]孟華. 比較文學形象學[C]. 北京大學出版,2001,2,124.
[13]姜聿華,宮齊編. 中國文化述論[M].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259.
[14]王以芳. 論美國傳教士對中國晚清社會的“文明化”虛構[J]. 山東社會科學,2013,(06):67-71.
[15]東人達.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1840-1949)[D]. 中央民族大學,2003:49.
On The Image Of Women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rough Pollard’s Eyes
JIN Rong-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In the 1900s, the British Methodist Samuel Pollard travelled across the oceans to southwestern China in order to disseminate the gospel. Then, two kinds of totally opposite attitudes were shaped in his contact with the Flowery Miao and Han wome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be into the reasons which lead to his clear-cut writing strategies and cognitive attitude. It explores that the outcome is closely-rooted in Pollard’s identity as a preacher,a western narrator and his cultural background.
Flowery Miao Women ; Han Women; Writing Strategies; Cultural Field
K297.74
A
2095-7408(2017)04-0028-05
2017-05-16
貴州大學文科重點學科及特色學科重大科研項目“英語文獻中的貴州形象研究(1860-1949)”(GDZT201506)階段性成果。
金榮慧(1992— ),女,貴州大方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學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