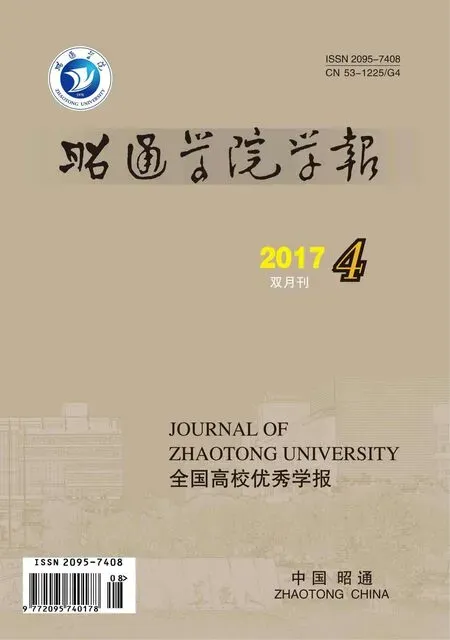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特色
鄭燕姣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文學研究
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特色
鄭燕姣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秦婦吟》是唐代重要的長篇敘事詩,它以不斷轉換的限知視角、縱橫交錯的結構模式、動靜結合的環境描寫,彰顯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論文試從這三方面入手,來闡釋其本身所具有的敘事藝術性。
《秦婦吟》; 限知視角; 結構模式; 環境描寫
《秦婦吟》是晚唐詩人韋莊的代表作,是唐詩史上一首重要的長篇敘事詩。此詩誕生時曾風靡一世,吟傳甚廣。然而由于政治緣故,韋莊晚年諱言此詩,后來其弟韋藹為他編輯《浣花集》時也未將此詩收入,致使此詩被湮沒上千年。直至近代,《秦婦吟》寫本才復出于敦煌石窟。自其復出以來至現在,對它的研究已近百年。百年以來,學者們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價值,以及作者諱言此詩的原因這幾方面。然而,《秦婦吟》作為一首生動記載時代動蕩與戰亂的長篇敘事詩,其敘事的藝術價值顯然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本文擬從敘事角度、結構模式、環境描寫這三個方面入手,挖掘其作為敘事詩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一、不斷轉換的限知視角
不同于小說戲劇,敘事詩用詩的形式記敘人和事物,通過對事件的場面重現和相對的完整的故事情節來抒發作者的感情,表現篇幅長短不一。而關于敘事詩這種體裁是否能夠獨立存在,曾有過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詩的本質在于抒情,不能敘事,一敘事也就沒有詩了。而彭功智先生認為,敘事詩這種體裁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從世界范圍來看,敘事詩不但獨立存在,而且它的產生還早于抒情詩。歐洲的詩史開始于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首詩是世界公認的敘事詩,我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從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來看,我國詩歌歷史始于抒情詩,但是《詩經》中也不完全是抒情詩,敘事詩也占很大的比重。[1]我國古代不但有大量的敘事詩,而且藝術質量也極高。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敘事詩的繁榮時期,涌現出了一系列敘事詩的名篇佳作,其中以韋莊的《秦婦吟》尤具代表性。
敘事詩同樣作為敘事作品,對敘事文本的情境、事件、人物等進行描繪時,也需要有一個看待這一切的視角,或者觀察點,通過這一觀察點將所看到的一切呈現出來。熱奈特以“視點”這一范疇為出發點,通過考慮聚焦主體,將敘述聚焦分為三類:零聚焦敘事、內聚焦敘事、外聚焦敘事。零聚焦敘事是一種無所不知的敘述者的敘事,敘述者所知道的多于人物。內聚焦敘事是敘述者只說出某個特定的人物所知道的情況,敘述者等于人物。外聚焦敘事是敘述者少于人物所知道的,相當于敘述者小于人物。[2]87韋莊的《秦婦吟》通過一位身陷兵中復又逃離的長安婦秦婦之口陳述其親身經歷,從而展現了那一大動蕩的艱難時世之各個方面,采用的便是內聚焦敘事下不斷轉換的限知視角。
全詩總共十二段。第一段行人在路旁遇見在綠蔭下歇腳的“如花人”,便問女郎從何處而來,女郎未語聲先咽,后來平靜之后向行人訴說其因兵亂流落至此,至今仍然記得在長安城里淪陷的那三年的光景,視角由行人轉向秦婦。第二至七段秦婦敘述自己目睹黃巢軍攻占長安城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第八段至第九段,秦婦走出長安城只見人煙寥落,田園破敗,恰好路遇金天神,就“試問金天神”,而金天“無語愁于人”,接著金天神向秦婦講述戰后遭遇,視角又由秦婦轉向金天神。“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又將視角重新回歸到秦婦。第十至十一段,秦婦出楊震關過新安東,路遇老翁,老翁自述其本來家境殷實,因黃巢軍和官兵的搶劫搜刮才致“家財既盡骨肉離”,敘述視角由秦婦轉向老翁。第十二段開頭以“妾聞此老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兩句提示視角由老翁重新轉向秦婦,在秦婦敘述了自己的見聞以后,偶然聽到金陵客敘述戰亂時江南的景象“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賦稅如云送軍壘。”敘事視角又由秦婦轉向金陵客。最后視角再次回歸秦婦,她感嘆到奈何四海盡滔滔,江南卻“平如砥”。在這十二個段落中,敘述者先由行人轉向秦婦,再由秦婦轉向金天神,金天神又轉向秦婦,秦婦再轉向老翁,老翁轉向秦婦,秦婦又轉向金陵客,最后又由金陵客回歸到秦婦,敘述視角在有限視角之間不斷的轉換、敘述聲音的增加,拓寬了故事的橫剖面,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整首詩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愈發廣闊。
二、縱橫交錯的結構模式
中國詩歌的敘事傳統,從《詩經》之時萌芽,歷經漢代、南北朝的發展與推進,至唐朝時已日臻成熟。《詩經》中的敘事詩,諸如《衛風·氓》《大雅·公劉》《邶風·谷風》等篇,采用的多是中國最傳統的敘事方式,即按照事情發展的順序來進行。以《衛風·氓》為例,全篇以一名被棄女子的口吻順敘述說了其情變經歷和深切體驗。漢代時,涌現出了《孔雀東南飛》《上山采蘼蕪》《陌上桑》等膾炙人口的名篇,其敘事傳統較之前也有了明顯的不同,主要表現在跳出了縱向發展的結構,開始置入了生活的橫剖面。比如《孔雀東南飛》,雖然其全過程寫的是焦仲卿、劉蘭芝夫婦被迫分離并雙雙自殺的故事,但是作者有意選取了夫妻被迫分離、劉兄逼嫁、夫妻相約殉情的幾個戲劇性場景,通過幾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生活畫面生動刻畫出了焦劉夫婦、焦母以及劉兄的人物形象。敘事詩在唐代白居易手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不再拘泥于橫剖面式的結構,而是注重將情感揉入敘事詩故事之中,將情節和心理結合起來,用簡單卻飽滿的情節表現生活的縱向發展。韋莊在創作《秦婦吟》時進一步推陳出新博采眾長,他把漢代確立的橫剖面式的結構和白居易發展的縱向結構完美地結合起來,相互串聯,擴大了作品的內涵與外延。
盡管《秦婦吟》的敘述視角在有限視角之間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轉換,但是其轉換的結構基本沒有變,即甲與乙相遇,乙對甲訴說,乙的訴說內容包含著其他人物的敘述,但是乙的敘述始終是故事的主敘述。這也就涉及到故事的結構模式,即以秦婦為主的縱向結構和以其他人物穿插敘述的橫向結構交錯進行的結構模式。
作者首先安排行人與秦婦相遇,接著秦婦開始向行人訴說她在長安城淪陷三年的遭遇:廣明元年至中和三年三月黃巢軍攻占長安,自稱齊帝,三年之中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秦婦被迫嫁給黃巢軍人,僥幸保全一命,卻憂心忡忡不得安寧。她整日處在戒備森嚴的武器包圍里,每日餐食必有一味人肝膾,雖然掠奪的寶物雖多,卻非她喜愛。黃巢新朝廷中的官員大多蓬頭垢面,衣衫不整,臉上刺字雕花,象笏翻持,金魚倒佩,早晨上朝,下午酗酒。黃巢軍和官兵大戰以后,整個長安都城破敗荒蕪,腳下所踏盡是尸骨。官兵收復長安以后,秦婦走出長安行至華陰縣,只見金天神廟廟前古柏殘破,殿上金爐生暗塵。金天神向秦婦訴苦:自從黃巢起兵造反以來,天昏地暗,風雨烏黑。秦婦過新安東后,路遇老翁,老翁自述所受災難,黃巢軍和官兵所到之處,皆被搜刮掠奪,慘不忍睹。秦婦聽后淚如雨下,出門只見梟鳴,不見人跡,想再往東走,不知到何處是好,恰好有人從金陵來,說江南的風景大不相同,城池堅固,四郊無戰,官兵惠愛百姓如同子女。全詩采用較近乎小說的創作手法,通過秦婦形象的塑造、農民軍入城的鋪陳描寫,金天神的虛構、新安老翁的形容勾勒出一副宏偉壯闊的畫面。而主線便是秦婦的述說,秦婦所講之事簡單明了,不過是她在長安城淪陷三年的遭遇,但是詩人在她講述時又特意安排了金天神、老翁、金陵客的出場,他們分別述說了他們在戰亂時的不同情景,通過眾多人物的不同感受來表達相同的內容,即戰亂讓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秦婦所講的故事形成了全詩最初的敘述框架和縱向發展的主線,在這一框架下又有金天神、老翁、金陵客這些敘述者,他們的述說以及詩人對其他生活面的描寫形成了全詩幾條并列的橫線。這種橫縱交錯的敘事結構較之于單一的敘事結構無疑使作品的容量更大、包孕更廣,意味更長。
三、動靜結合的環境描寫
就在故事中的空間位置而言,環境分為靜態環境與動態環境。靜態環境指故事囿于基本固定的空間,人物在此范圍內活動;動態環境指故事中的背景處于不斷變動之中。靜態環境是故事的常見形態,大凡敘述某一特定地點的故事都是靜態環境,而動態環境有多種呈現方式,顯而易見的是故事中地點的變化,人物從一個地方轉向另一個地方。[3]163
《秦婦吟》著重環境氣氛的創造,全詩環境由動態轉為靜態,再由靜化動,動靜結合,形成了戰亂荒蕪的氣氛。先是以行人的眼光環顧洛陽城周邊,城外桃花似雪,人煙稀落,只見有一個婦人在樹蔭下歇腳。秦婦向行人講述她在長安城淪陷三年的遭遇,視線從行人轉向秦婦,隨著秦婦移動。秦婦講述三年前臘月五日早上,她打開了鏡盒,卻懶得梳頭,就獨自靠著欄干教鸚鵡說話,忽然看見門外塵土飛揚,接著又看見街上有人在打鼓。百姓們慌慌張張地跑出門來,上朝的官員也都趕回家來,還懷疑他們所聽到的消息不確,但是不一會兒黃巢軍就已經攻入,只見百姓們叫喚著東躲西藏,門外兵馬馳突,屋子里一片混亂。婦女和孩子們被擄掠燒殺,只留下一聲聲慘叫。黃巢軍攻入長安城,所到之處燒殺掠奪,秦婦眼中所見全是尸骨,耳中所聽盡是哭聲,當時慘不忍睹的畫面隨著秦婦的視線動態的呈現出來。接著,秦婦講述她被迫嫁給黃巢士兵后的生活情況,她整日被劍戟包圍,黃巢部隊里立過功的官兵臉上都刻有刺字雕花,大多衣衫襤褸,衣冠不整,有些頭發沒有留長,已戴上了簪子,三公捧朝笏常常是翻轉的,兩史佩戴的金魚常常是顛倒掛的。此時對兇神惡煞的黃巢官兵的描寫儼然已經脫離人物描繪而成為靜態環境的一部分,烘托出戰亂時代動蕩的氛圍。唐軍與黃巢軍交戰敗退以后,詩人用“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幾句帶我們環視了寂寥殘敗的長安城。過去的繁華的長安街,現在已全是麥苗,杏園中的花木、御溝兩旁的楊柳,都被人砍去只剩一片荒蕪。華美的屋宇不見蹤影,朱門甲第的富貴大戶破敗不堪。皇宮里的含元殿、花萼樓,已是荊棘叢生,任憑狐貍野兔去游走。皇宮貯藏珍寶的內庫,已被燒成灰燼;在天街上行走,腳下踏到的盡是公卿貴族的尸骨。從坊市到宮室,從樹木到建筑,滿眼所見,無一點舊時繁盛的蹤跡。詩人將戰后的荒蕪寓于動態的環境描繪之中,渲染出寂寥的氣氛。后來官兵收復長安以后,秦婦走出長安城,行至金天神廟前時,只見田園破敗荒蕪,廟前古柏樹都被砍光,僅馀殘蘗;殿上的銅香爐也已黯然失色,積滿灰塵。一種戰亂后陰冷恐怖的氛圍在殘敗的古柏樹上流露出來。環境描寫又由動態化為靜態。全詩環境描寫不斷的轉化,動靜的巧妙結合,生動揭示出戰爭的造成的家園荒蕪,人民困苦。
四、結語
《秦婦吟》誕生以后,民間廣為流傳,韋莊也因此被稱為“秦婦吟秀才”,與白居易的“長恨歌主”并稱佳話。后人也把《秦婦吟》與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北朝樂府《木蘭辭》并稱為“樂府三絕”。它用純乎寫實的手法,生動記載了歷史的滄桑巨變,其筆鋒之所及,涉及了封建官軍混戰與統治者內部矛盾。人民疾苦,生靈災禍,盡在紙上。凡刻劃處,皆力透紙背,描摹處,情態畢見。作為一首長篇敘事詩,它以不斷轉換的限知視角、縱橫交錯的結構模式、動靜結合的環境描寫,彰顯出了它作為敘事詩而具有的獨特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1]彭功智. 淺談我國古代敘事詩[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5(2):30—35.
[2]譚君強. 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胡亞敏. 敘事學[M].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曾思藝. 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試論《秦婦吟》的藝術成就[J]. 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5):74—77.
[5]胡根林. 唐代敘事詩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4.
On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Weizhuang 's Qinfuyin
ZHENG Yan-j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Qinfuyin is a long narrative poem of the Tang Dynasty important it constantly, conversion of the limited perspective, the description of structure arranged in a crisscross pattern combining static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narrative art from three aspects.
Qinfuyin; limited perspective; structural model;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I207.22
A
2095-7408(2017)04-0071-04
2017-04-11
鄭燕姣(1993— ),女,山西繁峙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