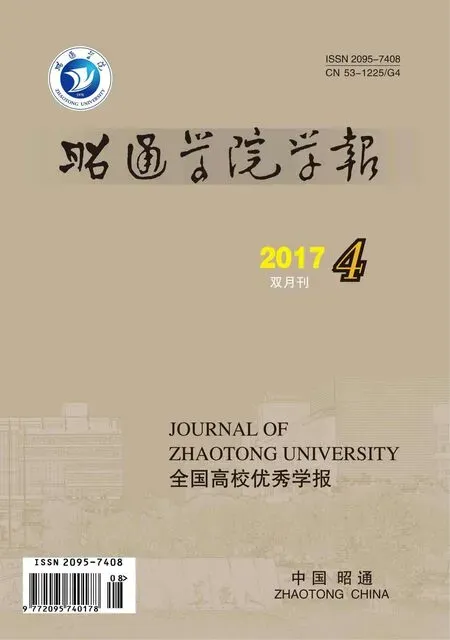論史鐵生散文的超越性美學
張祎楠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文學研究
論史鐵生散文的超越性美學
張祎楠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史鐵生用自己的生命體驗進行創作,將自己經歷苦難后悟出的哲理融于創作中,使得他的散文在質樸平淡的外表下卻蘊含著思辨的哲學氣息,他的這種個體性書寫為當代文學史開辟了新的一種散文書寫范式。在史鐵生散文的哲學敘事中,他總結出了每個人都會面臨的三種人生的根本困境,并給出了超越這些困境的方法。論文就是以史鐵生散文的人生困境為出發點,探尋其超越困境的根本方法,并試圖發現這種超越性的美學欣賞價值與意義。
人生困境; 過程論; 超越性
在中國當代散文創作中,史鐵生以自己的生命體驗為藍本進行創作,寫下他所悟出的生命哲學,這為當代文學史開辟了一種新的個體性的散文書寫范式。史鐵生正是以這樣的個體性書寫占有著一席之地,劉錫慶評價史鐵生散文時說:“他攀上了當代散文的巔峰”[1],這句贊譽就是最好的印證。在史鐵生的散文里,字里行間都是平和沖淡的味道,沒有玩略技巧之嫌,閱讀的舒適感極強,會給讀者猶如在聆聽一位有故事的人將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的感覺。史鐵生的散文除了“故事性”強以外,最重要的是還他對于人生的哲學的敘事,他將自己經歷苦難后悟出的哲理融于創作中,使得散文在質樸平淡的外表下卻蘊含著思辨的哲學氣息,這是他能攀上散文巔峰的關鍵因素。在史鐵生的人生哲理探索過程中,總結出了每個人都會面臨的三種人生的根本困境,人們如何面對這些困境,他給出的答案就是超越它們,超越的方法是享受過程。本文就是以史鐵生散文的人生困境為出發點,探尋其超越困境的根本方法,并試圖發現這種超越性的美學欣賞價值與意義。
一、三種人生困境
寫作和癱瘓,兩件對史鐵生人生有重大影響的事件都與他插隊經歷有關。史鐵生的插隊經歷是他日后創作的重要素材更對他的寫作心態和作品樣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后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后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后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著寫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么,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2]”史鐵生從小就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下鄉期間勞苦的工作使他因脈管炎而癱瘓,多方求醫未果,給他身體和心理的帶來巨大傷痛。
史鐵生過去的那些經歷,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不少的精神財富,是形成他生命哲學的源泉。癱瘓后的史鐵生面臨著生活窘迫和生命危機,但他頂住了來自身體殘疾和精神奔潰的雙重壓力,在直面自我苦難時悟出了生活和生命的真諦,并在創作中把他理解的人生哲理書寫下來。在《自言自語》里史鐵生就總結出了人生的三種根本困境:“第一,人生來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來注定是活在無數他人中間并且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這意味著孤獨。第二,人生來就有欲望,人實現欲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他欲望的能力,這是一個永恒的距離。這意味著痛苦。第三,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3]169
二、困境的超越
史鐵生提出的三種人生根本困境,他一開始認為是上帝給我們的折磨,可是后來發現我們都理解錯了。上帝給我們設置三種人生困境其實是給我們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困境是人們獲得歡樂和人生意義的前提條件,我們只有不斷地超越上帝設下的三種困境,才能在這一過程當中體會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史鐵生正是深深領悟到了這一超越的過程與結果的意義,于是在他的散文中,才有了這種超越性美學的存在。
史鐵生對于三種根本困境的超越,首先表現為對自身殘疾的超越,更進一步來說是對于自身肉身的一種超越。史鐵生面臨的第一關就是身體的殘疾,這是阻礙他認知世界的關鍵因素,如何打破殘疾的心理障礙,是他超越的第一關卡。這也是他比大多數常人要多出來的一關。完成這層超越,他就要和常人一樣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孤獨。這種孤獨更多來說是指精神層面上的,這就需要我們超越肉體凡身,直抵精神靈魂的深處,以一種平和的姿態去超越藏在靈魂深處的孤獨。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正是在孤獨的環境下創作出來的,當初發現這個人跡罕至的地壇,對于他來說是欣喜的,因為在這里他能夠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可以用心去思考問題和理解生命。在史鐵生眼里,這個園子仿佛是為他而準備的,在那里等了他幾百年,就如他所說這樣的寧靜之地,像是上帝為他的苦心安排。像是上帝為了補償他癱瘓的病痛,這地兒為他而留,讓他能在此地認真的思考人生,升華自己的精神靈魂,在飽嘗孤獨之苦后理解它,并超越它。對于每個生命個體來說,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我們有足夠的人生閱歷和耐心才能完成,適應孤獨是我們每個人的必修課。其次,是對于世俗欲望的超越。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時無刻都充滿欲望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合理的欲望是值得肯定的,那是我們不懈追求的力量源泉,這樣的追尋過程會使得我們的人生更加有意義;而腐敗墮落的欲望是可怕的,它會讓我們利欲熏心、迷失自我,甚至有可能會毀了我們自己。對于欲望史鐵生并不是排斥的,他所謂的欲望困境的超越也不是對欲望的否定,而是想讓我們正視自己的欲望,努力去追尋自我合理的欲望,去享受這一追尋的過程,在追尋的過程中實現精神與靈魂的升華,這才是他要達到的對世俗欲望超越的效果。最后,是要對此生有限的超越,即完成對死亡困境的超越。面對死亡這類沉重的話題,我們常常采取避而不談的態度,因此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的直面死亡,也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它。史鐵生在多次想輕生之后,慢慢頓悟了生死問題,這是他孤獨的在地壇中思考的結果。正如他理解的那樣: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它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那么我們就不必再受這個問題的困擾,轉而去體驗生活給予我們的歡樂和苦難,這些經歷是打磨我們靈魂最有效的方式,我們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對死亡困境的超越。只要精神和靈魂不死,就是永生,這是史鐵生想要告訴我們的。
從對三種根本困境的超越中,我們能夠總結史鐵生給出的根本方法:用過程取代目的。這種“過程論”的方法在史鐵生散文《好運設計》中做了最精彩的闡述:“過程!對,生命的意義就在于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虛無你才能夠進入這審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絕望你才能找到這審美的救助。”[3]53史鐵生之所以悟出了“生命的意義在于過程”這一命題,正是因為其長期的殘疾造成的生存的臨界體驗,而過程正是所有生命在面臨挫折和苦難時的一種獨特的生命在場方式和生存方式[4]。史鐵生用他自己的切身體會,為我們記錄下了他人生過程的精彩,讓我們看到了他超越困境所做出的努力,在欽佩他的同時也震撼著我們每一位讀者的心靈。他為我們提供的“過程論”,是希望我們在面對困境的時候,在超越困境的同時完成自我的超越,這是一種精神的超越,更是人類自我靈魂的超越。在超越自我的這段距離間,就是所謂的過程。如若我們更注重目的,容易使得我們在過程中迷失心智,最終也難以達到目的,反而陷入到一種絕望空虛的境地中去。所以,在面對困境時,我們不妨像史鐵生一樣,學會享受過程而不去更分注重目的,這樣我們就更容易超越苦難、超越困境、超越自我,最終完成對精神靈魂的救贖,充分實現自我的人生意義與價值。
三、超越性的意義
史鐵生散文中具有的超越性理論,為我們解讀他的散文作品提供了一種研究視角。在閱讀史鐵生的散文過程中,他的文字常常會引起我們的思考。他喜歡“設問模式”的寫作,自己提出問題,然后再做自我解答,讀者往往會不知不覺就被帶入思考,參與到文本對話當中去。史鐵生對于困境超越的探討,就是在這種寫作模式下完成的,這樣讀者在閱讀時就會被帶入到這種探討對話中,使讀者更能體會和理解這種超越性,并對照自我的生活狀況做出反思;另外,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從史鐵生的親身經歷中看到超越性的價值,還能從中看到一個靈魂的升華過程,讓自己在閱讀審美中獲得心靈的震撼。因此,這種超越性的意義,更多的是體現在它的教育意義和審美價值之上。
超越性的教育意義十分明顯。我們在閱讀史鐵生的經歷時,不免會對其超越困境所做的努力給予贊賞,他在文中也已經給了我們超越困境的方法與答案,親自為我們做了一次示范。所以在我們審視到自己身上時,也就學會像史鐵生一樣去努力克服挫折和苦難,學習他享受這一努力的過程而不過分注重目的,這種模仿的方式就是超越性的教育意義。史鐵生散文超越性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審美價值上。這種審美的價值,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之上,而是要觸及到我們靈魂的深處。那么,這樣的審美該如何獲得呢?有學者給出了答案:審美的確認,使得對困境的抗爭不再顯得那么現實和現世,它強調,從精神的彼岸反觀創造生命的此岸過程,自會獲得一種欣賞性的意義[5]。這段論述高度總結了史鐵生超越性審美價值,再一次強調了“過程論”是獲得審美的最本質條件。其實,史鐵生的過程論最初是建立在目的的破滅之上的。在史鐵生看來,目的的虛假使他陷入空虛和無聊,無以為繼的他只能轉而向過程尋求安慰,并最終在過程中達到了審美性的滿足[6]。因此,不僅僅是史鐵生,對于我們而言,欣賞過程也是我們超越困境,完成靈魂升華,追尋真正人生價值的過程,我們在對文本審美的同時也是在對人類自我超越精神的審美。這應該才是超越性意義的價值所在。
在當今紛繁復雜、浮躁不安的社會現狀下,我們常常被壓的喘不過氣來,史鐵生提出的人生的三個根本困境似乎更加突出了。那么,如何面對這些人生中的障礙,史鐵生在散文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過程論”依舊沒有過時,它仍然是我們超越困境,完成靈魂的升華,找到人生真正的價值與意義的方法。史鐵生雖已經離去,可是他為我們留下的精神之燈依然照耀著前路。
[1]劉錫慶. 他攀上了當代散文的巔峰:史鐵生散文成就之我見[J]. 文藝報,2002,(8).
[2]史鐵生.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J].小說選刊,1983,(7).
[3]史鐵生. 史鐵生散文選[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陳玲娜. 史鐵生過程論思想概觀[J]. 大眾文藝,2010,(06):57-58.
[5]王 堯. 生命由夢想展開——論史鐵生散文[J].當代文壇,1996,(2):29-32.
[6]汪雨萌. 史鐵生研究綜述[J]. 當代作家評論,2012,(4):160-169.
Transcendence Aesthetics on Shi Tiesheng's Prose
ZHANG Yi-nan
(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Shi Tiesheng write with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adding he realized own philosophyafter suffering into creation, making his prose in plain appearance but contains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his individual writing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stablishes a new kind of prose writing paradigm.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hi Tiesheng's Prose narrative, he summarized the everyone faces three life predicaments, and gives the way beyond these. This article is base on life predicament of Shi Tiesheng's Prose, exploring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of beyond the difficulties,and try to fin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meaning.
life predicament; Researcher; transcendence
I207.6
A
2095-7408(2017)04-0089-03
2017-05-11
張祎楠(1991— ),男,彝族,云南楚雄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