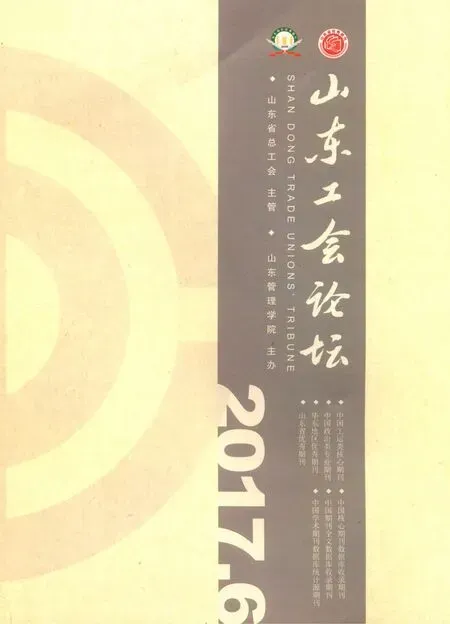日本勞動關系的新自由主義調整及其影響
楊洪曉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100048)
【勞動關系研究】
日本勞動關系的新自由主義調整及其影響
楊洪曉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100048)
二戰(zhàn)后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日本形成了以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yè)工會為特征的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上世紀90年代經(jīng)濟泡沫破滅,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普遍流行的大背景下,日本冒然對勞動關系領域進行了廣泛的新自由主義調整。然而,這一調整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它不僅對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形成了巨大沖擊,加速了全球化時代“強資本弱勞工”趨勢的發(fā)展,其長期的、潛在的對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差距拉大的影響更需要引起重視。日本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的程度和影響仍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日本;勞動關系;新自由主義
上世紀90年代是日本經(jīng)濟和勞動關系調整演變的重要轉折期,在經(jīng)濟泡沫破滅之后,日本經(jīng)濟陷入長期低迷,經(jīng)歷了“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在勞動關系方面,日本采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對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進行了大幅調整。對于日本勞動關系調整的性質和方向,即由傳統(tǒng)的協(xié)調型勞動關系向新自由主義的調整,學界沒有爭論,但對調整的程度和產生的影響卻存在不同的認識。大部分的學者認為,經(jīng)過持續(xù)的政策調整,日本已放棄了傳統(tǒng)的以終身雇傭為基礎的勞動關系模式,一種以自由選擇和靈活就業(yè)為基礎的新的勞動關系模式正逐漸確立起來。但也有少數(shù)學者認為,日本勞動關系目前還處在調整演變中,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在許多領域仍然占據(jù)主導地位,尤其從比較的角度看,日本仍然明顯區(qū)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不宜過早做出結論。勞動關系不僅是反應國家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狀況的重要“晴雨表”,同時也對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秩序具有直接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調整,使日本的勞動關系狀況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既影響到了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的狀況,也對日本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變化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隨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jīng)濟危機的到來,曾經(jīng)一度輝煌了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神話也因此而破產,各國形成了一股對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的潮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對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調整及其影響進行重新審視,具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義。
一、日本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形成與特征
日本的現(xiàn)代化始于明治維新,在明治維新后幾十年的發(fā)展中,日本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勞動關系模式。戰(zhàn)前日本的勞動關系即已表現(xiàn)出明顯的家族主義特點,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加強,勞動關系也逐漸被壓抑扭曲。
二戰(zhàn)結束后到50年代中期經(jīng)濟起飛前,日本經(jīng)歷了一段勞資沖突對抗非常激烈的時期。當時,日本的工會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工會組織的罷工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對企業(yè)生產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很大沖擊。1946年2月,日本僅有675個工會,會員人數(shù)不足50萬人,但到1948年7月,工會數(shù)量已迅速增加到33940個,會員人數(shù)也迅猛擴張到663萬多人[1](p62-68)。當時的工會多以產業(yè)工會的形式組建,工會組織同心同德,具有很強的戰(zhàn)斗力,工會組織的罷工活動多數(shù)情況下都取得了勝利,比如,當時由電氣產業(yè)工會確立的以保障生活為核心的“電產型工資”,即是當時工會斗爭獲得的突出成果。工人的組織和抗議活動還獲得了當時占領日本的美國軍事當局的支持,美國為避免日本重新走上軍國主義老路,對日本進行了廣泛的民主化改造,扶持勞工、賦予工人更多的民主權利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工會活動得以展開和獲得成果的重要條件。廣泛的罷工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水平和社會地位,但是頻繁罷工也對企業(yè)的正常生產和社會秩序帶來很大影響,日本政府開始考慮限制工人罷工的權利。特別是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美國軍事當局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了抵消和限制共產主義的影響,美國放棄了對工會組織的支持,轉而扶持企業(yè)以對抗工人,在此背景下,日本左翼工會運動陷入低谷,勞資關系由沖突開始走向緩和。
從1956年開始,日本經(jīng)濟步入高速增長階段,一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為止,日本經(jīng)濟連續(xù)18年保持了年均增長率超過10%的發(fā)展速度,創(chuàng)造了舉世矚目的“日本奇跡”。在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同時,日本政府還注重改善民生,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7年的時間提前實現(xiàn)了國民收入增長一倍的目標。在經(jīng)濟高速增長期里,日本實現(xiàn)了華麗轉身,經(jīng)濟總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收入也躋身于發(fā)達國家先進行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大幅改善了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工人階級的地位和生存狀況有了巨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保障,工人越來越安于現(xiàn)狀而不再仇視資本。此前激烈的勞資對抗所付出的沉重的個人、企業(yè)和社會代價,也使政府和社會都在尋求避免產生新的對抗。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勞動關系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從對抗走向對話,從沖突走向協(xié)調,確立起以對話、協(xié)調為主要特征的勞動關系模式,這就是日本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模式。這一勞資關系協(xié)調模式成為“日本模式”或“日本經(jīng)營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成戰(zhàn)后經(jīng)濟長期高速發(fā)展的“日本神話”的重要基礎。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終身雇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講求年功序列和建立企業(yè)工會。
所謂終身雇傭制,又稱正式工制度,是指工人一旦被企業(yè)錄用為正式職工就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此過程中企業(yè)不能隨意解雇職工,工人也不會輕易跳槽,除非企業(yè)陷入極度的經(jīng)營困難,或者職工無法繼續(xù)在當前的企業(yè)工作。終身雇傭并不是在合同中明文規(guī)定的,而是日本社會形成的一種默契或慣例。終身雇傭的效果是兩方面的,從經(jīng)營者方面說,“日本企業(yè)除非在面臨倒閉或其他危機情況下是絕不會解雇員工的。當一個企業(yè)被迫大量裁員時,這個企業(yè)的經(jīng)營者便會成為社會輿論抨擊的目標,他們被認為是不負責任”。“從員工的角度來說,通常認為一再調換企業(yè)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跳槽’常常被看成是無法勝任工作,或者在心理上有缺陷而無法與同事相處。”[2]終身雇傭制的前身是20世紀初日本重化工業(yè)采取的“童養(yǎng)工”制度,在二戰(zhàn)后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終身雇傭成為日本企業(yè)廣泛采用的做法。終身雇傭制的形成,是企業(yè)經(jīng)營者面對工人斗爭的壓力主動調整的結果。在戰(zhàn)后激烈的勞資對抗中,解雇工人是誘發(fā)沖突和全面罷工的重要原因,雇主由此認識到不能輕易解雇工人,相比解雇工人造成罷工的損失,終身雇傭更為可取,而且由此所產生的成本也可以通過一些辦法彌補。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形勢也促成了終身雇傭制的普遍采用,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增加了企業(yè)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同期日本的人口生育率卻出現(xiàn)了下降趨勢,至1963年,日本第一次出現(xiàn)了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1](p62-68)。在這樣的情況下,終身雇傭對于企業(yè)的生產經(jīng)營來說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于是日本企業(yè)普遍采取了終身雇傭制的做法。
所謂年功序列制,是指工人的待遇會隨著工齡的增長而增長,工人在企業(yè)工作的時間越長,越能獲得更好的待遇,包括工資水平和職務地位。工人在企業(yè)工作的“年資”,成為衡量工人工資水平和職務晉升的最主要依據(jù)。年功序列制的形成與終身雇傭制有著密切的關系,是為了解決終身雇傭之后,可能產生的用工成本增高和生產價值減少以及便于加強管理而采取的做法。年功序列制具有講求資歷的一面,這容易使人對其形成刻板印象,認為年功序列就是“論資排輩”,年輕人在其中永無出頭之日。這是對年功序列制的一個誤解,因為它并不是只看資歷,也講能力和貢獻,如果某個員工具有突出的能力或做出重要的貢獻,他就會脫穎而出獲得越級對待,如果大家的能力水平和貢獻差不多,這時候年資就成為主要的參考指標;另一方面,在年功序列制里,由于企業(yè)嚴格的學習培訓和任用制度,更老的資歷其實往往不只是更長工齡,也代表著更高的能力和更多的貢獻,如果某位更長工齡的職工沒有表現(xiàn)出更強的能力和貢獻,他會覺得很沒面子,這會迫使他更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年功序列制沒有弱化工人之間的競爭,相反,某種程度上它使工人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因為誰都不想落后,也只有比別人表現(xiàn)更好,才能獲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地位。
與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相應,日本的工會組織采取了以企業(yè)工會為主導的形式。所謂企業(yè)工會,是指以企業(yè)為單位組織工會,每個企業(yè)都會組織成立一個工會,該工會包括了企業(yè)中的所有職工,其中也包括白領和高級管理人員。企業(yè)工會模糊了普通職工和管理者之間的區(qū)別,不單純是一個職工利益的代表機構,它同時也參與企業(yè)的管理和運營,與資方之間進行密切的協(xié)商與合作,企業(yè)工會本身就是企業(y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企業(yè)和企業(yè)工會之間的關系不是對抗性的,而是相互信任、緊密合作的關系,企業(yè)將工會看作是自身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賦予企業(yè)工會相當?shù)臋嗔Γ髽I(yè)工會也將自己的利益和前途與企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站在企業(yè)管理的角度考慮如何將企業(yè)做得更大更好,這是一種“共同體”式的勞動關系。企業(yè)工會是日本企業(yè)運營的一大特點,其最主要的優(yōu)點在于它幫助企業(yè)營建了一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協(xié)調的勞動關系,最大程度的減少了勞資之間的糾紛。企業(yè)工會的成立是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確立的自然結果,三者共同塑造了日本企業(yè)中和諧的勞動關系,日本人常常將他們的企業(yè)看作是“家”,這是日本企業(yè)比較穩(wěn)定并富有競爭力的重要原因。
為了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與問題,日本企業(yè)確立了勞資協(xié)商制度和集體談判制度,在企業(yè)雇主和工會組織之間建立了經(jīng)常性的溝通渠道,由勞資雙方對企業(yè)的生產經(jīng)營、日常管理以及工人的工資待遇進行協(xié)商,這大大減少了日本企業(yè)勞資沖突的數(shù)量。此外,日本還設立了勞動委員會來專門協(xié)調處理勞動關系爭議。因為有著相對完備的勞資關系處理機制,再加上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yè)工會制的實施,因而在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時期,日本工人罷工的數(shù)量出現(xiàn)了大幅下降,即使有罷工也都是比較和平的罷工,像二戰(zhàn)后初期那種強烈的罷工斗爭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傳統(tǒng)的以協(xié)調對話為特征的勞動關系模式,不僅是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的產物,本身也對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日本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挑戰(zhàn)與調整
日本傳統(tǒng)的協(xié)調型勞動關系模式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受到了挑戰(zhàn)。由于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的島國,其經(jīng)濟的發(fā)展高度依賴于對外貿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發(fā)生,給日本經(jīng)濟帶來了巨大壓力,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年代由此結束。由石油價格的猛漲所引起的通貨膨脹,不僅大幅提高了企業(yè)的生產成本,削弱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且使工人的工資收入在物價上漲面前嚴重縮水,勞資雙方的關系因此而緊張起來。然而,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沒有想過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之外的其他選擇,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談判協(xié)商后,勞資雙方最終達成妥協(xié)以共渡難關,工會愿意采取合作態(tài)度,接受緩慢的工資增長速度,以支持企業(yè)的生產經(jīng)營;企業(yè)則繼續(xù)實行終身雇傭制,保障工人的日常生活。在雙方的合作下,日本最終渡過了經(jīng)濟難關。這場危機暴露了日本傳統(tǒng)模式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更主要的是顯示了日本模式所具有的適應能力,這也是日本傳統(tǒng)模式優(yōu)勢在國際社會上的一次顯示,日本模式由此收獲了更大的美名。靠著和衷共濟的能力,日本經(jīng)濟走出了石油危機的陰影,走向更大的國際舞臺。
促使傳統(tǒng)模式繼續(xù)下去的還有這一模式本身名聲的壓力。在20世紀60年代的快速增長中,日本模式已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滯漲危機中,但是日本卻通過勞資妥協(xié)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的平穩(wěn)著陸和重新發(fā)展。傳統(tǒng)的以協(xié)調合作為特征的勞動關系模式,被看作是日本發(fā)展的關鍵,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yè)工會制度,更是被國際社會冠以“三大神器”的美名。這一國際聲譽助長了日本模式的持續(xù)性,使日本即使面臨一些危機也難以摒棄這一傳統(tǒng)的做法,所謂的盛名有時候也會是一種負擔。比如,在1985年廣場協(xié)議簽訂后,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在出口困難的情況下,日本仍然堅持了傳統(tǒng)的終身雇傭制。
為了抵消廣場協(xié)議的消極影響,以及創(chuàng)造更多的“日本第一”的神話,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采取了一些刺激經(jīng)濟的做法,如放松金融管制和實施緩和的貨幣政策等。這些做法在短期內刺激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但也形成了嚴重的經(jīng)濟泡沫,其典型代表就是股票和房地產行業(yè)的快速上漲。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jīng)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經(jīng)濟陷入長期低迷,經(jīng)歷了所謂“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眾多的企業(yè)在這場長期的危機中面臨艱難的轉型。面對低迷的經(jīng)濟形勢,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模式背負了越來越多的批評,被認為是削弱企業(yè)競爭力和導致經(jīng)濟不景氣的主要因素。許多企業(yè)縮小了享受終身雇傭待遇的正式職工的范圍,積極利用外部勞動力市場,以節(jié)省企業(yè)的人力成本和提高就業(yè)的靈活性。
在工資構成方面,改變過去過于重視年資的情況,突出“能力主義”的原則,更加強調能力和業(yè)績在工資構成中的比重。1995年,日本最主要的企業(yè)家組織“日本經(jīng)營者團體聯(lián)盟”,發(fā)表了題為《新時代的“日本式經(jīng)營”——挑戰(zhàn)的方向和具體措施》的重要報告,提倡企業(yè)不再拘泥于傳統(tǒng)的雇傭習慣,大膽地使勞動力彈性化和流動化,從而削減人工費用,降低企業(yè)的成本負擔。
面對持續(xù)低迷的經(jīng)濟狀態(tài),日本政府也放棄了對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堅持,開始進行積極調整改革。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宏觀政策調整的主要特征是,適應全球新自由主義調整的主流趨勢,對勞動關系進行去管制化的自由化調整。有學者將20世紀90年代經(jīng)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新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調整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結構調整”向“結構改革”過渡的時期(1986-1995年)。1986年,中曾根內閣確立了通過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理”擴大內需的政策。1993年成立的細川內閣對94個項目放松管制,拉開了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序幕。第二個階段是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框架形成時期(1996-2000年)。1996年成立的橋本內閣繼續(xù)把放松管制作為核心政策,并制定了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內容包括:促進國內勞動力自由流動、促進企業(yè)競爭、縮小行政干預經(jīng)濟的范圍、減少政府對社會福利的負擔比例等。第三個階段是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激進時期(2001-2006年)。2001年成立的小泉內閣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結構調整,除了鼓勵企業(yè)兼并和重組之外,對公共部門如道路公團和郵政事業(yè)等進行了民營化,改組、合并了政策性金融機構[3]。
經(jīng)過這樣一些調整改革之后,新自由主義的做法在日本逐漸站穩(wěn)了腳跟,對日本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戰(zhàn),新自由主義改革在釋放某些企業(yè)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日本勞動關系方面的重要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用人制度發(fā)生重大改變。據(jù)統(tǒng)計,正式員工占企業(yè)雇傭人員比率從1984年的74.9%下降至1992年的72.4%[1](p62-68)。企業(yè)越來越多地使用勞務派遣工、小時工等非正規(guī)就業(yè)者。日本政府也頒布政策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鼓勵勞務派遣的做法。1986年出臺的《勞動者派遣法》只允許13類職業(yè)采用勞動派遣制度,1994年經(jīng)修訂后將勞動派遣的范圍擴大到26類職業(yè),2003年又規(guī)定勞動派遣的期限可由1年延長到3年。2015年的修訂做了兩個重要修改,一是廢除同一崗位使用勞動力派遣人員最長3年的使用年限,二是取消了26種特殊勞動力派遣的規(guī)定。這一修訂案事實上完全放開了企業(yè)對非正式用工的限制。企業(yè)的工資體系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主要的改變是從年功序列制改為績效薪酬制,能力績效成為衡量工資水平高低的主要標準。“年薪制的登場意味著劃定工資的時間標準從終身制改為年度制,與日本原有的工資體系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因此,年薪制若能普及,說明日本工資體系已脫胎換骨。”[4]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調整,改變了企業(yè)和職工之間的關系,他們不再是命運相連的“共同體”,而是有期限的雇傭勞動關系,員工對企業(yè)的忠誠度的變化深刻反映了這一點。在1995的一項調查中,只有20.6%的受訪者認為將來公司會照顧自己,只有17.8%的人認為辭職是對公司或老板的背叛[5]。
三、日本勞動關系調整的新自由主義背景
日本20世紀90年代對勞動關系的調整,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這兩股潮流對日本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模式形成了很大挑戰(zhàn),日本政府所進行的改革調整相當程度上是對這兩股潮流挑戰(zhàn)的回應。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兩股潮流來說,它們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發(fā)展的主流就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推動了以超越國家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的發(fā)展,而新自由主義也正是借著全球化的潮流而擴展到全世界,建立起其“普世性”的神話。因此,這兩股潮流雖然不同,但在當時卻形成某種“合流”。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全球化的發(fā)展已成洶涌之勢,任何國家都無法阻擋全球化的步伐。全球化的發(fā)展既是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追逐剩余價值的結果,也是新的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術支持推動的結果。全球化打破了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的界限,要求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實現(xiàn)生產資料在全球的最優(yōu)配置。全球化的發(fā)展深刻改變了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的特征,也加強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然而全球化的發(fā)展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挑戰(zhàn),擴大了各國所面臨的風險,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群體在全球化中的風險和受益情況是不同的。從勞資關系的角度說,全球化所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便利了資本的國際化遷移,而勞工卻不能實現(xiàn)自由的國際遷移,其結果就是導致了“強資本弱勞工”的基本趨勢和格局。日本傳統(tǒng)勞動關系在全球化中所經(jīng)受的挑戰(zhàn)尤大,因為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講究的是終身雇傭和按資晉升,這雖然在穩(wěn)定勞動者隊伍、促進勞資協(xié)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卻是與全球化所要求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相悖的,也不符合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原則。在全球化的沖擊面前,日本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必然要做出調整。
在全球化大行其道的同時,基于美英國家經(jīng)驗的新自由主義也獲得了廣泛的傳播。新自由主義最初是美英國家為應對“滯漲”危機而采取的一套做法,其核心是去除國家管制,以私人市場為核心調整經(jīng)濟結構和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在新自由主義做法的刺激下,美英國家終于走出滯漲危機,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由于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美國于是利用其超級大國的影響力,在國際上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塑造新自由主義為全球通用的“普世價值”,甚至通過附加條件的貸款方式強迫其他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舉措。新自由主義在理念上看起來很正確合理,許多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再加上美國的大力宣傳鼓動,新自由主義的“普世性神話”于是樹立起來,這使更多的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是“三化”,即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實質是“去國家化”,將國家所有的產業(yè)交給私人接管和經(jīng)營,因為私人經(jīng)營比國家經(jīng)營更具有效率;市場化即由市場衡量一切,國家大幅度退出經(jīng)濟和社會領域,將諸多的職能交由市場來實現(xiàn);自由化就是減少政府管制和干預,讓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新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色彩,信奉私人市場的自動調節(jié)作用,而不相信國家的干預和調節(jié)作用,主張將國家從市場中驅逐出去。新自由主義的流行,是對二戰(zhàn)結束后各國廣泛采取的以國家干預為特征的凱恩斯主義的逆反,反應的是保守的自由市場派的重新得勢。新自由主義的經(jīng)驗明顯來自于傳統(tǒng)的以私人市場為核心的美英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具有效果的國家也多是與美英文化類似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然而,在文化背景差異較大的國家里,新自由主義的實施效果卻并不理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使拉美經(jīng)濟跌入動蕩。對于英美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實施的效果也并不都是好的,短期內它使英美經(jīng)濟走出滯漲重新獲得發(fā)展,然而在長期性上,它卻損害了勞工群體的利益,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為今后經(jīng)濟危機的爆發(fā)和社會的不安積蓄了動力。
日本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發(fā)展方法和勞動關系調整方法,實際上與新自由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傳統(tǒng)方法更為強調的是廣泛的公私合作,既重視市場的基礎調節(jié)作用,又重視政府的計劃和干預作用,強調政府和民間的積極合作,而不是單純依靠私人市場。日本經(jīng)濟在與美國簽訂廣場協(xié)議后,已然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經(jīng)濟面臨嚴重下行壓力,日本政府為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采取了一些短期做法,這些做法造成了嚴重的經(jīng)濟泡沫,日本經(jīng)濟在泡沫中達到了繁榮的頂點,舉國一片興奮。然而,繁華的背后掩蓋著嚴重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jīng)濟破滅之后,日本政府和企業(yè)無法一下子接受現(xiàn)實,他們開始變得過于悲觀,將問題歸咎于傳統(tǒng)勞動關系使日本企業(yè)背負的壓力太大,無法有效提高競爭力。這時候,由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正在建立起來,日本以一種急迫的態(tài)度,在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削足適履地學習和引進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勞資關系模式,對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進行了不切合本國實際的西方式調整。正是這樣的調整改革導致日本的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勞動關系模式隨之逐漸成形。
四、日本勞動關系新自由主義調整的影響與評價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對日本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某種程度上瓦解了傳統(tǒng)日本模式的基本特征,大部分的學者認為經(jīng)過改革后,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已經(jīng)不復存在,日本正在建立起新的勞動關系模式。新自由主義改革對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多樣化就業(yè)政策的實施和放松管制政策,在一定范圍內瓦解了傳統(tǒng)的終身雇傭制度,動搖了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的基礎。在改革調整過程中,日本企業(yè)為節(jié)約人力成本,大幅壓縮了終身雇傭的正式工的使用范圍,采取靈活就業(yè)方式,更多從外部勞動力市場招募人才,這一做法宣告終身雇傭制度事實上的破產。
第二,成就主義導向的工資制度或者說績效工資制的引進,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傳統(tǒng)的年功序列制。20世紀90年代,為抑制工資的上漲和提升企業(yè)競爭能力,日本企業(yè)廣泛地采用西方的績效工資制度,將員工的工資主要建立在個人能力和工作成績上,而不再是原來的年資上,這一做法的結果就是徹底終結了原來的年功序列制。年功序列制的瓦解也與多樣化就業(yè)方式有關,年功序列只適合企業(yè)終身雇傭的正式工,對靈活就業(yè)人員則必須提出一種新的工資衡量方式,這是年功序列制遭受的一大沖擊。
第三,新自由主義改革嚴重削弱了企業(yè)內部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越來越衰弱。新自由主義改革對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帶來了巨大沖擊,工會組織工作難度加大,終身雇傭制度的廢除和靈活就業(yè)的實現(xiàn),使工人內部發(fā)生了相當大的分化,彼此之間難以建立起共同認同感,這使工會難以有效地將不同工人召集到自己旗下。另外,工會在集體談判中的作用也受到嚴重削弱,無法再通過談判或罷工的方式有效地實現(xiàn)工資增長目標。
第四,就勞資雙方力量對比而言,新自由主義調整加速了勞工力量的衰弱和資本力量的強勢,進一步促成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總體而言,勞工力量的衰弱是全球化發(fā)展所帶來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是資本“用腳投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是,日本政府所進行的人為的政策調整卻加大了這一邏輯的效果,使資本更強而勞工更弱。面對全球化發(fā)展所帶來的“強資本弱勞工”趨勢,政府的作用本應是“扶弱抑強”而不是“扶強抑弱”,應積極維護勞工的合法權益,避免他們遭受更大的損失,而不是為資本的強勢提供更多的支持。從公平與穩(wěn)定的角度看,長期勞工權益受損的結果必然會拉大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進而對社會的公平和穩(wěn)定產生消極影響。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調整中,日本政府的著眼點卻更多的放在了資本一邊,通過解除政策管制和增加市場流動性的方式,日本政府為資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活動的機會。去除市場管制、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的福利水平、大規(guī)模的私有化,這些做法都助長了資本的強勢和削弱了工人的力量。日本勞工力量在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后呈現(xiàn)出進一步衰弱的趨勢,突出表現(xiàn)在工會組織率和員工入會率的“雙低”上。1995年日本工會的組織率為23.9%,到2010年工會組織率進一步下降到18.5%,而在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年代里,工會組織率長期維持在35%左右。從人員的組成來說,工會所吸納的會員數(shù)量也在持續(xù)下降,1995年工會會員數(shù)量是1261.4萬,而到2010年這一數(shù)量減少到1000萬[6]。與工會組織率的下降相關,工會的社會影響力也在下降,這突出表現(xiàn)在“春斗”作用的逐步縮小上。“春斗”作為日本富有特色的產業(yè)集體行動,始于1956年,是工會通過集體罷工方式迫使企業(yè)增長工資的行動,以后成為慣例。在日本經(jīng)濟高速增長時期,春斗的效果非常顯著,每年通過春斗實現(xiàn)的名義工資增長率都在20%以上。但從石油危機發(fā)生之后,春斗的效果也隨之下降,通過春斗獲得的增幅降至10%以下。在20世紀90年代經(jīng)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春斗的作用進一步縮小,1992年降至5%以下,2002年之后,春斗的效果進一步降低至2%以下。工會組織現(xiàn)在對于春斗的效果已經(jīng)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春斗的內容也從工資增長的單一目標改為以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并重,而且斗爭的方式盡量緩和、平穩(wěn),極少使用罷工等強制性方式。工會已經(jīng)毫無疑問的衰落了。
第五,從其實際實施效果看,除了帶來短暫的、局部的經(jīng)濟復蘇之外,其長期的、潛在和消極的影響更不可忽視,日本不僅沒有從危機中走出來,反而陷入長期的停滯和蕭條中。新自由主義調整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包括但不僅限于失業(yè)率上升、收入差距擴大、國內總需求下降、勞動者對企業(yè)的忠誠度下降、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產品質量和國際競爭力下降等。首先,大量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和大量解雇工人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使日本經(jīng)歷了從零失業(yè)到持續(xù)4%以上失業(yè)率,如果不考慮某些形式的“靈活就業(yè)”,其失業(yè)率還會更高。伴隨失業(yè)或半失業(yè)而來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失業(yè)人員的貧困化自不必說,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人員工資待遇與正規(guī)就業(yè)人員相比常有很大的差距,而且非正規(guī)就業(yè)人員的工作也是缺乏保障的,隨時都面臨著被解雇辭退的風險。績效工資制的引進也拉大了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更顯著的貧富分化。日本社會的一個總體變化趨勢是,財富傾向于向占人口更少的一小部分群體集中,而相當一部分群體收入?yún)s有下降的趨勢,社會貧困人口的總量在增加[7]。其次,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瓦解,大大降低了勞動者對企業(yè)的忠誠度,工人無法將精力集中在扎實的工作上面,這嚴重地侵蝕了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導致產品質量和企業(yè)競爭力的下降。例如,素來以創(chuàng)新能力強和產品質量高著稱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近年來因為產品質量問題引發(fā)的召回事件越來越多,其原因正是與績效工資所導致的急功近利的設計,以及為節(jié)約生產成本而大量使用非正規(guī)就業(yè)者所致。曾經(jīng)作為電子產品行業(yè)領頭羊的索尼,如今也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索尼前常務董事天外伺郎曾感嘆說,是績效主義毀了索尼,績效主義最大的弊端是搞壞了公司氣氛,使員工無法拿出工作激情發(fā)揮自己的潛力[8]。
最后,關于日本勞動關系的調整還需要說明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調整所造成的影響目前還是有爭議的,雖然主流的看法認為日本正在確立起新的勞動關系模式,但仍有少數(shù)學者認為傳統(tǒng)勞動關系模式并沒有完全退去。新自由主義改革雖然造成了很大沖擊,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企業(yè)都采用這一做法,時至今日,日本依然有不少產業(yè)或企業(yè)保持著傳統(tǒng)的終身雇傭關系。另一方面,即使在大企業(yè)中,采納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所造成的影響也應謹慎衡量,畢竟還是有相當?shù)念I域繼續(xù)使用正式工制度,尤其是在一些關鍵部門和核心崗位,正式工制度仍然是備受青睞的做法,高級管理人員的晉升仍然把年資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對于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模式是一種取代還是一種補充或共存,仍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劉國華,張青枝.論戰(zhàn)后日本勞資關系的演變及其歷史經(jīng)驗[J].科技和產業(yè),2011(4).
[2][日]松本厚治.企業(yè)主義——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的力量源泉[M]. 北京: 企業(yè)管理出版社,1997:31-32.
[3]呂守軍.日本勞資關系的新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基于法國調節(jié)學派制度理論的研究[J]. 教學與研究,2011(11):46-54.
[4][日]橋本壽朗等.現(xiàn)代日本經(jīng)濟[M].上海:上海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2001.27.
[5][美]高柏.日本經(jīng)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59.
[6]劉文.日韓工會發(fā)展比較及啟示[J].東北亞論壇,2012(2):35-47.
[7][日]渡邊雅男.現(xiàn)代日本社會結構的階級分析[J].政治學研究,2008(1):26-34.
[8][日]天外伺郎.績效主義毀了索尼[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12/16/2466246_178971101.shtml,2017-08-20.
Adjustment and In fl uence of New Liberalism in Japanese Labor Relations’ Liberalism
Yang Hongxiao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ermanent employment,seniority system and enterprises unions emerged in Japan in the process of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bubbles in the 1990s and popularity of globalism and new liberalism, Japan risked in making wide and new liberalism adjustment to the labor relations field. However, it did not achieve their expectation but seriously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and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ers” tendency during the global era. More attention needed to pay on the long-term potential in fl uence on enlarging the social gap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Extent of adjustment on new liberalism and its in fl uence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Japan; labor relations; new liberalism
房克樂)
本文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中央高校基本業(yè)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全球化進程中勞資關系問題反思”(項目編號:17ZY0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F249.313
A
2095-7416(2017)06-0014-07
2017-10-09
楊洪曉(1984-),男,山東日照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