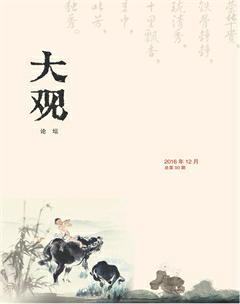龔賢山水畫技法研究
栗偉凱
作品多寫金陵山水,長于用墨。龔賢喜用老辣樸拙的筆觸,沉著穩重,禿筆與尖筆兼用。禿筆,取之圓潤蒼勁,勾屋,皴擦,畫樹和點苔蒼老有力。龔賢用筆在主張“欲秀而老”,秀而老就是準確、簡練而流暢有變化。畫家程正揆在贈龔賢的詩中道:“鐵干銀鉤老筆翻,力能從簡意能繁”,這很好地點出了龔賢在用筆上的特點和成就。他提出筆法、墨氣、丘壑、氣韻作為畫家四要,主張作畫要中鋒用筆,并且要古、健、老、蒼,才能避免刻、結、板之病,頗為精辟。龔賢用墨,以層層積墨見長,雖不用潑墨,實具有潑墨煙潤淋漓的效果,頗有宋人的用墨特點。其畫山石樹木中鋒用筆,蒼勁古厚,并用積墨法作反復皴擦積染,多至十幾層,墨色極為濃重,但仍有深淺、濃淡、明暗等細微變化,山石樹木往往渾融一體,僅在陽面或輪廓邊緣處留出些許高光和堅實的輪廓,效果強烈,具有渾厚、蒼秀、沉郁的獨特風格,成功地表現了江南山水茂密、滋潤、幽深的特征。龔賢作畫最善用墨,主張墨氣要厚、潤,他發展了積墨畫法,龔賢精研此法是追求一種蒼潤的境界,他以干筆作墨骨,再以層層皴染包潤之,令山林樹木呈現出鮮潤沉厚的墨韻,使畫面濕潤厚重之感,這種畫法適于表現江南濕意濃重的山水景色,同時也使龔賢的繪畫具有了一種深郁靜穆的格調。龔賢的畫法分兩類,世稱“墨龔”和“白龔”。他善用黑白對比的技法,前者濃密蒼茫,后者簡淡雅潔。他在《半千課徒畫說》中稱:“非黑,無以顯其白;非白,無以利其黑。”又如《平遠小景》圖(冊頁,紙本水墨)中所畫的房屋,簡潔明麗,在周圍筆墨的映襯下,潔白的屋墻似乎透出光亮。此處即用黑白對比的技法。
所畫山水能掃除時習,上追董 (源)、巨(然),用墨深厚,皴擦每至十余次,自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自寫小照作為一個掃葉僧,因名所居之樓,為掃葉樓。有《畫訣》傳世,言近旨遠,極方便于初學畫的人。 龔賢的山水畫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在表現技巧上,他的作品有個惹人注目的特點,就是用墨。
龔賢的山水畫非常重視構圖。他的畫視野開闊,氣象萬千。他的“三遠”構圖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出神人化。他往往提高視線的角度,“平遠”構圖,多采取俯視角度,這樣,視野開闊,平淡中倍增飄渺的感覺。尺幅之中,山河無盡。作“高遠”構圖,也是如此,先俯視,爾后眼光往上作仰視,真有下攬深谷、上突危峰的氣概。他十分注重上下的位置。他的山水畫一般很“滿”,但“滿”而不塞,常常用云帶、流水作為空白透氣。從整個畫面來說,很有氣韻。這才是龔賢的筆、墨、丘壑渾然一體的韻,從而創造出有地方特色的山水畫。他是當之無愧的“金陵畫派”的首領。
龔賢能獨立成家,他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便是用墨的方式與同時代的畫家不同。與龔賢處于同一時代的四王是當時畫壇的主流。四王一味在案頭臨摹仿效黃公望和倪云林,他們追求的是筆墨的“天真幽淡”,體現的是一種學者型的書卷氣。石濤與龔賢在學習宋人師法自然上具有共同點,但石濤與四王一樣重視元人水墨寫意的技巧,在藝術語言的選擇上和龔賢有大不同。龔賢所推崇的是董源、米芾、吳鎮以及離自己最近的沈周,但他的墨法和沈周也不一樣。龔賢的一生基本活動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江南的丘陵河川以及廣袤的平原是他惟一的視覺經驗,誠然,他的閱歷眼界以及氣度都不如石濤,但這種局限也造就了他的個人特色。
“氣宜渾厚,色宜蒼秀”,這是龔賢對山水畫整個畫面視覺效果的要求。但凡見過江南豐饒明麗山川者,都會感到“渾厚”與“蒼秀”確是眼前之景最精到的概括。如何表現這“渾厚”“蒼秀”?龔賢放棄了中國畫法中常用的“破墨”技法,這種技法在元明清文入畫中非常普遍,就是利用水墨在生宣紙上的一次性滲透達到表現效果。龔賢運用的是宋人的“積墨”法。他畫的山石樹木總是經過多次的皴擦渲染,墨色極其濃重,而濃重里卻隱含著豐富細微的明暗變化,通過層層積效的對比關系來傳達山水的“渾厚”與“蒼秀”。他畫的石頭,輪廓中大部分為筆跡嚴整渾成的多次皴擦渲染,而僅在合“理”的地方留下空白的受光部分,這有些像西方繪畫中所謂的“高光”。石頭的厚重體積,堅硬的面的轉折,以及在濕潤的空氣中那種被浸潤的質感都得到了恰當的體現。有人認為龔賢可能在畫法上受過當時居住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的啟發,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龔賢用墨擅長利用黑白對比的效果,他曾說:“非墨無以顯其白,非白無以判其黑。”他畫中的空白處雖然不著一筆,卻能使人感覺到空朦彌漫的霧氣或是清澈透明的汪洋湖泊與河流。他用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潤”。他畫的樹能達到蒼翠欲滴的效果就在于用墨之“潤”。龔賢認為要把“潤”和“濕”區分開來。“墨言潤,明其非濕也”。“潤墨鮮,濕墨死”。“鮮”就是有光澤和勃勃生機,但“濕”而不“潤”的用墨,下筆之后不能恰當地掌握墨與對象表現要求相適應的濃淡干濕的變化,最后使墨只能浮于紙上,或是一片糊涂而成為一團死墨。
對于用筆,龔賢認為“欲秀而老”。“秀而老”就是準確而簡練,流暢而有變化。龔賢早年用筆稍有鈍滯,但到了晚年則大膽潑辣而蒼勁活潑。他在勾勒一些房屋橋梁以及枯樹峭壁時,隨意數筆便表現各自的精神,真正顯示了他用筆的“秀而老”。龔賢的好友、畫家程正樓曾在贈詩中這樣評價他:“鐵干銀鉤老筆翻,力能從簡意能繁。”這句話準確地道出了龔賢用筆的特點與成就。
與龔賢同時代的人,對他評價頗高的多是他的好友,如周亮工、孔尚任、程正拴、張瑤星等人。周亮工認為:“其畫掃除蹊徑,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信不誣也。”程正拴題半千畫曰:“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孔尚任有詩贊揚他:“野遺自是古靈光,文采風流老更強。幅幅江山臨北苑,年年筆硯選中唐。”而清代編撰《國朝畫征錄》的張庚,因為視董其昌和王原祁為畫苑正宗,因此在贊揚:“半千畫筆得北苑(董源)法,沉雄深厚,蒼老矣。”之后,又批評他“惜秀韻不足耳”。而秦祖永對龔賢基本持否定態度,說他“墨太濃重,無清疏秀逸之趣”(13)。今天看來,龔賢是一位具有現代意義的山水畫大師,他對現代山水畫大師如黃賓虹、李可染等人都有較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