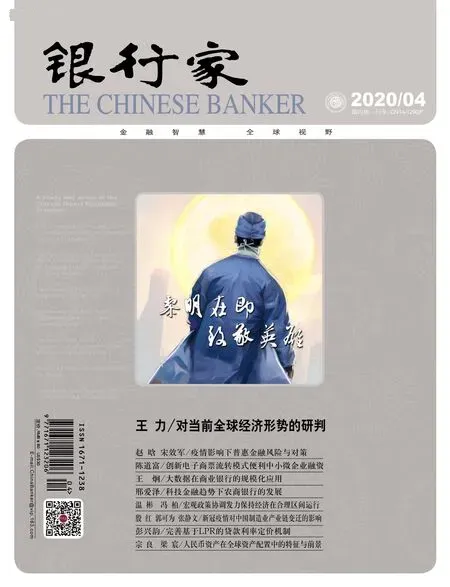高度關注意大利銀行業的危與機
熊啟躍+劉銳+易曉溦


編者按:意大利銀行業是歐元區第四大銀行體系,其在本國金融體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近來,意大利銀行業資產負債規模收縮,利潤大幅下滑,不良貸款快速攀升,評級、股價等市場指標急劇惡化。2017年,意大利經濟依舊疲弱,負利率政策短期難以扭轉局面,意大利國內政權更迭將造成動蕩,這些都會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如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防控,會使當前情況惡化,不排除發生銀行業危機的可能。對于未來意大利局勢的不確定性,中資銀行應如何做出好合適的防范預案?作者給出了相關建議。
高度關注意大利銀行業的困境及潛在影響
意大利銀行業具有系統重要性
2015年,意大利經濟總量達1.64萬億歐元(GDP按照現價統計),在歐元區僅次于德國和法國(德國GDP為3.03萬億歐元、法國GDP為2.18萬億歐元),列第三位。截至2015年底,意大利銀行業資產規模達3.29萬億歐元,列歐元區第四位。無論對歐元區銀行業,還是對國內金融體系,意大利銀行業都具有系統重要性。
對歐元區銀行業而言,截至2015年末,歐元區銀行業資產規模為27.7萬億歐元,意大利銀行業規模占比接近12%。另外,在歐洲央行直接監管的124家銀行集團中(這124家銀行集團的資產規模占歐元區銀行業資產規模的82%),有14家來自意大利,占比為11.3%,這14家銀行在124家銀行中的資產占比達10%。另外,截至2015年底,意大利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高達3600億歐元,占歐元區不良貸款總規模的33.3%。
對意大利金融體系而言,2015年底,意大利銀行業在國內金融業的資產占比為64.1%,據主導地位。銀行集團是意大利金融機構的主要組織方式,獨立于銀行集團的金融機構不足意大利機構總數的15%,租賃、保理、保險以及證券投資等公司大都由銀行控股。另外,銀行信貸是意大利實體經濟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2015年,意大利非金融企業通過外源融資籌集資金1.03萬億歐元,其中8611億歐元是通過銀行信貸獲得的,占比為83.31%。
意大利銀行業深陷經營困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意大利銀行業經營表現每況愈下,體現在:
資產負債規模負增長。一般情況下,銀行資產規模每年應呈現自然增長狀態。然而自2008年以來,意大利銀行業的資產和負債規模呈負增長態勢。2015年末,意大利銀行業資產和負債規模為3.3萬億歐元和2.9萬億歐元,分別較2008年減少0.15萬億歐元和0.26萬億歐元,降幅為4.9%和9.7%。
低(負)利率環境下,盈利大幅收縮。意大利銀行業以傳統存貸款業務為主,維持穩定的凈息差是其盈利的關鍵。2008年以來,歐央行開始實施低利率政策,2014年更是將存款便利利率調至負值區間。負利率政策推出后(2014~2015年),意大利五大行的平均凈息差較負利率推出前(2008~2013年)下降0.37個百分點,降幅達20.3%(表1)。其中,錫耶納銀行和意聯銀行降幅分別達29.7%和23.7%。受利息收入大幅下降的影響,2015年意大利銀行業僅實現凈利潤37.1億歐元,較2008年下降66.1%。
不良資產大幅攀升,風險吸收能力堪憂。2015年末,意大利銀行業不良貸款規模達3604億歐元,是2008年的2.1倍;不良貸款率為18.1%,較2008年提高11.8個百分點。2015年末,意大利銀行業撥備覆蓋率為45.4%,較2008年下降0.7個百分點,其中,“壞賬類”不良貸款覆蓋率為58.6%,較2008年下降3.9個百分點;“不太可能支付”類貸款覆蓋率為27.5%,較2008年下降1.8個百分點;逾期類貸款覆蓋率為18.8%,較2008年下降10.4個百分點(表2)。同期,意大利銀行業平均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2.8%,較歐元區平均水平低2.8個百分點。
評級、估值等市場指標跌至“谷底”。截至2016年底,意大利五大行穆迪長期信用評級處于B2~A3級,錫耶納銀行長期信用評級僅為B2級,接近“垃圾債”評級。五大行市凈率僅為0.38倍,錫耶納銀行市凈率為0.07倍(表3)。2016年7月,歐洲銀行業管理局(以下稱EBA)公布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極端壓力情景下錫耶納銀行2018年末資本充足率和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僅為1.03%和-2.44%,遠低于監管要求。
風險及潛在影響
考慮到意大利銀行業的系統重要性,其當前的低迷表現將造成一系列風險:
一是拖累意大利經濟增長。危機以來,意大利銀行業體系的低迷表現拖累了意大利經濟。2008~2015年,意大利年均GDP增速僅為-1%,較歐元區平均增速水平低1.2個百分點,在19個歐元區國家中增速僅高于希臘(-3.7%)(圖1)。同期,意大利銀行業的資產和負債分別下降0.15萬億歐元和0.26萬億歐元,降幅分別達4.9%和9.7%。更為重要的是,2008~2015年,意大利銀行業非金融企業貸款余額的降幅要明顯大于資產余額降幅,說明在銀行整體的信貸收縮中,非金融企業受到的影響最大,而它們往往是促進經濟增長、吸納就業的主要力量。
二是壞賬導致更多銀行陷入困境。2016年上半年末,錫耶納銀行、人民儲蓄銀行、聯合圣保羅銀行、意聯銀行和裕信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33.2%、25.0%、17.0%、14.7%和14.7%。如果扣除撥備、計算不良貸款凈額,錫耶納銀行和人民儲蓄銀行的不良貸款凈額比股東權益分別為1.89倍和1.22倍(表4),這意味著如果違約損失率為100%,這兩家銀行都將處于資不抵債局面。2015年,意大利不良貸款平均回收率僅為35%,較2012年下降14個百分點,銀行體系撥備覆蓋率(50%左右)已不能覆蓋不良貸款的真實損失(65%)。對意大利部分中小型銀行而言,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已經大量侵蝕資本,許多銀行都已陷入困境。
三是負面外部信號嚴重影響銀行再融資能力。通過外源融資籌措資金,是化解不良貸款風險的重要途徑。然而,負面外部信號已經嚴重影響意大利銀行體系的再融資能力。2016年,意大利銀行業發債規模同比下降15%。錫耶納銀行50億歐元籌資計劃因市場信心不足而中止,不得不選擇執行政府的BRRD計劃(Banking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即銀行恢復與處置指引,以下稱BRRD)。裕信銀行130億歐元的增資計劃也因其股價超跌面臨不確定性,如果裕信銀行不能從市場籌集足夠資金,其也面臨啟動BRRD計劃的可能。相較于大型銀行,意大利中小銀行的再融資能力下降更為明顯。再融資能力下降削弱了意大利銀行體系的風險抵御能力,顯著增加了銀行業的脆弱性。
四是執行BRRD帶來市場恐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意大利共有8家銀行(包括意大利第三大銀行——錫耶納銀行;3家中等規模銀行——維琴查人民銀行、威尼托銀行和卡里奇銀行;4家小規模銀行——埃特魯利亞銀行、CariChieti銀行、馬爾凱銀行和CariFerrara銀行)進入BRRD計劃。這8家銀行中,錫耶納銀行的體量最大,受到了市場的高度關注。由于前期50億歐元的再融資計劃失敗,錫耶納銀行不得不執行由意大利政府主導的“審慎資本重組”方案,該方案遵循BRRD框架,要求錫耶納銀行增資88億歐元,以滿足極端壓力情景下8%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和11.5%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在籌集的88億歐元中,意大利政府出資46億歐元,剩下42億歐元將通過對錫耶納銀行次級債進行“債轉股”實現。錫耶納銀行發行的42億歐元次級債中,有20億歐元的投資者來自私人部門,他們不愿意執行轉股條款,這給BRRD執行造成了較大難度。同時,由于償付順序靠后的次級債投資者面臨風險,這使錫耶納銀行的儲戶和一般債券持有者的信心產生了負面影響。2016年重組方案推出以來,錫耶納銀行的存款余額下降10%。參考希臘和塞浦路斯銀行危機的相關經驗,在對銀行進行BRRD的過程中,容易造成市場恐慌,導致擠兌和資本外逃。
中期趨勢研判
意大利銀行業具有系統重要性,其持續穩定地運行對意大利乃至歐元區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意義重大。當前,意大利銀行業深陷經營困境。從中期看,意大利經濟依舊疲弱,負利率政策短期難以扭轉,意大利政權更迭將造成動蕩,這些風險都會影響銀行的經營狀況,如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防控,會使當前情況惡化,不排除發生銀行危機的可能。
首先,意大利經濟疲弱不支持銀行業績企穩。2016年,歐元區經濟增速回升,呈現出復蘇態勢。然而,意大利經濟依舊低迷,2016年四季度,意大利GDP環比增速僅為0.2%,低于歐元區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較2016年三季度下降0.1個百分點,在歐元區19個國家中列倒數第三。考慮到歐洲整體的動蕩局勢,意大利經濟2017年復蘇的概率較低。基于以上判斷,實體經濟貸款需求和信貸質量明顯改善的可能性偏低。
其次,負利率政策短期不會調整。當前,歐元區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牢固、經濟企穩的態勢并不明朗。歐洲央行短期內調整貨幣政策立場的可能性不大,存款便利利率將繼續維持在-0.4%的水平。意大利銀行業所處的低息差環境不會發生明顯變化,其利息收入和盈利狀況仍將處于較低水平。
再次,政局不確定性給銀行業帶來風險。意大利大選每五年舉行一次,新一輪大選應于2018年舉行,從目前情況看,意大利很可能在2017年提前舉行大選。大選結果對銀行業影響深遠。新一屆大選的主要競爭者包括執政黨民主黨和五星自由黨。兩黨最新的民調支持率都在30%左右。2017年2月,倫齊宣布辭去民主黨總書記職務,這意味著民主黨內部可能出現分裂。該事件無疑增加了五星自由黨獲得勝利的概率。五星自由黨代表意大利中南部平民階層利益,是一個親俄羅斯且主張“脫歐”的政黨。意大利憲法規定,如果取勝政黨能獲得40%以上的選票,那么該政黨將在下議院獲得55%的獎勵席位,而不用參照選舉中的支持比例分得相應席位。55%的下議院席位意味著對重大事件的決策具有完全的控制權。當前,不排除政黨之間存在聯合競選,以謀求下議院絕對控制權的可能。
政治風險是2017年意大利銀行業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政權更迭對銀行業造成的潛在影響包括:
(1)不良貸款處置面臨不確定性。倫齊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動不良貸款化解,啟動了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債轉股和資本補充計劃等措施,這些前期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意大利政權未來的更迭可能對前期不良貸款處置政策的延續性會產生一定影響,不良貸款處置速度可能會因此放慢。
(2)銀行體系債務風險加劇。意大利銀行業的資產端持有大量歐洲主權債券,特別是本國債券。意大利政局的不穩定將使主權債券風險提高。同時,銀行業負債端有15%左右的資金來自零售債券,2015年,意大利部分中小銀行發行的次級零售債券出現減記或強制轉股事件,政治不確定性的增大會通過影響意大利主權評級,造成銀行債券持有者的恐慌。
(3)意大利“脫歐”的概率提升。從目前態勢看,意大利“脫歐”的可能性正不斷提高,“脫歐”派五星自由黨和北方同盟在國內的影響力持續上升。一旦意大利“脫歐”成功,參考英國“脫歐”經驗,其至少將從“通行證”機制的改變、在意大利和歐元區形成差異化的監管制度以及派生金融風險等方面對意大利銀行體系產生沖擊。
中資銀行對策
短期內加強風險防范
針對意大利銀行體系可能存在的風險,中資銀行短期內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一是防范意大利乃至歐元區政局變動產生的風險。意大利銀行業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是政治風險。2017年是歐洲大選年,法國、德國等歐元區核心國家都將舉行大選。意大利大選也很有可能提前舉行。可以預期的是,無論哪個政黨上臺,持有何種政治主張,政權更迭必然產生較大影響。如果支持“脫歐”的五星自由黨獲勝,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中資銀行應高度關注意大利國內政治局勢變動,特別是對意大利、德法大選的走勢及結果保持跟蹤,并相應采取預案。整體上看,2017年歐洲政局充滿變數,金融市場也會隨選舉結果大幅波動,中資銀行應有針對性地防范市場風險。
二是防范“問題銀行”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意大利銀行業的壞賬風險已基本釋放,銀行業進入壞賬消化和處置的“陣痛期”。BRRD計劃使“問題銀行”低層級資本持有者將面臨投資發生損失的風險,會造成“問題銀行”的儲戶和一般債權人的恐慌。如果“問題銀行”規模較大,可能導致存款“搬家”和擠兌現象。如果參考希臘和塞浦路斯銀行危機的教訓,恐慌還可能造成資本大量外逃。中資銀行應關注意大利“問題銀行”的處置進程,對負面事件所產生的風險進行防控,并定期開展壓力測試,保證極端情況下的風險吸收能力。
三是加強監管合規和聲譽風險防范。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歐元區對于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趨嚴。近年來,國際大型銀行巨額罰單不斷,中資銀行應加強海外法律合規管理,特別是反洗錢和涉嫌為恐怖主義融資方面,應加大管理的力度。同時,針對歐洲恐怖主義勢力抬頭、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以及近來意大利國內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發等問題,中資銀行應提高安全防范意識,加大對海外機構的安全保障,對員工人身安全、網點資金和設備安全采取必要防控措施;加強聲譽風險管理,對突發性風險事件,要及時采取行動,第一時間減小聲譽風險。
四是繼續審慎敘做在意資產業務。中資銀行在意大利的資產規模不大,整體風險可控。綜合評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建議中資銀行繼續審慎敘做在意資產業務。控制與“問題銀行”的同業業務;審慎開展意大利非金融企業和個人貸款業務,服務客戶可聚焦國內“走出去”企業;審慎開展意大利及歐元區主權債務的投資,減少歐元計價資產的持有。
中長期抓住有利機遇
雖然短期內應以防控風險為主,但從中長期角度看中資銀行也應抓住有利機遇。
一是抓住意大利低估值契機。中資銀行可在意大利尋找一些低估值、且通過兼并重組能夠在中長期產生較大協同效應的資產進行收購;針對長期具有投資價值、短期估值水平超跌的公司,可適當購買股權;即使不能進行收購和持股,中資銀行也可考慮利用在資金、信息和專業咨詢領域的優勢,促成中資銀行客戶對意大利廉價資產的收購;2015年以來,意大利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的處置意愿明顯加強,銀行出售不良貸款的規模顯著提升,這一方面加快了不良貸款的處置周期,但同時也降低了不良貸款的回收率。這意味著不良貸款處置市場的業務機會增多,且收益提高。中資銀行應尋找該領域的業務機遇,謀求與有關機構開展合作,探索在壞賬處置領域獲得更多收入。
二是利用意大利低融資成本環境。當前,意大利乃至歐元區流動性充裕、資金價格低廉。2017年,在歐元區整體動蕩的背景下,歐元走強的概率較低。中資銀行可憑借良好的信譽和穩定的長期信用評級,加大在意大利乃至歐元區的資金籌措力度。對于弱勢幣種,如歐元和英鎊,可發行短期限浮動利率債券,對強勢幣種,如美元,可考慮發行長期、固定利率債券。在寬松貨幣環境下,交易業務具有較多創收機會,中資銀行應加強歐洲地區交易中心建設,加大交易人才培養力度,提升交易業務創收能力。
三是抓住歐洲政治經濟格局改變帶來的戰略機遇。當前,歐洲“亂局”削弱了歐洲統一經濟體在全球政治經濟領域的話語權。中資銀行應進一步發揮國際化優勢,促進中意兩國在貿易、產業以及金融領域合作的深化;同時,高度關注意大利政局變動對兩國外交關系的潛在影響,結合這些變化調整在意的發展戰略。
(作者單位:熊啟躍、易曉溦,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劉銳,中國建設銀行米蘭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