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選講
管子選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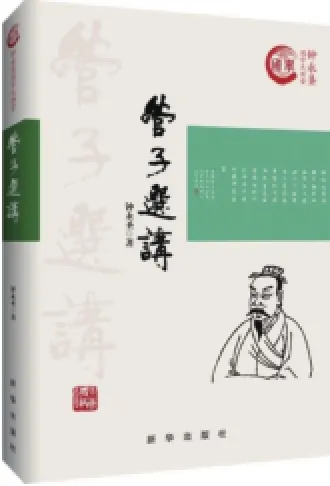
鐘永圣 著/新華出版社/2017-01/58.00/9787516630266
本書是作者系列講座的結集。作者首先以親和力的語言,向讀者傳授了學習傳統經典*重要的三個方法——“以經解經”、“體慧”,以及“至誠誦讀”。作者重實踐的“體慧”而非僅止在知識的了解,重至誠的感悟而不拘泥于學術的辯駁,在他的充滿智慧的講解下《管子》不再是玄之又玄的“天書”,是一部人人都能看得懂,獲得切實的啟迪和智慧,從而改變自身命運的讀物。
《管子選講》書摘
許久了,人們談論春秋“諸子百家”,總是儒、墨、道、法、兵、陰陽,忘了還有“管”家,忘了以“經濟家”為代表的齊國“稷下學派”曾經那么舉足輕重、那么獨領風騷、那么稱一時之盛。
按照出生時間的先后順序,管子實際上是“春秋第一子”,老子、孔子、墨子、孫子、韓子皆生在其后;如果把以管仲為代表的思想理論體系稱為“管家”,那么管家其實也是“春秋第一家”,齊國正是憑借管家思想才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言:“齊國遵其政,常強于諸侯。”因此《管子》一書,也就是“中華經濟學第一書”,上海財經大學已故的胡寄窗教授稱其為“一本偉大經濟巨著”,認為《管子》全書以“經濟”為論證主題“在先秦著作中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我們說其第一,并非是把它評價為中華傳統經濟學的“創始”,而是指《管子》論述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在文獻上“最完備”、在戰略上“最理論聯系實際”、在國家經濟策略上“最集大成”。
孫中山先生解釋“政治”為處理眾人之事,中國文化中“經濟學”本來就是“政治的”,本不需要在“經濟學”前加“政治”這個限定語。之所以還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是順應近代以來借鑒西方的文化概念早已經形成的表達習慣。有些文化語匯一旦形成,就成了約定成俗的觀念,不暫時將錯就錯似乎就無法溝通。要想徹底地扭轉偏見和誤解,只能依靠長時間的歷史驗證。
華夏文明的傳統經濟學核心理念創始于《易經》,《乾卦·文言》中說:“利者,義之和也。”指明了取利的原則和財富的倫理來源。這一理念源頭是如此重要,不但體現了華夏文明“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且清晰地闡明了“利”的貫通性質:物理上的利,實際是倫理上和氣的體現。利,因和氣而成為“益”,因爭奪而成為“害”。一種所得到底是“利益”還是“利害”,不是由資本決定的,而是取決于當事人心念和行為的倫理性質。例如,同樣一筆錢,因為捐贈而成為“善款”,因為貪腐而成為“贓款”;作為生產和分配決定因素的資本,一方面可以因為擁有者的自私與殘酷,成為“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語);另一方面也可以因為擁有者的關懷與善意,成為“匡扶正義、兼濟天下”的善財之源。
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學者把這種“貫通各學科”的現象稱為“跨學科”,實際上是未能徹本知源的提法,因為社會科學學問的實質本無學科界限。現代西方經濟學者中也有一些人大談“人本經濟學”,同樣是不能明心見性的未到之語,人有善惡好壞諸種不同的表現,試問經濟學到底要“本”哪一個“人”?最根本的說法在中華傳統經典里,例如曾子在《大學》里表達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所以最徹底的說法應當是“德本經濟學”。
說到經濟的“德本”,超出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界限。西方經濟學把“資源配置”作為首要問題,只在財富的“物”象上做文章,始終未能深入到財富的“本”地。而中國傳統經典往往以達到“學究天人之際”境界的語言,一語道破“財富的來源”。例如,《易經·坤卦·文言》中指出“厚德載物”,明言德行積累不到一定程度,就無法承載(獲得)一切“物”質財富。再如《道德經》中指出“道生一二三乃至萬物”,清晰地指明作為萬物中的一物的財富,在根本上是由“道”生發出來的。可是由于世間人大多數不明“道”,所以還是對“財富的來源”不明所以。這樣,老子在《道德經》的結尾就直截了當地把答案和盤托出:“即以為人己愈有,即以與人己愈多!”那就是說,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自己擁有的就越多;給出去的越多,自己收回來的也就越多!
人類社會在倫理上界定“為他人”是公、是善、是德,界定“給出去”是公、是善、是德,這正是對“德本財末”觀念異曲同工的解釋。《黃帝內經·靈樞·本神》中說“天之在我者,德也”,說明“我”要想發財,就必須積“德”;我要想積德,就必須遵守“天”的規矩。“天”就是自然,自然的規矩就是“天道”,就是“天理”。天理化為人間的規矩,就是人倫,人倫的具體內容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管子恰恰明確地指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以此作為治國理政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在齊國倡導中華倫理經濟學,最后在短短二三十年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把齊國送上霸主地位,影響后世幾百年。以至于孔子都感慨地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至于孔子以圣人境界,因管子未能倡行王道、復興周室而“小之”,導致后世既無實踐經驗也無圣人境界的儒生居然也長期輕看管子及其學說,實在是自命清高、因噎廢食、求全責備、流弊深遠的憾事!
以現代分科的角度看,管子經濟學是倫理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統一,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統一,是政府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學的統一。在中華文化中,“經”指恒常之道,是最權威、最徹底、最合適的“理性”;“濟”的本義是過河,引申為周濟、幫助、與樂和拔苦。綜合起來,“經濟”的本義是指“以最智慧、最無害、最有益的方式讓天下人民獲得物質與精神的全方位滿足”。絕不僅僅是西方起源于亞當·斯密《國富論》的那個研究資源配置的“經濟學”。這種文化翻譯的歷史誤會,據某些學者考證,肇始于一個叫神田孝平的日本人,他在1892年前后把economics這個詞匯翻譯成漢字的“經濟學”,導致當時沒有文化自信的國民以為自家沒有經濟學,這一錯就是一百多年。其實管子經濟學恰恰是包括但不限于資源配置的經濟學;是強調與時競而不與人爭的經濟學;是圓覺的智慧而不是局限分科的經濟學。
以今天的學術視角來看,《管子》的根本理念都是“跨學科”的論述,既是倫理的經濟學,也是政治的經濟學,更是行為的經濟學。例如,管子論述德、義、禮這些倫理內容都是以實實在在的經濟內容為依托的:德有六興(另一說,叫六典),分別是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窮;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纖、嗇、省用,以備饑饉;禮有八經,分別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在這樣的理論體系內,涵容著解行相應、知行合一的智慧,絕不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所批評的那種遠離真實的“黑板經濟學”。
之所以很確切地說《管子》中所述的內容是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是因為管子時刻把國家的治理與發展經濟統一起來。例如《管子》開篇就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那么怎么能達到天下大治呢?管子認為只要熱愛人民,利益大眾就能做到:“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天下治矣。”利益大眾,治理國家,首要的任務就是“富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如果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不能不說是從“黨的富民政策”開始的!不能不佩服管子論述國家治理政策見解之深。如果我們放眼當今世界上那些動蕩的國家的經濟狀況,不能不說是從國家思想價值觀念的局勢混亂開始的,越亂越貧,越貧越亂,越亂越無法實現“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不能不佩服管子論述倫理經濟理念之高。可是,即使這些很有現實說服力的論述被人知曉,仍然不能使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擁躉消除對中國本土經濟學的鄙夷和不屑,常常提起“人家”西方經濟學有多深刻和多科學!例如說亞當·斯密論述人性自利多么有洞見,由此“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論證的起始點而被廣為傳誦。那么我們不妨看看《管子·禁藏》篇中論述人性自利的思想有多么深刻,而其文言又有多么美:“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孵卵,無形無聲,而惟見其成。”
特別是最后幾句,“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相當于把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倡導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用十六個字就論述完了,精彩絕倫。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號召大家“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管子》以中國古代文化的表達形式闡述的傳統經濟學具有鮮明的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如果我們很好地梳理和總結,它同樣可以有現代學術規范所需要的時代性、系統性和專業性,不但內容上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語言上具有獨創的中國風格,而且在境界上更具有安定天下、傲視群雄的中國氣派。
恢復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挖掘和整理,恢復中華經濟學的本義,以使大眾樹立正確的經濟觀念,具有正本清源的教化作用。 通過傳統經典的溫習以在文化源頭上認祖歸宗,可以增強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摒棄“人在局限條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錯誤經濟觀念,可以挽救世道人心;確立經濟學“善財利生,普濟天下”的“中國標準”,可以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