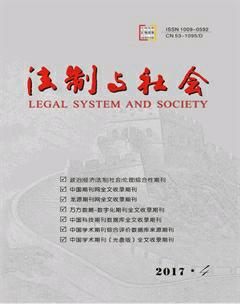《極地航行準則》
摘 要 氣候變暖帶來冰雪消融。在實踐中,其他國家經過北極航道,一般要遵循加拿大和俄羅斯的國內法,甚至接受其強制引航和破冰服務。但如今,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極地航行準則》通過,俄加主張航道為“內水”及依據其國內法強制管控北極航道的做法將越來越難以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可以說,《準則》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北極航道國際海峽性質的接受度。
關鍵詞 《極地航行準則》 北極航道 法律地位
作者簡介:張星河,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科書記員。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003
北極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北極,是全球的北極。北極航道盡管受制于幾個主要北極國家的管轄,但其法律地位不是在成為國際海峽的路上,就是已具備國際海峽的標準。北極航道的治理不單單是某一區域某一方面的治理,而是跨區域甚至是全球性,涉及到環境保護、航行安全、經濟、商業、軍事、政治等多領域的綜合性、整體性治理。任何一個國家單憑一己之力管理和控制北極航道的做法既不符合北極事務全球性的特質,也與全球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影響不相匹配。在此背景下,全球層面專門性、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極地航行準則》應運而生。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被視為現今國際社會對北極航道法律地位達成的初步共識,這一共識推動著北極航道在不遠的未來完全成為國際海峽的愿景成真。
一、《極地航行準則》的制定過程
《極地航行準則》的出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20世紀80年代,有關在極地水域建造和設計船舶的國內規則就開始相繼出現。國內規則的紛亂復雜導致國家、企業、船級社協會和保險公司之間的混亂。于是,90年代開始,國際層面統一的極地規則發展起來,但直到2002年,IMO才通過了不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北極冰覆蓋水域船舶航行指南》(以下簡稱《北極指南》)。
《北極指南》旨在補充《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現有的規范要求,以應對北極冰覆蓋水域的氣候變化,提出了海洋安全和防治污染的額外要求。由于《北極指南》僅適用于北極地區而非南極地區,2009年又制定了同樣不具有約束力的《極地水域船舶航行指南》(以下簡稱《極地指南》)。《極地指南》的宗旨與《北極指南》相同,不同的是《極地指南》是對《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與《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二者的補充規定,且可適用于南極地區。
鑒于兩個航行指南都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國際社會對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統一極地航行規則的需求仍然存在。2010年,受到來自丹麥、挪威、美國和英國的倡議,IMO啟動了由其分委員會制定具有強制力的極地準則的議事項目。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北極理事會支持這項提議,加拿大和俄羅斯也表示積極參與準則的制定。
2014年11月,海上安全委員會(MSC)在其第94屆會議上,審議并通過了《準則》和SOLAS補充規定;環境保護條款和MARPOL補充規定則由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在其2015年5月舉行的第68屆會議上獲得通過。至此,IMO完全通過了《極地航行準則》及其相關補充規定。作為SOLAS和MARPOL兩份公約的一部分,這份準則將具有強制約束力,于2017年1月1日生效。這份準則具有里程碑式意義,標志著在極其艱苦的極地水域環境下IMO保護船舶和人命進入一個嶄新階段。
二、《極地航行準則》的基本內容
作為SOLAS和MARPOL兩個公約的補充規定,《極地航行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總結了目前極地水域存在的危險因素,提供了船舶安全航行和極地環境保護的規范制度。《準則》包含規范性和非規范性兩部分,各部分又分別包括航行安全措施和防止船舶污染措施。 航行安全方面,船舶在極地水域航行須持有極地船舶證書。證書的取得要滿足《準則》規定的船舶建造、設計、裝備、操作、搜救等一系列要求。但破冰船助航制度是作為《準則》非規范性要求的一部分而存在。
防止污染方面,《準則》絕對禁止石油污染,但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地允許污水和垃圾污染。相比于加拿大的“零排放”標準,這一規定要寬松一些。
《準則》與其他國際法的關系方面,SOLAS第十四章明確規定“將不影響國家依據其他國際法項下的權利和義務”。
三、《極地航行準則》下北極航道法律地位的性質
《準則》問世后,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問題:《準則》將對現有北極航道法律制度安排產生怎樣的影響?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第234條將有何意義?對加俄北極航道國內法規則及其主張航道非國際海峽性的立場有何變化?
(一)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34條的影響
正如上所述,SOLAS明確了《準則》的通過不影響國家在其他國際法項下承擔的義務和享受的權利,這似乎意味著北極航道的法律性質與航道的具體管控可以分離開來獨立進行,也表示加俄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34條制定的國內法和主張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但是,《準則》在整體上會提高主張和依據的標準,比如,第234條中沿岸國制定的規則必須“依據最可靠的科學證據”這一條件,在《準則》細化了船舶認證、設計、建造、裝備、操作及環境保護的具體規定后,沿岸國所依據的“科學證據”必須有確實準確的數據和充分有理的分析作為支撐。 鑒于IMO在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準則》的通過使得沿岸國依據第234條單方做出規定還需要獲得更多國家的支持。
然而,《準則》對第234條產生的意義不可過分夸大。原因還在于第234條是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眾多國家間相互妥協的產物,其用詞和理解存在多種解釋。如對“專屬經濟區范圍內”和“適當顧及航行”的不同理解就會導致沿岸國及其他國家在“冰封區域”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不同,而《準則》還無法達到界定這些模糊詞語的程度。
(二)對加俄國內法的影響
在積極參與《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加拿大和俄羅斯兩國都不約而同地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協調國內法與《準則》關系的努力。俄羅斯對其在北方海航道的管轄范圍作了較為清晰的界定,消除了管轄可能擴展到公海的爭議,還將原來的強制破冰助航制度更改為與《準則》較為一致的許可證制度;加拿大逐步推進關于船舶結構、密封性、穩定性的規定與《準則》相一致;加拿大和俄羅斯都建立了各自的船舶冰級體系,對不同冰級的船舶規定了航行的限制時間等。
盡管如此,出于兩國對北極航道的權利主張和實際管控,加拿大和俄羅斯仍有相當比例的國內法規則超越了《準則》和現有的國際法規則,并且這種不協調還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最明顯的例子是俄羅斯對北方海航道實行的許可證制度中,許可證的頒發來自沿岸國和港口國,根據國際法和俄羅斯國內法,所有進入北方海航道的船舶都須申請并獲得俄羅斯當局的允許才可通行。而《準則》中的極地船舶許可證則由船旗國管轄,船旗國主管機關根據《準則》規定的要求來頒發證書。這種事前的許可制度在《準則》之外額外地加重了通行北方海航道船舶的負擔,明顯與《準則》有沖突。
(三)推動北極航道多邊治理和單邊治理的共生化發展
北極氣候變化從“冰封”到“冰融”的趨勢,推動著北極事務尤其是北極航道治理從“邊緣”到“重要關切”,也促使這一區域由曾經的“冷戰前沿”成為如今的“對話平臺”。隨著《準則》的誕生,IMO基本完成了由軟法引導到軟法引導和硬法規制并存的轉變,強化了北極航道區域的全球及多邊治理局勢,淡化了北極航道法律地位內水觀與國際海峽觀的爭執,加速了采取多邊行動達成共識以有效解決爭端的進程。
與此同時,以俄羅斯和加拿大等主要北極國家引導的北極航道單邊治理也共存共生。此種單邊治理某種程度上不僅是多邊行動的借鑒來源,也是其重要補充。比如,《準則》關于船舶的排污標準低于加拿大與俄羅斯的單邊環境標準,但正在向其更為嚴格的標準靠近。《準則》有關破冰引航制度的規定是非強制性的,加拿大和俄羅斯在不超越國際法范圍內,以其國內法做出的破冰和引航制度是對國際層面北極水域船舶航行規則的補充。
(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極航道國際海峽性質的國際普遍接受性
共生的含義不僅在于合作,還在于競爭。北極航道上多邊治理和單邊治理競爭趨勢較為明顯,《準則》的強勢介入對于北極航道國際海峽性質的國際普遍接受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為了加強合作趨勢,北極沿岸國家應當對第234條的使用采取一種更加開明和合作的態度,增強與IMO的協調和聯系,共同推進北極航運更高標準的發展。在此過程中,作為正在由區域治理向全球治理平臺演化的北極理事會,將以其科學評估、軟法引導和硬法規制三位一體的治理手段,為北極航道事務推進添磚加瓦,積極應對北極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各種挑戰。
北極航道成為國際海峽為俄羅斯和加拿大之外國家帶來的首要的和最大的福利就是航行利益,而便利的海洋航行將為各國帶來更多的權利,同時產生相應的義務。中國在北極地區不享有任何主權權利,但隨著北極航道國際地位的發展以及中國由地區性大國走向世界性大國,中國將會成為受益最大的國家之一。因此,加強中國的北極研究,積極參與到北極事務當中,是十分迫在眉睫的。
注釋:
International Code for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Waters (Polar Code),MEPC 68/21/Add.1,2015.
Molenaar,Erik J.Options for Regional Regulation of Merchant Shipping Outside IMO,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rctic Region[J].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2014,45(3).272.
參考文獻:
[1]北極問題研究編寫組.北極問題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2]陸軍元.北極地緣政治與中國應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3]郭培清,等.北極航道的國際問題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4]張瑩潔.論國際海事組織《北極航行準則》.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5]李浩梅.國際法視角下加俄航行管控制度分析.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4.
[6]何鐵華.《極地規則》與北極俄羅斯沿岸水域的制度安排.中國海事.2014(9).
[7]Michael Byer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rctic.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8]Oran R. Young .The Age of the Arctic. Foreign Policy61,1985(3).
[9]Charles Emmerson. The Future History of the Arctic.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