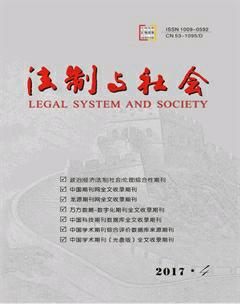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網絡犯罪中的適用
摘 要 縱觀當今時代,電子信息技術正在從多方位滲透進人們的生活,并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正如科技是把雙刃劍,電子信息技術也有其反面副作用,技術一旦被濫用,將會使人們的生活受到威脅,網絡犯罪也由此產生。在網絡犯罪中,電子證據作為一種維護人們權益的工具,其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網絡犯罪中的適用進行研究。
關鍵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電子證據 網絡犯罪
作者簡介:祁楚晗,西南交通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056
一、非法刑事電子證據的界定
縱觀《刑事訴訟法》,電子證據應當是證據形式合法、取證主體合法以及取證程序合法的一種新式證據。那么,什么是非法刑事電子證據呢?從本質角度來考量,證據自身并沒有合法與非法的差別,只是由于在收集證據時存在瑕疵,由此所形成的分類;基于廣義角度來分析,在整個形勢訴訟中,所收集的且與法律固定不相符的電子證據,也就是非法刑事電子證據。基于狹義角度來考量,所謂非法刑事電子證據,實際就是公安司法機關相關偵查人員,在與相關法律法規相違背的基本狀況下,運用其它形式的不正當方法,對電子證據材料所進行的收集工作。
從司法實踐角度來分析,非法電子證據主要存在于如下情況中:
1.公安司法機關未能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來完成證據的收集工作,比如為持有搜查證及扣押令等,便對電子數據進行收集。此些證據由于與法定程序相違背,因此被披上了非法的外衣。
2.對公民的生命權、隱私權及健康權等權利造成侵犯,以此為代價所進行的電子數據的收集。比如通過刑訊逼供手段所得到的電子證據以及誘惑偵查電子證據等,因健康權及人格權乃是整個人權架構當中的重要表現形式,如果公安司法人員運用各種不合法手段,對電子數據進行收集,并且是基于侵犯人權的基調下所開展的,因此,同樣可將其劃定在非法刑事電子證據范疇。對于非法電子證據相應分類而言,可將實體違法與程序違法為支撐,對其進行劃分,在整個司法實踐當中,不管為何種情形,均為對程序公正所造成的相應侵害,同時也是對法律的一種蔑視,相悖于我國依法治國的基礎理念。
二、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于調整電子證據的原因
(一)該規則本身進一步適用于調整新的偵查方式的需要
隨著高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傳統意義上的偵查模型已經發生變化。如監聽取證中不需要面對面就可以實現“隔墻有耳”甚至“隔城有耳”式的獲取他人通訊信息一樣,在網絡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在網絡的通訊中,由于信息的傳遞是通過一定的網絡進行的,因此通過專用的設備可以實現非接觸式的取證,這種取證方式既不需要直接在物理上接觸被取證人的計算機,也不需要面對被取證人,而是通過秘密手段“潛入”計算機獲取相應的電子數據。這種手段顯然需要在法律的規制內進行,否則一旦被濫用,則可能在多個方面構成對公眾的基本權利構成傷害。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將這種傷害歸為三類:一是對公民通訊自由權的侵害;二是對公民居住權的侵害;三是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與這種可能造成的傷害相伴的是在互聯網時代個人隱私變得越來越脆弱,如有學者所言,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數字化的經濟是網絡化的經濟,信息高速公路把個人計算機、政府辦公用計算機和公司商用計算機串在了一起。個人信息如果進入公眾領域,不管別人是故意公布、疏忽,還是某種方式的盜用,從本質上來講,根均難以阻止或者控制個人信息的散布。尤其是目前信息數字化的情況下,復制和散布都比以前容易得多。
其次,隨著私有和公有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不清,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職能現在承包給私人機構,這意味著由公共部門掌握的個人信息就會流失出去。公共和私營部門共享資料的情形越來越多:比如與銀行共享關于福利享受的個人數據和財務信息,以便確認他們享受福利的資格,這就縮小了公、私部門之間的鴻溝。公眾越來越有可能——至少是潛在地有可能查到詳細的個人信息。
最后,由于許多原來被限定用于軍事用途的技術現在已經被允許用于公共安全甚至轉為民用,則這些技術的觸角便有機會伸向了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個人隱私空間。如英國電信公司正在出口一項技術,該技術能從中央控制區發出指令,利用一條電話線就可以監聽到某部電話附近發生的事情。汽車租賃行業在廣泛使用全球地理定位系統或衛星定位系統。在移動電話方面,則可以容易地跟蹤到使用傳統無線電和微波技術的電話的位置。采用一種被稱為“活動徽章”的技術則可以實時標出建筑物里某個人的位置,并且記錄最后一次跟人聯系時的時間和地點。還有學者預測,以測量器官特征如視網膜外形的“生物統計學系統”將成為監視方法新的趨勢。因此,在這兩方面的綜合作用下,圍繞電子證據取證問題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改良就愈加引人注目。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變化
面對以網絡犯罪為代表的高技術犯罪的嚴重威脅,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一個兼容多重價值使命的規則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這種變化。如果說規范偵查行為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單純意義上的一維價值的話,那么從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利用電子證據與保護隱私權等多個角度考量該規則,則需要從中理出至少一條關于多維價值取舍的底線。
一方面,打擊這些高技術犯罪需要充分利用科技證據,增強公安司法機關收集、審查、判斷運用如監聽數據、測謊結論、電子郵件、電子文檔等電子證據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利用這些證據時必須確保公安司法機關的行為是在法制的界限內進行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一條證據能力的重要評價規則其內容的設置直接關系到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這些證據實現對高技術犯罪的控制。由于使用高科技手段進行偵查的犯罪多是較嚴重的,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往往面臨在多重價值取舍上抉擇。有學者將司法實踐中運用的科技證據按照對個人權利的限制程度的不同,有兩類劃分,其一,利用偵查措施,便能夠從中得到所需的科技證據,比如DNA鑒定結論或者是精神病鑒定結論等。其二,通過對他人的基本權利限制,以此種方式而獲取的數據,比如對個人電子信箱中電子郵件的獲得。該學者認為,由于第一類證據在收集時對人權侵害不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般也不需要對其進行調整。而第二類證據,則需要對相對人在尊嚴、隱私、財產及人身等予以限制,甚至是將之剝奪,因而必然設置一定的底線。上述原則可以作為在排除電子證據時應遵循的一般原則,當然還需要結合具體的取證方式,進一步細化非法證據,將規則對各種偵查手段所造成的制約予以排除。
三、我國非法電子證據的排除規則
所謂非法電子證據排除規則,實際上就是司法機關于案件辦理過程中,不可采用一些非正當方法,來完成電子證據的收集,并且也不能將其當作定案依據。目前,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言,其不僅被聯合國所認可,而且還被世界諸多國家所接受,可謂世界領域內一種相對通用的國際司法準則。根據聯合國所頒布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可知,就能看出聯合國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持肯定態度。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影響,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重視度也呈上升趨勢。但在2010年之前,由于司法領域對于非法證據的關注度不足,針對我國所頒布的各種法律制度而言,其中基本上均會構建起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對于原先頒布的《刑事訴訟法》第43條得知,禁止通過刑訊逼供手段獲取證據,嚴禁通過欺騙、引誘及威脅等方式、方法,來獲取證據,由此可知,在整個原刑事訴訟法當中,僅有進至刑訊逼供這種手段,這僅僅是一種形式意義上的口號,并未在實質方面對于非法證據作出判定與處置。司法機關對于證據來源的合法性審查僅僅停留在表面,而非從刑訊逼供這種非法獲取證據手段下看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本質。1998年,最高法頒布了《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而最高檢則頒布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這兩個司法解釋規定,經查證,認定運用的是刑訊逼供手段,或采用的欺騙、引誘及威脅等不當方式,來獲取的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等,均不可將其當作案件的定案依據。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經由非法途徑所得到的口供,但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
社會各界對于偵察機關采取刑訊逼供手段獲取非法證據致人含冤入獄這一行為深惡痛絕,更是通過新興傳媒進行口誅筆伐。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法學領域的專家學者,都支持構建完備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人們普遍期望以立法方式,對刑訊逼供這一手段給予遏制,對存在與偵查機關當中的各類違法偵查行為進行糾正,以此來更好的對犯罪嫌疑人的正當合法權益提供保護。
基于此,在2010年,最高法聯合最高檢及其它相關部門,頒布了諸多法律規定,即《死刑案件的證據規定》、《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等,對非法證據的范圍作出了詳盡的規定,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當中,其第一條便規定了非法言詞證據必須強制排除。這一規定在我國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相當于里程碑似的地位。
四、總結
總而言之,世界各國已對非法證據排除規給予了高度重視與認可,且均開始著手以法律條文的模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地位。我國在此方面也越發重視,并且在新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對禁止刑訊逼供等內容進行了細致規定,但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方面,仍然需要進行持續更新與完善,此法在《刑事訴訟法》當中所存在的不足情況,使得在司法實踐當中,我國電子證據在合法性方面需經受諸多挑戰。因此,在司法實踐當中,不僅需要將那些非法得到的電子證據給予減少,還需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當中,盡管納入電子非法證據的排除。
參考文獻:
[1]李細珍.我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程序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4.
[2]何家弘.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需要司法判例.法學家.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