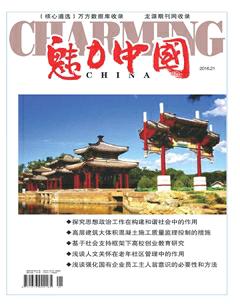《活著》的思想分析
摘 要:中國人講究“福禍相依”的辯證哲學。在《活著》這部作品中,作者以冷漠、有些令人絕望,甚至偏激的暴力敘述沖擊著大眾習以為常的表達形式。主人公福貴由富入貧,由奢入儉,經歷了許多挫折,和家里十二口人的死亡,僅剩自己一人,與一頭老牛為伴,活著在這個世界,好像很孤獨,也好像很平靜。
關鍵詞:生死 思想 苦難 福貴
歷史上從事寫作的人很多,但大多數籍籍無名,一輩子書寫最后還是落寞在泥土里,還有一些人則靠著著作等身,留名青史。余華屬于后者,他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當代作家之一。《活著》則是余華先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一.《活著》與余華
盡管余華早在1995年,就已經發表了《活著》和《許三多賣血記》,但直到1998年他才憑借《活著》獲得意大利最高文學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得以享譽世界,進而受到國內文壇的矚目。目前對外發行的《活著》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中篇小說《活著》,發表于《收獲》的1992年第6期,全篇近7萬字,1994年,電影導演張藝謀看中了這版《活著》,并邀請余華將其改編成電影劇本。余華在原著的基礎上增寫了近5萬字,使之成為12萬字的長篇小說,即《活著》的第二個版本,這是最為廣大讀者所了解的版本,也是我要說的《活著》。
《活著》并不像很多長篇以厚重磅礴見長,余華的敘事單純,語言樸實,幾乎以一種冷靜的筆調完成了整個小說。這正是他貫穿諸多作品的一家風格——偏執的暴力,冷峻的執刀。不知為何,人對于苦難為主題的一切藝術創作都格外傾心,正如叔本華所說的“我們對于痛苦何其敏感,對快樂卻相當麻木”,痛苦使人既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回避,每個人對它都有自己的思考與見解。《活著》通過反復渲染鋪墊福貴的命運多舛,來吐露底層人物的悲苦辛酸:福貴,作為地主家的闊少爺,自幼頑劣,無德無信,父親恨他“不可救藥”,私塾先生斷言他“朽木不可雕也”,長大了準能當個“二流子”。長大后的他也的確如父親老師所說,成了一個敗家子,整日沉溺于嫖娼與惡賭之間,最終將組長留下的家業輸得干干凈凈,父親被他氣死。從此,他痛改前非,兢兢業業,但苦難與厄運從此刻才開始緊緊糾纏他:先是他去城里為生病的母親請郎中,不幸被國民黨的軍隊抓去當壯丁,跟著部隊一走就是兩年。直至僥幸當了解放軍的俘虜,才從戰場撿回了一條命;但他回家后才得知,母親在他離家倆月后就死了。后來女兒鳳霞也因生病成了啞巴。接著是兒子有慶被醫院抽血過多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兒鳳霞產后大出血致死,女婿二喜遇難橫死,小外孫苦根吃豆子被撐死。一連串的家庭悲劇從1940年延伸到1980年,讀完不禁令人感慨,苦海真的無涯嗎?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悲劇便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活著》作為余華轉變對世界、人生態度的標志性小說,“一部形而下的平面敘述和形而上的人生思考并存的小說。”作者這樣描述他的創作本意:“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活著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并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我聽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先后離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的對待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
二.作品的理解與“福貴為何不死”
一部作品從誕生之日起,他就不再只是作家腦海中的文學,經典之所以常讀常新,就是因為總有一批獨具慧眼的讀者,能夠從中讀出自己的新見解。而作品的內涵,也是因為一千個哈姆雷特而豐富。作者其實更像一位讀者,他所把握的也很主觀,甚至有失偏頗。
《活著》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一個賭徒的坎坷人生”。福貴的一生,始終處于一種以生命作賭注與命運賭博的處境,他由開始的一個富家子弟,到輸得一無所有,再到承受失去一切親人的地獄般的經歷,其實是每個人必經的生與死,天堂與地獄。主人公承受了太多苦難與享樂,我們可以稱之為戲劇性的兩種極致人生。但余華越是將福貴經歷的苦難鋪陳得淋漓盡致,他寄寓其中的人生態度就越是朦朧,所以很多人提出了疑問“福貴為何不死?”
我們常常對經歷挫折與苦難的人笑談樂觀,卻難以在置身其中時保持一份淡然。所以,面對福貴那樣的人生經歷,讀者撕心裂肺的同情,但當事人卻平靜的出乎意料,人們難免會不適。如果他道了一聲苦,流下一滴淚,我們便可以理所當然地去表現我們身上的溫暖,力量,安慰。偏偏面對的是無言的承受。是事與愿違,只留下記憶把痛苦刻至骨髓。不由的讓人質疑甚至憤怒。是什么使得人物能夠“從精神上自行閹割其自身對苦難的‘痛感神經”,麻痹的像塊石頭?這種魯迅口中的“僵尸的樂觀”“溫情的受難”,讓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哀其不幸,同其不爭的情緒。
其實,悲劇并非都是聲嘶力竭的控訴與呼天搶地的哀號,大眾的眼光雖然是創作必需的參考,但好的文章還是需要作者獨到的見解,最好的文章,往往是“出其意料卻得乎情理”。余華以其冰冷的筆,在紙張上涂鴉出一幅鮮血淋漓的底層人物受難圖,軟弱,愚昧,落后,消極受難,屈命而活。我們的不適應,我們的疑惑,不正是從反面表達了作者于苦難敘述,虛構表達上的造詣之深?優秀的作品不同于世,但一樣深諳人心。
三.作品中的戲劇性和對待世界的態度
有人說,余華的思想和普通人不一樣,他的筆和一般的作家不一樣。該關心的地方偏偏漠不關心,該憤慨的地方他偏偏無動于衷;該起波瀾的地方他偏偏平靜如水。《活著》中,劫后余生的外孫子苦根在長久的饑餓之后,用“撐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看似荒誕,但不禁悲從中來。還有許多類似的荒誕劇情,“大煉鋼”時期,一村子人聽了小孩子的觀點,竟然置鐵于水中煮,結果卻又陰差陽錯的由于夜晚睡著疏于看管,而煉鋼成功……
我們平時對生死的話題總是避諱。借由小說《活著》的主題,牽扯出很多人對于命運,人生的思考。該怎么活,才能活下去,活得好,活出人樣來。人總是想著自己要做什么,想太久,就容易頓足不前,原地踏步。然后習慣性的使自己置身于一種漫無目的的忙碌狀態,懷著一種事事與我無關的超脫通達,然后留下一堆遺憾,驚醒的回頭,才發現偏離了人生的軌道。于一種茫然中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棲身之處——家庭,一個自己逃離不了的地方。也許這也是整個人類的命運,反反復復的孕育,撫養,孕育,撫養……直到死去,但停止的只是部分,整個鐵定的規律不會止步。
“負下未易居”。生命的誠誠可貴,生活的岌岌相迫,兩者的沖突下奏響的就是余華所表達出來的“活著”。
參考文獻:
[1]張清華. 文學的減法——論余華[J]. 南方文壇. 2002(04)
[2]余華 虛偽的作品[M]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9
[3]郜元寶 余華創作中的苦難意識[J] 文學評論 1994(05)
[4]洪治綱 悲憫的力量[J] 當代作家評論 2004(11)
[5]夏中義 富華 苦難中地溫情與溫情地受難[J] 南方文壇 2001
[6]余華 我為何寫作[J] 文苑 2009(05)
作者簡介:
姓名:李嘉程,出生年月:1994.07.12,性別:男,民族:漢,籍貫(精確到市):山西省晉中市,學歷:本科,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單位所在地(精確到市):湖北省武漢市,單位所在地郵編: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