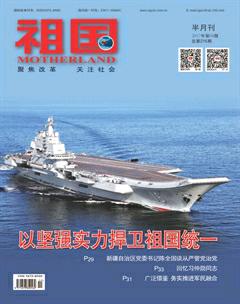功名外衣下的士人悲喜人生
摘要:《儒林外史》以冷峻的眼光審視人間百態,以理性的智慧探索讀書人麻木不仁的精神世界。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勾映射出了科舉制度下士人在窮其生命追逐名利的同時所呈現出的人品、學識及世態人情等多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儒林外史》 科舉 人品 學識 世情
一、通脫平易充滿生活情趣的時代的精神
吳敬梓所處的時代,如胡適《吳敬梓年譜》所言,“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而《儒林外史》的思想傾向與乾嘉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精神氛圍是一致的。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說吳敬梓是他那個時代的思想先驅。
乾嘉兩朝隨著程朱理學的衰落,士人的精神迅速趨于自由率真,他們不再推崇虛假,追求平易、樸實、親切的人生。一批代表作家如吳敬梓、曹雪芹、袁枚、紀昀等不約而同的鄙薄道學先生,不相信所謂超凡入圣的人格;與此同時,飄逸不拘,通脫曠達,富有生活情趣的魏晉風度得到提倡和贊美。并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一種光風霽月的日常生活情趣,一種如長天秋水般澄澈的雅人深致,一種對世事無所芥蒂的夷曠情懷。由于富于生活情趣面向日常生活,所以道德倫理受到重視。道德倫理的作用本來就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維護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轉。乾嘉時期的知識分子常把“人倫”、“日用”并提,如章學誠《原道》:“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以言夫道矣。”對于道德倫理的重視在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中刻下了鮮明的烙印。《儒林外史》所許可的王冕、杜少卿、虞博士、莊征君等都是道德上的完人;馬二先生因其“性行乃亦君子”,作者寫來便多親切之感;而梅玖、申甫祥、高翰林等人因其丑陋的行徑而讓人厭惡不已。
二、士人心態與讀書做官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擔當幾乎責無旁貸的落在知識分子身上。士的人生價值的實現途徑是走上仕途。“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這是讀書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要做官,就必須要贏得君王的賞識。秦漢已降,歷代統治者出于集權政治的需要,力圖削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使他們依附于自己。在統治階級采取的種種措施中以始于隋唐的科舉制度最見成效。
統治階級實行科舉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選拔人才,但在考中科舉即可名利雙收的現實利益的誘惑下,很多讀書人的眼睛只盯著功名富貴。民間社會士農工商兵的社會階層排序,更加刺激了這種價值取向。因此榜上有名即意味著學識過人,從此富貴榮耀;名落孫山則證明了其學識淺陋,遭受白眼。然舉業無憑,功名偶然,于是信命數,信風水;于是,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試官。凡此種種讓吳敬梓痛苦不堪,促使他以一腔悲憫的情懷對此種種丑行予以無情的鞭撻,匯集成了偉大作品《儒林外史》,借此呼喚知識分子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的回歸。
三、功名外衣下的士人形貌
科舉制度為讀書人實現個體價值滿足指明了一條唯一且充滿崎嶇的道路。激勵千百萬讀書人擠上這條道路的是看上去光芒璀璨的功名。伴隨功名而來的是被人仰視的富與貴。圍繞著功名富貴,上演了太多的人間悲喜劇。《儒林外史》展示給我們的則是其中幾個精彩的場景:
(一)中舉——貧富貴賤的分水嶺。明清時代,考中舉人是讀書人成為上層紳士的標志,決定一個讀書人能否贏得功名利祿,所以市井小民打心眼里崇拜舉人,認為他們是“文曲星下凡”。《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前后胡屠戶前倨后恭的言行形象的反映出了這一特點。年過花甲窮困潦倒的范進想去考舉人,因沒有盤費,去同岳父商議,結果被他罵了個狗血臨頭。然而在范進中舉之后胡屠戶自覺女婿是天上的文曲星了,自己和文曲星相比簡直卑微之極,再也擺不出威風凜凜丈人的架子來。后來當范進發瘋使,眾人請他打一個耳光時,他說什么也不敢,怕冒犯星宿死后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民間社會對舉人的迷信心理來源于明清的科舉制度。這一時期的科舉制度分為三級:第一級是院試;第二級是鄉試;第三級是會試。考中院試者稱秀才。秀才是下層紳士的標志。雖然秀才不能做官,但他們從此可以免除賦稅和徭役。考中鄉試者叫舉人。舉人考試競爭非常激烈,往往沒一百名秀才中才有一兩名考中。舉人不僅可以參加會試考進士,即使考不中進士,也能參加“大挑”,或做知縣或做學官,從此進入仕途。因此考上舉人是成為上層紳士的標志,在讀書人的人生經歷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也正因此考了二十多年沒考上的范進中舉后才會喜極而瘋,丑態百出。周進中舉后“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相與。”就連曾經因瞧不起周進而砸了他塾師飯碗的申埔祥也親自制備的賀禮來套近乎。其間的冷暖之情澆薄之態可見一斑。在最高一級的會試考試中考中的叫進士,進士幾乎都能做官,是上層紳士的標志。
(二)人品——權勢利欲的等價物。明清科舉制度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朝廷的本意在于灌輸圣賢之道,而應試者卻將此作為獵取功名富貴的工具。“士習末端,儒效罕著”,教育目的與實際狀況嚴重分離。由于考取功名即可富貴加身高人一等,所以大多數應試者只將《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看作是獵取功名富貴的工具,根本不理會其中的精義。[清]陳灃《太上感應篇.序》切中要害的分析道:“世俗讀《四書》者,以為時文之題目而已;讀《五經》者,以為時文之辭彩而已。” 用“代圣賢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貴,最終“富貴”戰勝了“圣賢”,于是勢利熏心變成了一股在正常不過的社會風氣了。吳敬梓將部分讀書人的墮落、社會風氣的敗壞歸罪于“八股取士”制度。因此,他故意設置了一個與之相反的偏激命題:“不讀書”、不做官,倒有可能保持心靈的高尚與純潔。并在書中塑造了一個“不讀書”不做官的君子系列。
(三)學問——無關功名的奢侈品。一心追求功名的人,其學問有限。《閱微草堂筆記》卷一有一個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話。他以光為喻,認為“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其光“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唯功令文字只是團團黑煙。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沒有學問,這不只是紀昀的看法,明清兩代許多人都持這種見解。[清]顧炎武曾在[日知錄]卷十六中慨嘆:“嗟乎!八股勝而六經衰,十八房(即刻板流行的進士考卷)興而二十一史廢”!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寫范進不知道蘇軾是誰,馬二不知道李清照是什么人,張靜齋胡鄒劉基“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進士出身的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只有八股文。因此科舉考中與否,與應試者的人品學問不相關;不是進士、登高科者就有學問!
(四)世情——功名利祿的試金石。權勢在手時,人們就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權勢喪失了,人們就冷眼相對、無情離去。世態炎涼,古今皆然。《儒林外史》做了非常精妙的展示。當一個破落書生一夜之間成為“天上文曲星”,他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個人功成名就時巨大喜悅,還有周圍人對他態度的急劇變化。所謂“一冷一暖,謂之世情”,吳敬梓對此做了非常精妙的描寫。周進是《儒林外史》中出場很早的人物之一。在第二回中,我們看到這位老童生來汶上縣薛家集教私塾糊口,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年紀輕輕的秀才梅玖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他稱周進為“周長兄”;強調考上秀才的“老友”與沒考上秀才的“小友”是從不論資排輩的,否則就是壞了圣人的規矩。一再嘲諷周進雖“胡須滿腮”卻連秀才都不是。“把周進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周進在觀音庵交伙食錢吃飯,但和尚只給他“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舉人王惠故意在庵中大吃大喝羞辱于他,吃完后揚長而去,留下了滿地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等垃圾讓周進掃,“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幾年后,周進由童生而監生而舉人而進士而部屬學道而國子監司業,他在汶上縣薛家集所呆過的觀音庵也越來越受人們尊崇。觀音庵里一張供桌,供著他的金字牌位,堂屋中間墻上還是周進寫的對聯,盡管因為時間太久,紅紙都已變白。尤其有趣的是,過去稱他為“周長兄”的梅玖,現在見了對聯,卻對和尚這樣發話:“還是周大老爺親筆,你不該貼在這里,那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才是。”由周長兄而周老師而周大老爺,梅玖對周進的稱謂隨周進的升遷而升遷,煞是耐人尋味。人情勢利,世情澆薄。權勢在手眾人趨之若鶩;權勢喪失即眾叛親離。悠悠濁世,古今皆然,我們可以從《儒林外史》中窺斑見豹!
參考文獻:
[1]李漢秋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3]張國風.《儒林外史》試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2.
[4]陳文新,魯小俊.且看長河落日圓——《儒林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吳招弟,助教,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陜西警官職業學院,研究方向:唐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