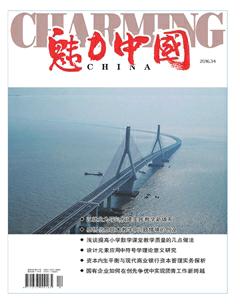歷史故事的舞臺化演繹—淺析林兆華版與田沁鑫版話劇《趙氏孤兒》的藝術形式
鄭新然
【摘要】《趙氏孤兒》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話劇《趙氏孤兒》是第一個把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引入當代話劇舞臺的作品。本文通過分析2003年林兆華與田沁鑫分別導演的兩版《趙氏孤兒》話劇,將趙氏孤兒的歷史故事重新審核,分析當下歷史故事的舞臺化演繹。
【關鍵詞】話劇;舞臺;敘事;人物
在《史記》的《趙世家》篇中記載這樣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趙氏先祖在晉景公三年慘遭族誅之禍,趙朔與趙莊姬的遺腹子在程嬰和公孫杵臼的幫助中僥幸躲過了這場滅門慘案,這個孩子長大后,在韓厥等人的幫助下將趙氏宗族的地位恢復起來,這個故事便是“趙氏孤兒。”趙氏孤兒在宋元時期被紀君祥改編成元雜劇,從此廣為流傳。而在二十一世紀,它被林兆華、田沁鑫兩位導演改編成了話劇形式搬上了舞臺。經歷了長時間歷史的沉淀與不同形式的改編,《趙氏孤兒》的故事在現代話劇的改編上也給導演們更多的改編和演繹空間。林兆華版與田沁鑫版的話劇《趙氏孤兒》便分別以不同視點角度以及側重為“趙氏孤兒”的故事帶來新的主題意義。
關于這兩版話劇,從直觀的舞臺場景上說,田沁鑫導演的《趙氏孤兒》注重西方現代戲劇觀念與東方藝術審美的結合,強調整體舞臺空間的拓展。例如升降幕布、移動隔斷等舞臺道具的使用,田沁鑫導演通過控制它們位置的移動和變換,來塑造出不同的舞臺場景與空間結構,并通過沉重的“黑”與靚麗的“紅”這兩種色調的運用——亮麗“紅”與沉重“黑”來提煉話劇敘述的整體氣氛,給觀眾一種直觀的冷艷的視覺畫面,通過舞臺布景展現話劇的風格特色,從而配合情節來完成敘事上的倒序式回憶和插敘式復仇前史的講述。
而林兆華導演則不同,他所導演的《趙氏孤兒》更體現出了他“輕內容而重形式”、“輕實在而重空靈”的新世紀導演特征,從而創造了一種唯美視覺的造型形象。該劇從直觀的舞臺布景上便令人嘆為觀止,他采用了巨大的舞臺表演場地,演出開場時灰暗色凝重的危巖峭壁與紅色的沒有任何空檔的臺面構成一個大直角,營造出的舞臺縱深帶給觀眾最直觀的外在感受。他沒有變換的幕布和幕板,所有的幕與場的切換大多由燈光控制來將舞臺分區,使分場切換得流暢自然、敘事緊湊。舞臺在變幻莫測的燈光以及陰影的渲染下,彌漫著一種讓人不寒而栗的氣氛。同時在舞臺藝術上,林兆華版多用真實的事物作為道具,讓舞臺上一切真實事物如實地反映現實。例如開場出現在舞臺后方的一匹白馬、征戰場景中演員身騎戰馬手舉戰旗、最后一幕中舞臺上從天而降的瓢潑大雨等,都制造了話劇舞臺上少有的視覺奇觀。
從敘事邏輯上說,林兆華、田沁鑫兩位導演同樣都把敘述重點放在了從趙家被屠岸賈滅門到趙氏孤兒死里逃生這一極具張力的前史中。林兆華版《趙氏孤兒》由劇中人物程嬰的敘述開場,順序講述了這一事件中所牽連的人物及結局走向;田沁鑫版《趙氏孤兒》則是以孤兒的夢境和自述開場,在觀眾的全知視角下采用焦點人物的眼光進行敘事,但在焦點人物并不是全知敘述者,從而使得觀眾對人物得以重新認識和解讀。比起林兆華版的順序流暢、由因及果的完整性,田沁鑫把敘述的起點安排在了臨近故事結尾的地方——十六年后趙氏孤兒已經長大成人的節點,使得故事情節向著順序和倒序兩個方向展開,讓不同的情節緊密聯系起來,也讓敘事移情更加方便。
從情節內容與人物塑造上說,田沁鑫導演倡導“歷史即當下”,她希望能借助《趙氏孤兒》話劇的現代演繹喚起當代社會的誠信。所以在情節內容的安排下,她增加描述程嬰衷腸義膽的篇幅,全力塑造了程嬰這樣一個有悖中國傳統宗法倫理——棄親生子不顧,而將他人孩子撫育成人的平民化悲情英雄角色。在當今以社會競爭為主流的殘酷現實中,善良和誠信都會遭到質疑,但她提倡的依舊是程嬰的義薄云天。同樣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田沁鑫更注重通過人物動作的夸張來刻畫人物之間的矛盾和糾葛,特別注重演員的肢體語言在舞臺上的表現。同時在服裝裝扮上,田沁鑫版《趙氏孤兒》略有后現代裝扮的感覺,通過服飾、裝扮以及演員表演的內在氣質展現出人物獨有的精神面貌。例如在韓童生所扮演的屠岸賈這一角色中,演員頭頂一頭灰白色的披肩發,凌亂不整、時而擋住半邊臉,身著以紅、黑為主基調的服裝,象征著權勢與罪惡之血并存,由此通過外在的裝扮展現出屠岸賈假面下內心的陰冷與自身的折磨;而倪大紅所扮演的程嬰,頭頂少發、身著藍白相間的素服,衣衫襤褸卻一臉嚴肅堅毅,展現出程嬰義薄云天的大義凌然。就像田沁鑫推出的一本收錄該劇本的書——《我做戲,因為我悲傷》,書中她說道:“我做戲,因為我悲傷。悲傷于現今社會的混亂,私欲的彌漫,道德底線的幾近崩潰,思想的覆滅,禮節的丟失。”這版話劇就像個叛逆的搖滾女子, 充滿了爆發力以及重整時代的激情。
而在林兆華版《趙氏孤兒》中,“孤兒不復仇”的結尾著實是一個顛覆性的主題。在情節內容上,林兆華多處渲染趙盾與屠岸賈二十年的恩怨情仇,利用觀眾的同情心潛移默化中為屠岸賈殺趙氏全家找到一個合理的“復仇”借口。而這部劇中的孤兒本人遲遲未出現,等到臨近結尾處出現時,他不像是趙氏孤兒本身,卻更像是程嬰養育多年為了復仇而長大的工具,但悲哀的是這個工具卻沒能完成他的使用價值。林兆華表示,他不想在這出話劇里表現“愚忠”和“愚孝”,也沒有所謂的正義與邪惡,而是著力表現孤兒面對人生的兩難抉擇,來讓該劇從“忠”與“義”的模式中轉變出來,把重點放在了對于個體的反思。這個顛覆傳統反思歷史的結尾,更像是一個現代性的結局,對劇中那些你死我活的搏殺以及鐵膽忠腸的報復是一種莫大的嘲諷,在林兆華導演的《趙氏孤兒》中,程嬰便成了是這個出乎意料的結局里最大的悲劇人物。
由此可見,對于歷史故事《趙氏孤兒》的解讀,不同導演在文學改編、藝術形式以及展現的細節中都融入了獨特的、發人深省的思想內涵,話劇乃至更多其他影視演繹之路的探索也將經歷歷史與現代思想的多重考驗。
參考文獻:
[1]陳白塵、董健,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2]譚雪生,話劇藝術概論,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
[3]田沁鑫,我做戲因為我悲傷,作家出版社,2003.
[4]陳軍,怎樣欣賞話劇的藝術性[J],財政監督,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