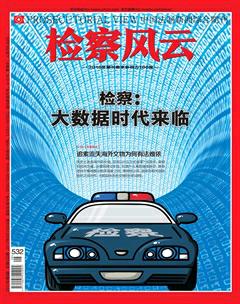網絡尋釁滋事犯罪實證分析
劉強
網絡信息傳播門檻低、自由程度高、互動性強的特點為言論自由提供寬松環境的同時,也滋生出各種網絡虛假信息。網絡虛假信息具有傳播速度快、波及范圍廣、查證難度大、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和公眾恐慌的特點,這使得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危害比傳統尋釁滋事犯罪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治理網絡虛假信息、打擊網絡尋釁滋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月制定了《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方面為打擊網絡尋釁滋事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另一方面明確了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法律界限和法律適用標準,推進了網絡法治的進程。
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實證分析
筆者選取了近年來,經媒體報道的影響范圍較大的50起網絡虛假信息事件,分析了網絡虛假信息的內容類型、發布平臺和動機目的:
1.內容類型
從網絡虛假信息內容類型來看,主要分為煽動危害公共安全、攻擊政府、捏造夸大災害性事故、破壞經濟秩序等內容。其中居于前三位的是煽動危害公共安全(23件)、攻擊政府(12件)、捏造夸大災害性事故(6件),占82%。根據統計,除部分丑化名人事件外,大部分網絡虛假信息事件不存在損害他人人格、名譽的情形,所以網絡尋釁滋事與網絡誹謗存在著明確界限。另外,通過內容類型的分析,還有助于分析網絡尋釁滋事的社會影響和危害后果。
2.發布平臺
從網絡虛假信息的發布平臺來看,網絡論壇成為網絡虛假信息的重災區,占52%,微博作為新興的自媒體也成為網絡虛假信息傳播的主要平臺,占26%。顯然網絡論壇的公共性和影響范圍較之于自媒體的微博、微信、QQ更大,其波及范圍和產生的社會后果也就越大。
3.動機目的
從動機目的來看,主要為吸引關注(76%)、牟取利益(11%)和報復泄憤(9%),尋求刺激(4%)。對動機目的的考察有助于認定網絡尋釁滋事的主觀動機,是區分尋釁滋事罪與敲詐勒索罪、非法經營罪的重要因素。
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成因分析
網絡謠言產生的原因復雜而多樣,主要有:一是網絡技術的發展為網絡謠言提供了生存土壤,特別是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自媒體的普及,使違法分子散布謠言的成本越來越低、影響范圍越來越大、傳播時間越來越短,同時被發現和查實的幾率也越來越小;二是網絡時代信息失衡使真相驗證難度增大,網絡特有的自由言論空間使得任何信息可在短時期內大規模傳播,而驗證信息的真實性卻需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三是網絡謠言的行為成本過低以及法律監管缺位,網絡謠言的傳播者往往可以通過微小的成本實現對謠言的制造和傳播并且不被發現,而懲治力度的不足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網絡謠言的蔓延。
處理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原則
1.客觀把握刑事可罰性
網絡尋釁滋事不僅破壞了網絡空間的秩序和規范,還會造成現實公共秩序的混亂,若影響和波及的范圍較大,進而引發群體性事件,損害國家形象,危害經濟金融秩序穩定時,自然需要刑事法律的介入,也就具有了刑事可罰性。
在肯定網絡尋釁滋事行為的刑事可罰性的同時,也要客觀把握刑法介入的尺度,在可罰與不可罰之間尋求刑法價值實現的最大化,防止因為過分擴大打擊面而侵害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言論自由權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和規制最終要通過具體的部門法來實現,就刑法而言,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發揮其作用:其一,處罰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犯罪;其二,貫徹罪刑法定原則,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的運用保護公民自由、權利的實現。我國刑法有關言論自由的規定可以分為限制言論自由的犯罪和保護言論自由的范圍,前者包括侮辱、誹謗、煽動、教唆類犯罪,后者則涵蓋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和報復陷害等犯罪。
公民依法在網絡上發表言論,行使憲法權利,受我國法律的保護。但網絡上的言論自由也并非沒有邊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會允許有煽動國家分裂、侮辱、誹謗他人的“言論自由”。在互聯網發源地的美國,早已明確將互聯網世界定性為“與真實世界一樣需要進行管控”的領域,并先后出臺130多項涉及互聯網管理的法律法規。2011年8月倫敦爆發騷亂,那些通過網絡社交媒體鼓勵騷亂的人事后都依法受到了懲罰。在德國,按照相關司法規定,所有現實社會通行的法律規定也適用于互聯網。德國是全球第一個發布網絡成文法的國家。德國的許多法律中也包含互聯網行為和言論的專門條款和內容。1997年,德國出臺了《信息與通信服務法》,隨后又逐步完善了涵蓋10余類法律內容的互聯網管理體系,這些法律明確規定了互聯網言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犯罪事實。
《解釋》的出臺,實際上設定了在信息網絡上發表言論的法律邊界。但同時,刑法介入應保持歉抑與理性,應當盡可能少的用刑事強制措施來維護社會秩序,盡可能多的保留公民個人的言論自由。所以,要審慎評估網絡尋釁滋事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從嚴打擊社會危害性大的案件,而對于一些社會危害性小的網絡尋釁滋事則留給網絡進行自我的信息糾正或者通過民事侵權途徑予以調整和解決,刑法應保持克制和容忍,以最小的控制犯罪成本達到最大限度的遏制犯罪,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的統一。
2.明確網絡各類主體的責任邊界
制止網絡虛假信息如果僅僅依靠網絡空間的道德自律顯然是不夠的,針對惡意制造和傳播網絡虛假信息的人應通過追究法律責任來規范網絡空間秩序,凈化網絡環境。201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比《解釋》更進一步的是該規定明確了非法刪帖、網絡或者自媒體轉發等行為的責任。這一規定積極回應了近年來伴隨著微博、微信等個人自媒體高度發展后出現的各類網絡侵權行為的追責。該規定明確,法院認定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轉載網絡信息行為的過錯及其程度,應當綜合以下因素:轉載主體所承擔的與其性質、影響范圍相適應的注意義務;所轉載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權益的明顯程度;對所轉載信息是否作出實質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標題,導致其與內容嚴重不符以及誤導公眾的可能性。這意味著網站、個人自媒體,特別是網絡大V,可能會因為未盡審慎注意義務而轉發網絡虛假信息而被追究責任。
微博、微信等近幾年迅猛發展的社交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自媒體,在傳播范圍、影響力等各個方面均有超出傳統媒體之勢,在信息傳播的主體上,往往是自媒體先發出聲音,產生影響后,傳統媒體再跟進。從技術手段來講,微博平臺突破了以往傳統媒體的線性傳播和網絡媒體的網狀傳播,形成了其獨特的鏈狀、環狀、樹狀的對話結構,從而為謠言的迅速傳播、聚合和裂變帶來了可能。可以說,微博的出現使網絡虛假信息制造者變得越來越猖狂,借助微博平臺,網絡虛假信息的發布在幾秒鐘就可以完成,并且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影響力。網絡水軍、網絡大V、個人自媒體等都有可能因為各種目的而成為網絡虛假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
針對網絡虛假信息的上述傳播特點,當網絡虛假信息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時,就需要進一步明確網絡虛假信息的制造者、傳播者中涉及的各類主體的責任邊界:針對網站以營利為目的對明知是虛假的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布服務,擾亂市場秩序的,以非法經營罪認定;針對個人或者網絡大V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以尋釁滋事罪處罰;針對一些提供資金、場所、技術支持幫助的人,在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的,為其提供資金、場所、技術支持等幫助的,則以共同犯罪論處。
3.準確區分此罪與彼罪的關系
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其通過網絡這一媒介實施了尋釁滋事行為,由于有網絡這一媒介存在,在司法實踐中就很容易與其他網絡類犯罪相混淆,所以在懲治網絡尋釁滋事犯罪過程中,需要準確區分此罪與彼罪,把握刑法條文之間的內在關系。事實上,要區分網絡尋釁滋事犯罪與破壞網絡秩序犯罪,關鍵是兩者所保護的法益不同,網絡尋釁滋事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公共場所的秩序安全,而且是現實生活中的公共場所秩序,而破壞網絡秩序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網絡的服務和運行秩序,破壞網絡秩序的行為應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非法侵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的行為,是對網絡系統或者設施的物理損壞。
從行為本身的性質來看,構成網絡尋釁滋事犯罪的同時有可能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罪名,那么就應該按照法條競合的原理來認定構成何罪,而不能一味利用網絡尋釁滋事犯罪條款的“口袋性”而適用該罪名。《解釋》第九條規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犯罪,同時又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的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此外,如果網絡傳播虛假信息而導致危害國家安全時,也可能構成刑法分則第一章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罪。
編輯: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