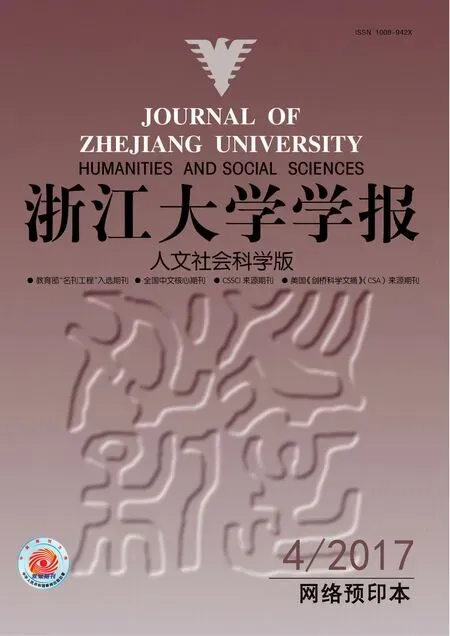美國“再工業化”的國家安全含義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余功德 黃建安
(1.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北京 100720; 2.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主題欄目: 非傳統安全問題研究
美國“再工業化”的國家安全含義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余功德1黃建安2
(1.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北京 100720; 2.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再工業化”是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經濟重建的重要內容,是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和重要轉向的標志。長期“去工業化”導致美國經濟上的過度虛擬化、社會上的貧富分化對立、政治上的兩極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美國夢”危機,對美國國家實力造成了系統性的損害,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了全局性、結構性的挑戰,威脅到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理制造業問題,這是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戰略的深層次原因。“再工業化”遠不止是一項經濟戰略,同時還是一項安全戰略,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具體體現,蘊含著對華戰略沖突的性質和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增強的意味。“再工業化”也不僅僅是應對金融危機的一種權宜之計,還是一次兼具長遠意義的戰略轉折。當然,這并不是說美國政府一定會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目標,是否去做與能否實現是兩回事。
美國; 再工業化; 國家安全; 對華影響
關于美國正在發生的“再工業化”政策轉向,國內學術界很早就予以了關注,如金碚、劉戒驕在2009年就指出,美國出現這方面的動向,有可能對我國制造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提醒國內注意[1]。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美國“再工業化”實質的分析、美國“再工業化”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以及對我國產業發展的啟示等幾個方面。關于對美國“再工業化”實質的分析,學者們主要形成了經濟視角的“產業升級觀”、社會視角的“就業問題觀”、政治視角的“選舉需要觀”等幾種觀點。“產業升級觀”認為,美國“再工業化”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空心化問題嚴重、制造業競爭力下降,主要目的是為了構筑新的制造業競爭優勢,占領未來產業制高點;“就業問題觀”認為,失業率居高不下是美國推行“再工業化”的重要原因;“選舉需要觀”認為,選舉因素是美國提出“再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出于選舉宣傳需要而形成的政治作秀,并無實質內涵,更無實施的長期計劃[2]。這些觀點在對美國“再工業化”的認識上,大多是圍繞著奧巴馬政府振興制造業的計劃和政策來進行的,忽視了對其背后的國家戰略因素的考察,對美國這次政策調整背后深層次的戰略動機和決策邏輯的系統揭示仍顯不足[3]。本文試圖從國家安全的視角,來發掘美國“再工業化”背后的國家戰略意義,并探討其對中國的影響。
一、 美國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進
“國家安全”是國際政治及其研究領域的核心概念。傳統上,國家安全一般指國家對外來攻擊進行抵御,主要側重于軍事領域,對軍事威脅進行軍事防御。美國報紙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于1943年首次提出并定義了國家安全,他認為國家安全是“在國家希望避免戰爭時,能免于必須犧牲核心價值的危險;在受到挑戰時,它能通過贏得戰爭的勝利來保護這些核心價值”[4]51。
但對于國家安全是否有確切的含義以及我們能否確切地定義國家安全,國際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5],這與國際學術界對“安全”概念的認知密切相關。美國學者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認為,安全是一種活生生的外皮,它所應用的時間和環境不同,它的色彩和內容就截然不同[6]24-25。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指出,安全不太可能被客觀地衡量,主觀認識往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7]。他認為,“安全,對既有價值來說,是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8]。一些著名學者,如巴里·布贊(Barry Buzan)、丹尼爾·費雷(Daniel Frei)、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等,否認安全有確切的定義,認為它不過是一個模糊的象征[9]2-3。他們認為,不同的行為體,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問題,會對安全做出不同的解釋,任何一個概念的界定都難免以偏概全,所以闡釋安全的含義只能聯系具體的情況[10]。基于對安全概念的這種認知,學者們認為,要給國家安全下一個普遍適用的定義也是困難的,因為同樣,不同的行為體,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問題,會對國家安全做出不同的解釋。如沃爾弗斯就指出,“國家安全是一個模糊的象征”,“對不同的人群可能不意味著同樣的事情,可能根本就沒有精確的含義。因而,當用來提供指導和基礎,以達到廣泛共識時,就可能被每個人用一個有吸引力的或欺騙性的名字,為其貼上任何他所喜歡的政策的標簽”[8]。
因此,國家安全的概念有其特殊性,不同的行為體對國家安全做出不同的解釋和界定,本質上是國家安全觀問題,這導致了各個國家之間在國家安全觀上的差別。
首先,國家安全具有主觀性。國家安全源于客觀的威脅和危險,但也取決于安全主體對這種威脅和危險的認知,而認知問題又因國家的歷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這里存在兩種極端現象:一是外部威脅和危險客觀存在,安全主體卻沒有意識到;二是本沒有外部威脅和危險,但安全主體卻認為其存在。
其次,國家安全具有動態性。一方面,外在的威脅和危險往往是多種多樣的,也是動態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會面對不同的問題;另一方面,安全主體對威脅和危險的認知也是各種各樣和動態變化的。兩者的結合,使得不同的安全主體往往會有不同的威脅和危險判斷,即使有相同的判斷,也可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第三,國家安全具有相對性。國家安全往往基于對國家實力和國家利益的判斷,各國的實力強弱不均,且此消彼長,應對威脅和危險的能力和手段也不一樣,因此對具有不同實力和利益訴求的國家來說,國家安全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最后,國家安全具有戰略性。“一個國家的安全都是一個廣泛的范圍,從一極的幾乎絕對不安全或不安全感,到另一極的幾乎絕對安全或沒有恐懼。”[8]一個國家究竟在這兩極之間選擇何種安全觀,實際上還要受其戰略文化的影響。崇尚強權的國家往往秉持絕對安全觀,對這些國家來說,國家安全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幌子,即使它在現實中受到的實際威脅或危險很小,它也可能去尋求絕對安全,以滿足其“獲得高位、尊敬、物質財富和特權等的國家欲望和野心”[8]。
粗略來看,美國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進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當然,各個階段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
第一階段,從美國建國伊始到19世紀末。這個階段,維護年輕共和國的生存和獨立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不管是在客觀上,還是在美國政府的主觀認知上,威脅和危險的來源都是歐洲大陸的強國,主要是英國。在安全內容上,傳統的軍事防御是主旋律,“美國的總統們年復一年地向國會強調加固海岸線以防備入侵者的重要性”[11]97。在安全手段上,美國除了積極的軍事防御之外,還采取了相輔相成的兩項戰略:一是在與歐洲大陸的關系上,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提出的“孤立主義”原則被奉為圭臬;二是這一時期,美國奉行大陸擴張政策,邊界從東海岸擴展到西海岸,并積極與世界各國開展貿易關系,到19世紀末,美國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世界首位。
第二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階段,美國開始角逐世界大國的地位,并在兩次世界大戰后一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在安全內容上,這一階段雖說仍是傳統的軍事安全,但美國對國家安全的關注已不再只是局限于自己國土的狹小范圍,而是開始在鞏固西半球霸權的基礎上放眼全球。在西半球,從19世紀70年代后,美國就越來越多地采用“門羅主義”調停拉美國家爭端,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幌子稱霸。在世界上,主要是在歐洲,美國將努力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作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保障,在均勢被打破時,兩次參加世界大戰,恢復歐洲的權力平衡。在安全手段上,在西半球,美國更多地使用了武力干涉;在世界其他地區,則是在運用武力的同時,力圖落實“集體安全”。
第三階段,“冷戰”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對國家安全的看法,在威脅和危險的來源和目標上更具全球性,內容上大大擴展,手段上更為綜合。“冷戰”初期,美國確立了“遏制”戰略,將蘇聯及其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宣稱美國國家安全是“保證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國家而存在,其基本制度和價值不受破壞”*P.L.80-235, 61 Stat 496,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July 26, 1947.。在安全內容上,這一時期盡管仍帶有傳統軍事防御的特征,但已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威脅放在了幾乎同等重要的位置。不管是蘇聯的軍事力量,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美國而言,其威脅都具有全球性,這一判斷貫穿“冷戰”始終,直到1987年,美國政府還宣稱“對美國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威脅是蘇聯所提出的全球性挑戰”[12]10。在安全手段上,傳統的軍事防御仍然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但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社會、心理以及意識形態等都被美國政府統籌在對蘇聯軍事防御和“遏制”的總綱之下,經濟援助、文化交流以及“心理戰”都被作為補充手段,這充分體現在這一時期詳細規劃了美國“冷戰”戰略的《克利福德報告》上[13]。
第四階段,“冷戰”結束后新的全球化時期。這一時期,“冷戰的結束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安全需要”[12]243,美國的國家安全觀經歷了重大變化。在安全目標上,從“冷戰”時期更多地強調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轉而強調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美國整個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也都圍繞著這個目標來進行。在安全內容上,對威脅和危險的判定日益擴大化。此時,蘇聯及其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這個壓倒一切的威脅不在了,很多新的威脅,如恐怖活動、毒品走私、環境破壞、跨國移民、“流氓國家”、經濟安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漸成為美國政府關切的對象。在安全手段上,也更加復雜多樣化,時至今日,“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等概念層出不窮。
縱觀美國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化,可以發現,美國國家安全觀前后呈現較為明顯的泛化趨勢。國家實力與國家利益的“二重唱”,是美國國家安全觀這種泛化趨勢的背后主線。“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是維護和推進國家利益的廣泛目標的陳述”[12]7,美國國家安全設定什么目標,取決于美國如何判定自己的國家實力和國家利益。這樣,在安全的整個光譜中,當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將國家安全置于最狹窄的一端的時候,美國則將一些“邊緣價值”都上升為國家的安全關切,進而提升到國家的安全戰略層面進行處理,以維護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也就是說,美國對世界霸權地位的迷戀,使得國家安全對美國來說更像是一塊幌子,它的泛化是在為美國尋求不合理的國家利益張目。這充分體現在“冷戰”后期開始的美國歷屆總統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中,這也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基本邏輯。美國制造業的國家安全內涵及其所引起的“再工業化”的爭論和努力,就內生于美國國家安全這個基本邏輯之中。
二、 美國國家安全中的制造業
一般來說,制造業屬于經濟議題,但制造業又有其特殊性。在現代社會,制造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形態之一,而且是現代國防和戰爭的基礎,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對美國來說,制造業很早就上升為一個國家安全議題,這與聯邦黨人的主張是聯系在一起的。
美國獨立之初,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工業很不發達。而當時,美國雖已獨立,但仍處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之中,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美國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意見也不一致,以杰斐遜為代表的共和黨人醉心于建立一個自耕農為主的共和國,而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人則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聯邦,并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保護商業活動[14]24-26。雙方爆發了一場大論戰,結果是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的主張在總統華盛頓的支持下占得上風,贏得了國家政策的主導權。1790年初,華盛頓在第一次向國會發表咨文時講到:“一個自由的民族不僅應該武裝良好,而且應該嚴守紀律,為達此目的,一個統一的、融會貫通的計劃是必不可少的:他們的安全和利益要求他們應該推動這樣的制造廠,以使他們在必需品特別是軍事供應上實現獨立。”[15]7天之后,參議院要求財政部就總統的指示向國會提交報告。1791年12月,時任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就發展制造業問題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報告[16]。在這份報告中,漢密爾頓提出:“不但國家的財富,而且國家的獨立和安全,都與制造業的繁榮實質上聯系在一起。每一個國家,在這些偉大目標上,都應該努力使其自身擁有國民供給的所有必需品。這為生計、住所、衣著和防衛等方面提供了必要途徑。”[17]顯然,在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看來,發展制造業同時也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是確保美國海外商業利益、促進國家自立、保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在漢密爾頓報告提交國會的5個月內,他所建議的各種措施都被國會以零散而非一攬子的方式付諸實施。在麥迪遜任內,財政部長加勒廷于1809年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其中的舉措與漢密爾頓的報告如出一轍。這個報告被國會通過,確立了美國通過獎勵金、進口稅和政府貸款保護和發展制造業的基本框架[16]。此后,美國制造業在這個框架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19世紀末,美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此時,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關系也得到緩和,并且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將西班牙驅逐出了西半球,美國的國家生存和獨立已不再受到嚴峻挑戰。取而代之,美國開始加入到大國政治的角逐之中,制造業開始服務于美國的國防建設和軍備擴張。到一戰、二戰,美國工業能力的優勢顯現出來,尤其是在二戰期間,美國龐大的工業能力對戰爭的勝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940年底,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號召美國加強國防工業生產,提出“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18]。接著美國出臺“租借法案”,向英法等盟國提供軍事援助,隨后又擴及蘇聯、中國等國家,有效地支援了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這一階段,制造業直接服從于國家戰爭的需要,“鉚工羅西”成為美國制造業在戰時總動員中的象征。
“冷戰”的開始,使美國轉而在對蘇遏制的框架下來思考制造業問題。蘇聯及其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被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這一威脅,按照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的說法,“克里姆林宮向美國的挑釁,在邏輯上和事實上,不僅針對我們的優點,還針對我們保護環境的物質能力”[19]274。這與蘇聯強大的工業和軍事能力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國遏制戰略的總體設計中,制造業成為重要一環,它既服務于美國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建設,又服務于政治和經濟制度建設,以便使美國及其主導的西方世界獲得相對于共產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優勢。《1950年國防生產法》很好地反映了“冷戰”時期制造業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角色。不管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制造業都是服務于美國國家實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同時,通過國家實力的提升,制造業又具有了意識形態上的意涵:它的有效運轉證明了美國制度比蘇聯制度更為優越,而美國制度的核心則是“自由”,與之相對的是蘇聯的“奴役”。
“冷戰”結束后,制造業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角色得到了延續。美國基本上保留了《1950年國防生產法》的工業管制條款,對戰略競爭對手,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美國仍然執行嚴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與國防有關的高新技術領域。略微不同的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維護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成為歷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制造業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地位通常是在維持美國世界霸權的邏輯下設定的。制造業被看作是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三根基本支柱之一(另兩根是軍事力量和美元)*J.F.Morton,″Toward a Premise for Grand Strategy,″ in R.R.Sheila(ed.),Economic Security: Neglected Dimen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3-61.。
三、 長期“去工業化”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挑戰
長期“去工業化”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與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在全球化經濟時代,由于外部的激烈競爭和內部的抗爭(最典型的是工會勢力),美國的資本家為了追尋更高的利潤和在競爭中取勝,出于市場、勞動力、生產資料等因素考慮,逐漸將生產轉移到了更具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主要以直接投資、外包或離岸等方式)。這個進程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初具規模,在這一波中被轉移出去的產業主要有制鞋、制衣、廉價電子產品、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制品,以及汽車制品等。
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國內制造業投資被對外直接投資趕超,制造業就業比重持續下降,生產率止步不前,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的地位和競爭力下降,“去工業化”問題開始引起美國朝野的普遍關注。不論是官方還是學界,都在積極研究應對之策,部分人士提出“再工業化”,要求恢復和提高制造業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20]223。1980年6月,美國《商業周刊》刊文指出,“美國如果要保持一些經濟活力,要保持領導地位,美國經濟必須進行根本變革。其目標必定是美國的再工業化”*Anon.,″Revitalizing the U.S. Economy,″ Business Week, June 30,1980, p.56.,美國上下掀起了一場有關“再工業化”的激烈爭論。卡特和里根兩位總統還曾將“再工業化”作為政策選擇。但后來卡特輸掉了大選,沒有機會將他的主張付諸實施,而里根則堅持用“供應經濟學”的辦法來解決美國的工業問題。隨著“冷戰”的結束,互聯網等美國軍用技術轉為民用,“新經濟”得以展開,當時的爭論也隨之沉寂,并未在政策層面帶來根本性的調整。
此后,全球化進程加快,特別是“外包”的廣泛運用,美國“去工業化”趨勢持續增強,美國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萎縮,基本上依靠世界市場來滿足需求,同時中高端產業也開始出現向外轉移趨勢。20世紀以來,美國經濟走向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美國中低端產業以更快的速度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高端產業也日益與全球市場聯系在一起,以至于美國商業工業委員會(USBIC)將2000—2010年這十年稱為“去工業化的10年”[21]。
從比較利益來講,通過產業轉移,美國資本家實現了個人收益的最大化。但從長遠來看,這種產業轉移對美國自身來說卻帶來了矛盾的結果:一方面是有利的,美國轉移了低端制造業,降低了生產成本,贏得了市場,可以獲得廉價制成品進口,可以專注于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和金融等服務業;另一方面又是不利的,產業轉移帶走的畢竟是生產能力,會導致國家生產能力下降,對國外制成品形成依賴,同時可能帶來失業以及財政和貿易赤字等問題。更主要的是,產業轉移目的地(如中國等)也借此機會奠定了自己的產業基礎,快速實現工業化,并不斷向產業鏈的高端挺進,從而對美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地位構成挑戰。
不僅如此,產業轉移的負面效應也反映在了美國的社會層面。伴隨著產業轉移的持續進行,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過度虛擬化”的趨勢,因此,就業結構也相應地向兩端集中,國內的高端產業可以為受教育程度高、技術水平高的國民提供就業,低端的就業依靠公共雇傭,中端的就業則因大量制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而面臨工作崗位不足的威脅。由于缺乏良好的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就業結構的兩極化帶來的是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劇,從而催生社會對立。
而社會的對立又通過民主政治體制傳導到了美國的政治層面。一方面,在產業轉移中獲益的大資本會通過代言人維持有利于產業轉移的稅收、外貿等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工會組織會發起抗爭,要求改變產業轉移的趨勢,底層民眾也會因為失業、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而掀起社會運動。這種社會對立體現在政治層面,表現為美國政治兩極化的加劇。
同時,經濟上的過度虛擬化、社會上的貧富分化對立和政治上的兩極化又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含義,美國中產階級面臨重重困境,日益萎縮,“美國夢”遇到了挑戰,它削弱了美國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引發意識形態危機。
從美國國家安全的邏輯內涵來看,長期“去工業化”給美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帶來的負面影響,無疑是對美國國家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系統性的損害,也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全局性、結構性的挑戰。這個挑戰將是長時期內美國政府不得不面臨以及應對的問題,不論美國政權發生什么樣的更迭。換句話說,“問題決定議程”,不管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上臺,出于國家戰略競爭的需要,都必須去面對并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具體而言,面臨的問題表現如下:
(一) 經濟上的過度虛擬化
一是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并存,危及美國財政和經濟安全。二戰以后,美國曾長期保持較低的債務水平,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內也維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下。但進入20世紀,到2011年末,美國聯邦政府的總債務已經達到創紀錄的14.8萬億美元,與2001年的5.8萬億美元相比,增長了9萬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98.7%。在這個高速增長的債務市場中,外國政府和機構持有的美國國債是關鍵因素,其中外國政府和機構持有的美國政府聯邦債券就占了41.6%[22]。而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與其龐大的貿易赤字又有著內在的聯系,外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國際貿易逆差的轉化。美國的貿易逆差來源主要是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則保持小幅順差。在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各產業格局中,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制成品的貿易逆差占據了主要份額。從2000年到2005年,美國制成品的貿易逆差都保持在貿易逆差總額的70%以上,2006年至今,除了2008年因為進口大幅下滑之外,均保持在60%-70%之間。可以說,制成品的貿易逆差構成了美國貿易逆差的大部分成因。這凸顯了長期“去工業化”對美國經濟結構和貿易不平衡的影響。外國政府和機構持有的美國債務快速上升,使美國社會普遍擔憂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受制于人。龐大的國家債務也使美國政府難以拿出大規模的資金去更新基礎設施、投資教育和科技、從事戰爭和對外援助等,從而影響了美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是美國的工業基礎受到削弱,危及美國國防安全。在長期的“去工業化”過程中,美國制造業產業鏈的完整性受到影響,不僅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幾近消失,而且一些戰略性產品都不得不依靠進口,這甚至波及美國的國防工業。美國制造業聯盟的一份研究成果考察分析了支撐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16個產業的狀況,發現其中13個在2002—2007年間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只有兩個產業保持增長,一個產業保持相對穩定[23]245。這些產業生產的相關部件在國防工業上應用廣泛,還遠未達到淘汰的時候,但在美國都受到嚴重削弱。有些關鍵產業,如半導體、印刷電路板、機床等,美國的生產能力已大幅下降,更多地依賴海外供給。此外,戰略原材料的生產能力也大量地向海外轉移,美國在一些關鍵性的戰略原材料,如高性能的鋼材、陶瓷、隱身材料、光學材料等,已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供給。稀土問題即是其典型體現。目前,美國在鋱、镥、釔等重稀土的生產上是零,在稀土金屬上只有少量的生產能力。美國國防上所用的稀土只有5%可由國內提供,剩下的都需要進口。美國不生產稀土,并不僅僅是美國的稀土儲量問題,更是因為美國以低廉的價格從中國進口稀土,從而關閉了國內的稀土產業。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美國曾經在稀土的生產和加工上是世界的領導者。自此之后,美國的稀土生產便日漸萎縮。更為嚴重的不僅僅是美國國內稀土產量低,而是到今天,“美國幾乎完全喪失了在稀土的提煉、制作、金屬生產、合成和制造永磁上的加工能力”[24]。
(二) 社會上的貧富分化對立
一是從基尼系數的變化來看,二戰后,經過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美國的經濟繁榮,美國的基尼系數有緩慢的下降,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快速上升,到2011年已經從1967年的0.397上升到0.477,增幅達20%[25]。
二是從人群收入方面的變化來看,資本和產業鏈外移,海外財富的大量流入并沒有使美國全體民眾受益,巨額財富只是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67—2011年,美國最富有的5%家庭的收入占整個社會收入的比重從17.2%上升到22.3%;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比重從43.6%上升到51.1%,占整個社會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貧窮的20%家庭的收入占比則從4.0%下降到3.2%;最貧窮的40%家庭的收入占比從14.8%下降到11.6%,減少了3.2個百分點[26]。同時,美國國會預算局的數據顯示,1979—2007年,占美國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的稅后收入比重從1979年的7.7%飆升到17.1%,而同期最貧窮的20%人群的稅后收入比重卻從7.1%下降到5.1%,底層80%的人群稅后收入比重從57.5%下降到48.2%[27]。
三是從貧困率的變化來看,美國的貧困率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快速上漲,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新經濟”的經濟繁榮時期顯著下降,2000年降到11.3%的低位,此后又快速攀升,到2011年仍保持在15%的高位[28]。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 450萬人上升到2011年的4 625萬人,上漲了88.8%,顯著高于同期美國總人口43%的上漲幅度。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貧困人口的上漲速度更快,從2001年的3 290萬快速上漲到2011年的4 625萬人,上漲了40.5%,而同期美國總人口只上漲了9.6%[27]。
頂層少數人的日益富有與底層貧困人口的上升深刻反映了近40年來美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深的現實。而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又是催生社會運動的沃土,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茶黨”(Tea Party)運動、“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等,從長遠來看,勢必危及美國的社會安全。
(三) 政治上的兩極化
一是選民的兩極化,兩黨選民在政治價值觀上的對立程度越來越大。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從1987年到2012年,美國兩黨選民在政治價值觀方面的對立持續拉大,從10%上升到了18%,幾乎翻了一倍。在一些重要的內政問題上,如在社會安全網、機會均等、政府范圍等議題的看法上,兩黨選民的差異指數都達到33以上,比1987年有較大幅度的增加[29]。
二是國會議員的兩極化,持中間立場的溫和派議員的比重在下降,國會議員在議案投票表決方面越來越多地與本黨多數議員保持一致。根據反映議員價值觀的DW-NOMINATE指標體系,不管是眾議院還是參議院,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中持中間立場的溫和派議員都在減少,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相應地,兩黨議員都各自趨向本黨的意識形態,民主黨議員越來越趨向自由,共和黨議員則越來越趨于保守[30]。
兩黨選民和國會議員的政治兩極化使美國兩黨在國家經濟社會政策領域中的斗爭更加白熱化。這在2000年后的歷次大選中都得到了體現。共和黨議員和民主黨議員在法案投票上幾乎完全以黨派劃界,兩黨的協調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失靈,兩黨的政治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這導致政府難以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應對各種危機。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到最近的2013年,前后18次的美國政府關門危機即是表現。從長遠來看,這勢必危及美國的政治安全。
(四) 意識形態上的“美國夢”危機
一是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水平保持停滯狀態,中產階級群體在日益萎縮。與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稍低,兩者呈平行態勢,但自20世紀70年代初之后,兩者的差距開始拉大。1971年,兩者的差距是0.6萬美元;到2011年,兩者的差距是2萬美元。從1971年到2011年,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從5.7萬美元上漲到8.1萬美元,上漲幅度為41.2%,兩倍于同期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增幅[31]。而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群體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顯著下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結果,2011年屬于這一階層的成年人只占所有成年人的51%;而在1971年,以同樣的標準衡量,這個比重則有61%[32]。
二是中產階級面臨著更多的支出壓力,特別是在醫保、教育和住房方面。醫保方面,1980年,美國個人的醫保費用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例為9.5%;到2010年,已經上升到16.3%。教育方面,2010年,美國的大學平均學費為2.1萬美元,扣除通脹因素,比1990年上漲了72%,對收入在總人群中居于中間的40%和60%的家庭來說,一年的大學學費分別占他們年收入的54%和40%。在美國,大學教育越來越與出身階層和收入水平高度相關,美國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與家庭收入的相關系數已經接近0.5,僅低于意大利和英國[33]。住房方面,1980年,房貸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8%,到2010年,這個比重已經增加到116%[33]。
三是作為前兩者的一個綜合結果,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獲得和負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到2012年,已經有62%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表示因資金緊張,不得不在下一年度削減家庭開支,這比金融危機之初的2008年高出近10個百分點;美國中產階級中高達85%的人認為比10年前更難以保持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32]。
傳統上,制造業是普通美國人上升為中產階級的一條重要通道,尤其對那些外來移民、少數族裔或底層美國人來說,制造業對文化程度的要求相對不高,給這些人提供了進入制造業就業并步入中產階級的機會。但是,經濟上的長期“去工業化”,使美國產業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制造業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抑制,對尚未躋身中產階級的人群來說,要進入這個行列已經越來越困難了,“美國夢”遇到了挑戰。“美國夢”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來源,承載著賦予和維持美國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功能。從長遠來看,這勢必危及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安全。
四、 美國“再工業化”的國家安全含義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徹底暴露了美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奧巴馬高舉“變革和希望”的大旗,為他贏得了當年的大選。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的確與選舉政治是有聯系的,因為奧巴馬的上臺與制造業占優勢的州及勞工組織的巨大支持是分不開的。而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美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9%-10%之間,奧巴馬迫切需要在短期內解決美國高失業率的問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失業率居高不下也的確是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戰略的重要原因。
但這些都不能算是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的深層次原因。對上臺后的奧巴馬政府來說,它要著手于解決金融危機的眼前問題,但更要著眼于解決危及美國長治久安的長遠問題,以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奧巴馬政府明確指出,“當我們應對這些危機時,我們的國家戰略必須更加著眼于長遠。我們必須為美國的領導地位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并在21世紀更好地塑造對我們的人民至關重要的結局”[34]。固然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急需解決的種種問題,但歸根結底,長期“去工業化”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引發美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多領域的危機,對美國國家實力造成了系統性的損害,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了全局性、結構性的挑戰,威脅到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這才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這迫使奧巴馬政府不得不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理制造業問題。
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做了很多調整,比如放棄“反恐戰爭”的提法、改善與穆斯林世界的關系、突出多邊主義與合作等等,顯示了不同于前任的風格。2010年5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其任內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其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系統闡述。總的來說,報告延續了“冷戰”以來美國歷屆政府的安全戰略目標,即維持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應著眼于重振美國的領導地位,使我們能夠在21世紀更有效地推進我們的利益”[34]。但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途徑上,奧巴馬政府做出了重大調整,將重心放在了國內重建上,特別是經濟重建,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的重大轉折。與“冷戰”結束后美國歷屆政府依靠美國無可匹敵的國家實力,輔以聯盟或國際組織,打造有利于美國的世界秩序不同,奧巴馬政府雖然仍然堅持美國塑造世界秩序的目標,但更多地將重心放在了美國實力的恢復上,選擇了將“建設國內,塑造海外”作為基本國家安全戰略[35]。奧巴馬政府強調:“我們的國家安全始于國內。我們邊界內所發生的事項一直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在相互聯系的時代,這更為真切。首先和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重建美國力量的基礎。”[34]
“建設國內”的中心就是經濟重建,奧巴馬政府在報告中指出,“我們工作的中心是讓經濟保持活力,這是美國力量的源泉”[34];而經濟重建,則以“再工業化”為主要方向。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伊始,就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再工業化”的綜合性舉措,大力推進美國制造業的振興,力圖推動美國經濟從過去維系在金融信貸之上的高消費模式向出口推動和制造業推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奧巴馬政府一再強調,“美國的經濟建立在流沙之上”,“我們不會回復到被外包、惡債和虛假的金融收益所削弱的經濟上來”[36]。2012年奧巴馬獲得連任前后,更進一步強調了制造業的重要性,明確表示,要從美國的制造業開始,“建設持久的經濟藍圖”[36],“重新點燃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一個上升的、繁榮的中產階級”[37]。
2015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其任內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仍然強調“任何確保美國人民的安全并促進我們國家安全利益的成功戰略,都必須基于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必須處于領導地位”,并再次指出“美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基礎,也是美國在國外影響力的重要來源”[38]。同時,報告還對“再工業化”戰略實施6年來所取得的成效進行了肯定,“僅在過去6年里,我們制止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催生了經濟增長的新時代”,“我們已經從全球性衰退中復蘇,在美國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其他發達經濟體創造的合在一起的總數還多”,“自從大蕭條以來,我們經歷了歷史上時間最長的私營部門就業增長,創造了近1 100萬新的就業機會。失業率下降到6年來的最低水平”[38]。
以制造業為抓手來處理國家安全問題,是美國歷史上制造業與國家安全關系在今天的回響。從短期看,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美國市場需求萎縮、就業和出口減少,國際貿易和資本上形成雙逆差,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擴大工業出口,平衡貿易逆差,降低失業率,緩解經濟壓力,是著手于解決金融危機的眼前問題[39]43-44。但從長遠看,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本質上是著眼于解決美國實力的衰落問題,從而為美國在世界上的持久霸權地位打下堅實基礎。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與其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因此,“再工業化”遠不止是一項經濟戰略,同時還是一項安全戰略,是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具體體現[35]。奧巴馬政府推動“再工業化”的背后,還有深刻的國家安全含義。
可以預見,即使美國政權發生更迭,持不同政見的共和黨政府上臺,最終也會延續這個戰略方向。他們可能采用一個不同的名稱,可能會對戰略做出一定的調整,但歸根結底,“問題決定議程”,其實質和內在邏輯不會改變。事實上,盡管特朗普對“美國霸權邏輯”頗有微詞,認為充當“世界警察”的代價過于沉重,提出“美國優先”,也表現出很強的“反全球化”色彩,但特朗普上臺后并沒有改變奧巴馬的“再工業化”戰略取向,只是在策略上進行了一些調整。與奧巴馬相對溫和、注重多邊的“再工業化”政策相比,特朗普傾向于通過更為激進、更加孤立的手段來增加美國工人的就業,支持美國制造業的發展。當然,這并不是說,美國政府一定會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目標,是否去做與能否實現是兩回事。
五、 美國“再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轉向“再工業化”,主要是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但由于中美經濟的深度交融和中美關系的微妙復雜,中國近些年來的崛起態勢,構成了美國此次“再工業化”轉向最大的外部因素。
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制造業領域取得的“世界工廠”地位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很大的輻射效應,帶動了區域合作,使得亞太地區逐漸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產業分工與整合。新美國基金會稱之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現象,認為這種格局對美國具有多重的安全含義:一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依賴對其經濟安全構成了挑戰;二是中國持有大量美債會導致中國獲得損害美國財政安全的權力;三是中國居于全球供應鏈的中心,將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捆綁在中國身上,增加了中國的地緣經濟權力,中國可以運用其財富來加深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財政依賴[40]。
這種局面使得美國決策層擔心中國最終將主導整個亞太地區。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亞太秩序,意味著對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挑戰。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更凸顯了中國實力的迅速上升。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美國開始加速撤出中東,與此同時,加快了“重返亞洲”的戰略調整,針對亞太地區展開了一系列攻勢,在外交上、安全上、經濟上都推出了重要舉措。這意味著,在接觸與防范的兩手中,即通常所說的“兩面下注”,美國對華政策防范的一面在顯著加強。與其前任相比,奧巴馬政府已不滿足于利用國際規則來阻止中國的崛起,而傾向于采用“大陸均衡”的均勢戰略來制衡中國。制造業上的進步是中國實力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盡管旨在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但在“重返亞洲”的戰略背景下和“建設國內,塑造海外”的安全戰略思路下,對中國防范的一面也體現在了“再工業化”戰略上。“中國制造”成為美國“再工業化”所要防范和瞄準的對象[35]。
(一) 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蘊含著對華戰略沖突的性質
第一,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具有創新引領的特點,如2009年和2011年兩度發布《美國創新戰略》報告,提出了美國發展創新型經濟的完整框架,把發展先進制造業、生物技術、清潔能源等作為優先突破的領域,2013年計劃一次性投資十億美元在全國構建一個由15個制造業創新研究所組成的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并通過了打擊“專利流氓”的《創新法案》等等,其主導方向絕非簡單的傳統制造業復興,而是以科技創新引領的更高起點的工業化,目的是“要確保下一次制造業革命發生在美國”,搶占制造業新一輪變革的制高點,維護美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地位。如美國進步中心就明確指出,美國不可能在大多數的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生產領域重新獲得競爭優勢,而在先進制造業方面,美國則必須進行競爭*M.Ettlinger & K.Gordon,″The Importance and Promise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Why It Matters If We Make in America and Where We Stand Today,″ 2011-04-07,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1/04/pdf/manufacturing.pdf, 2015-12-18.。當前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這意味著,未來中美兩國制造業的重點發展領域具有很大的重疊性,兩國在新興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和博弈將日趨激烈[41]。
第二,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具有出口導向的特點,如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計劃”、簽署“國家出口倡議”和《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設立“出口促進內閣”、成立“總統出口委員會”,2012年推出“金鑰匙”計劃,擬推動4 000家美國中小企業進入中國,力圖將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帶到中國等等,其核心思路是“美國制造,全球銷售”[42],注重強化美國在推行市場開放方面的能力,積極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為“美國制造”開拓出口市場。從長遠來看,這意味著對“中國制造”的一定程度的替代,勢必損害中國獲得的“世界工廠”地位。而奧巴馬政府致力于美國本土制造業的振興,出臺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甚至不惜制造愛國輿論,敦促美國海外制造業企業“回巢”美國本土或臨近的墨西哥,也增加了中國市場出現外企撤離、外資出逃的風險。
第三,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具有服務平衡的特點,中美關系過去數十年維持穩定所依賴的“壓艙石”——所謂“中美國”(Chimerica)經濟互補關系將出現動蕩。長期以來,中美之間形成了這樣一個互補的貿易模式:美國支付美元,從中國大量進口廉價制成品;中國則將從美國賺取的美元以債券等形式存放在美國,支撐美國國內的超前消費。但美國長期“去工業化”的負面效應在2008年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集中爆發出來,迫使奧巴馬政府推動所謂的“全球再平衡”,以解決其高漲的債務和虛擬經濟問題。按照奧巴馬政府的設想,美國增加出口,中國增加進口,美國增加儲蓄,中國增加消費,雙方逐漸達致新的平衡。在這個設想中,“再工業化”戰略是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則被“要求”擔負起配合的義務,這意味著中國未來發展將更多地面臨來自美國“全球再平衡”的戰略壓力,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將增加不安定因素[35]。
第四,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具有著眼安全的特點,如前文所述,“再工業化”遠不止是一項經濟戰略,同時還是一項安全戰略,其深層動機是要解決美國實力的衰落問題,維持美國在世界上的持久霸權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大洋洲在內的西方所謂的亞洲經濟的崛起是最顯著的地緣政治現象,中國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盡管目前亞洲地區在世界上的進出口份額還不敵歐洲,但趕超之勢已成,這意味著數百年來以大西洋為中心的經濟格局將會翻轉。在這種情勢下,奧巴馬政府打著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權的名義,提出“重返亞洲”,參加TPP談判,開啟TTIP談判,推動“再工業化”,實施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打亂正在進行中的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企圖以此孤立和遏制中國的崛起,勢必醞釀著加深與中國地緣政治沖突的風險[35]。
(二) 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蘊含著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增強的意味
第一,設定“購買美國貨”條款,并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制造”進入美國,尤其是中國制造的先進技術產品。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復蘇與再投資法案》中設定了“購買美國貨”條款,要求該計劃所需要的鋼、鐵及相關制成品均須美國制造,從而變相地把中國等國家的相關產品擋在門外,使其難以進入美國政府投資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而且事實上,“購買美國貨”條款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原本的政府投資計劃范圍,如之前發生的作為私營公司的美國西部快線公司單方終止與中方合作高鐵項目的事件,美國西部快線公司就聲稱,終止合約的決定主要基于中鐵國際公司無法獲取美國政府的必要授權,無法滿足“高速列車必須在美國制造”的規定,即“購買美國貨”法案[43]。不僅如此,奧巴馬政府還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中國的電子、通訊等先進技術產品設置進口限制。如由奧巴馬批準生效的《2012年國防授權法》第516部分就規定,美國商務部、司法部、國家航空航天局、國家科學基金會等部門在使用《國防授權法》的資金去采購“任何由中國擁有、指導或資助的一個或多個實體生產、制造或組裝的信息技術系統”時,須與聯邦調查局或其他相關機構進行磋商,對網絡間諜和破壞進行評估[44]。
第二,在WTO更為頻繁地對“中國制造”提起訴訟,利用國際貿易規則打壓和限制“中國制造”,保護美國制造業的發展。世貿組織的數據顯示,在奧巴馬政府的首個任期內,美國共向WTO提起針對中國的申訴案件8起,比小布什政府兩屆任期內提起的申訴還多[45]。而據我國商務部的統計,從奧巴馬政府上臺到2011年底的不足三年的時間里,美國針對中國采取的雙反措施就達到了40起,平均每年13起,是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兩倍以上[46]。2012年11月奧巴馬獲得連任后,其勢頭有增無減。2013年前三季度,美國共發起337調查34起,其中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件就有15起,占比為44.1%,位居首位。聯想、海爾、華為、中興以及三一重工等具有較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大企業頻繁涉案,并成為337調查的強制應訴企業[47]。僅2015年上半年,美國發起涉及中國產品的337調查5起,涉及實用新型等專利糾紛的機電、輕工、醫藥等產品頻遭調查,中國高科技、高附加值出口產品遭遇設限呈增長態勢[48]。
第三,為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宣布正式參與TPP談判,著手打造美國主導的排他性的自貿區,并有針對性地設立所謂的高標準,將中國排斥在外。2009年11月,奧巴馬宣布正式參與TPP談判,并開始積極推動TPP成員國的擴大,試圖在亞太地區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以期圍堵中國,削弱中國取得的“世界工廠”地位,打破幾十年來亞太地區圍繞中國進行的地區整合,解決其所擔心的亞太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問題[35]。2016年2月4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12個國家在奧克蘭正式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協議,只是隨著特朗普的上臺,已無疾而終。
總而言之,2008年前后,美國開始“再工業化”,中國也提出了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出臺了《中國制造2025》,可謂不謀而合。盡管目前特朗普的許多政策仍不明朗,但特朗普進一步推動美國“再工業化”的努力方向在其競選言論中已經明確,如對所有進口貨物施加20%的進口關稅,特別是對中國和墨西哥分別征收45%和35%的關稅,扭轉貿易逆差;退出TPP,甚至退出WTO,重新審視NAFTA,“展開公平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以讓工作和工業重返美國”;向海外美國制造業企業征收額外稅,“讓美國制造回家”;降低美國企業海外資金回流稅率,吸引美國海外資金回流;警告美國公司,消除“工作外包”,讓就業崗位回歸美國本土;運用匯率武器,“上任后100天內,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削弱中國等國家的出口能力,提振美國出口;收緊移民政策,限制外來移民,保護美國本地工人就業;等等。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美在制造業上會發生越來越多的正面交鋒。雙方政策的成敗與否將深刻影響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和未來的世界格局。

[1]金碚、劉戒驕:《美國“再工業化”的動向》,《中國經貿導刊》2009年第22期,第89頁。[JinBei&LiuJiejiao,″TrendofU.S.Re-industrialization,″ChinaEconomic&TradeHerald,No.22(2009),pp.89.][2]徐禮伯、沈坤榮:《美國“再工業化”國內研究述評》,《現代經濟探討》2013年第7期,第7887頁。[XuLibo&ShenKunrong,″ReviewontheDomesticResearchofU.S.Re-industrialization,″ModernEconomicRe-search,No.7(2013),pp.7887.][3]黃陽華、卓麗洪:《美國“再工業化”戰略與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10期,第2326頁。[HuangYanghua&ZhuoLihong,″U.S.Re-industrializationStrategyandthe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ChineseCadresTribune,No.10(2013),pp.2326.][4]W.Lippmann,USForeignPolicy:ShieldoftheRepublic,Boston:Little,Brown&Co.,1943.[5]劉躍進:《論國家安全的基本含義及其產生和發展》,《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6265頁。[LiuYuejin,″DiscussionontheBasicMeaningofNationalSecurityandItsEmergenceandDevelop-ment,″JournalofNorthChinaElectricPowerUniversity(SocialSciences),No.4(2001),pp.6265.][6]G.D.Foster,InSearchofaPost-ColdWarSecurityStructure,Collingdale:DIANEPublishingCompany,1994.[7]儲昭根:《安全的再定義及其邊界》,《國際論壇》2015年第4期,第4651頁。[ChuZhaogen,″RedefiningSecurityandItsDisciplinaryBoundary,″InternationalForum,No.4(2015),pp.4651.][8]A.Wolfers,″'NationalSecurity'asanAmbiguousSymbol,″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67,No.4(1952),pp.481502.[9]P.Mangold,NationalSecur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0.[10]孫晉平:《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家安全理論》,《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第39頁。[SunJin-ping,″TheTheoryofNationalSecurityin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JournalofUniversityof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No.4(2000),pp.39.][11]E.R.May,″NationalSecurityinAmericanHistory,″inG.Allison&G.F.Treverton(eds.),RethinkingAmerica sSecurity:BeyondColdWartoNewWorldOrder,NewYork&London:W.W.NortonandCom-pany,1992,pp.9299.[12]梅孜編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匯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年。[MeiZi(ed.&trans.),TheCollec-tionof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Beijing:CurrentAffairsPress,1996.][13]C.Clifford,″AmericanRelationswiththeSovietUnion,″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coldwar/documents/sectioned.php?documentid=41&pagenumber=1&groupid=1,20160418.[14][美]邁克爾·H·亨特:《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褚律元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M.H.Hunt,IdeologyandU.S.ForeignPolicy,trans.byChuLüyuan,Beijing:WorldAffairsPress,1999.][15]G.Washington,″FirstAnnualMessagetoCongress(January8,1790),″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3448,20160315.[16]D.A.Irwin,″TheAftermathofHamilton s'ReportonManufactures',″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Vol.64,No.3(2004),pp.800821.[17]A.Hamilton,″ReporttoCongressontheSubjectofManufactures,″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pds/livingrev/politics/text2/hamilton.pdf,20160216.[18]F.D.Roosevelt,″Onthe'ArsenalofDemocracy',″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3319,20160420.[19]劉同舜編:《“冷戰”、“遏制”和大西洋聯盟———1945-1950年美國戰略決策資料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LiuTongxun(ed.),ColdWar,ContainmentandtheAtlanticAlliance:SelectedDocumentsConcerningU.S.StrategicDecisionsfrom1945to1950,Shanghai:FudanUniversityPress,1993.][20]楊仕文:《美國非工業化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YangShiwen,ResearchofU.S.De-industrialization,Nanchang:JiangxiPeople sPublishingHouse,2009.][21]U.S.BusinessandIndustryCouncil,″20002010aDe-industrializationDecadeforU.S.Manufacturing,″20100601,http://americaneconomicalert.org/view_art.asp?Prod_ID=3531,20160602.

[22]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Securities(c):AnnualCross-BorderPortfolioHoldings,″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Pages/fpis.aspx,20160602.[23]M.Webber,″ErosionoftheDefenseIndustrialSupportBase,″inR.McCormack(ed.),ManufacturingaBet-terFutureforAmerica,WashingtonD.C.:TheAllianceforAmericanManufacturing,2009,pp.235253.[24]V.B.Grasso,″RareEarthElementsinNationalDefense:Background,OversightIssues,andOptionsforCon-gress,″20131223,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1744.pdf,20151118.[25]U.S.CensusBureau,″TableH4.GiniRatiosforHouseholds,byRaceandHispanicOriginofHouseholder,″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income-households.html,20160314.[26]U.S.CensusBureau,″ShareofAggregateIncomeReceivedbyEachFifthandTop5PercentofFamilies(AllRaces),″http://pages.pomona.edu/~vis04747/h21/readings/income_tables/incshare.pdf,20160218.[27]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TrendsintheDistributionofHouseholdIncomeBetween1979and2007,″http://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cbofiles/attachments/1025HouseholdIncome.pdf,20151215.[28]U.S.CensusBureau,″Income,PovertyandHealthInsuranceintheUnitedStates:2011Tables&Figures,″http://www.census.gov/search-results.html?q=Income%2C+Poverty+and+Health+Insurance+in+the+United+States%3A+2011+-+Tables+%26+Figures&search.x=0&search.y=0&search=submit&page=1&stateGeo=none&searchtype=web&cssp=SERP,20160309.[29]PewResearchCenter,″TrendsinAmericanValues:19872012,″20120604,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6/04/partisan-polarization-surges-in-bush-obama-years/,20160217.[30]VoteviewWebsite,″ThePolarizationoftheCongressionalParties,″20160130,http://voteview.com/po-litical_polarization_2015.html,20160316.[31]U.S.CensusBureau,″TableF7.TypeofFamily(AllRaces)byMedianandMeanIncome,″http://s3.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24475/t32905censusmedianincomes.pdf,20160602.[32]PewResearchCenter,″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ewer,Pooer,Gloomier,″20120822,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20160219.[33]S.R.Schwenninger&S.Sherraden,″TheAmericanMiddleClassunderStress,″20110427,http://newamerica.net/publications/policy/the_american_middle_class_under_stress,20160312.[34]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00526,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20151022.[35]黃建安:《美國“再工業化”政策舉措、戰略特點以及對中國的影響》,《浙江學刊》2014年第6期,第208213頁。[HuangJian an,″PolicyMovesandStrategicCharacteristicofU.S.Re-industrializationandItsImpactonChina,″ZhejiangAcademicJournal,No.6(2014),pp.208213.][36]TheWhiteHouse,″AnAmericaBuilttoLast,″20120124,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blueprint_for_an_america_built_to_last.pdf,20151223.[37]TheWhiteHouse,″The2013StateoftheUnion,″201302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president-barack-obamas-state-union-address,20151220.[38]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50206,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20160312.[39]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知識干部培訓叢書編寫委員會編:《信息化與再工業化知識干部讀本》,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年。[WritingCommitteeofCadreTrainingSeriesofKnowledgeonDeepFusionofInfor-matio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ed.),CadreTextbookonDeepFusionofInformatio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Beijing:PublishingHouseofElectronicsIndustry,2012.][40]T.Palley,″TheEconomicandGeo-politicalImplicationsofChina-centricGlobalization,″20120208,ht-tps://www.newamerica.org/economic-growth/policy-papers/the-economic-and-geo-political-implications-of-china-centric-globalization/,20160415.

[41]王達、劉曉鑫:《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6期,第7178頁。[WangDa&LiuXiaoxin,″U.S.Re-industrializationStrategyandItsImpactonChineseEconomy,″North-eastAsiaForum,No.6(2013),pp.7178.][42]J.Bryson,″RemarkstoSteelManufacturersAssociationConference,″20120515,http://www.commerce.gov/news/secretary-speeches/2012/05/15/remarks-steel-manufacturers-association-conference,20151019.[43]樓天和:《美國因何撕毀高鐵協議?》,2016年6月14日,http://www.yicai.com/news/5027022.html,2016年6月18日。[LouTianhe,″WhyDidU.S.BreaktheHigh-speedRailAgreement?″20160614,http://www.yicai.com/news/5027022.html,20160618.][44]113thCongressofU.S.A.,″H.R.933:ConsolidatedandFurtherContinuingAppropriationsAct,2013,″20130322,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3/hr933/text,20160219.[45]WorldTradeOrganization,″TableofDisputesbyMember,″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by_country_e.htm,20160326.[46]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美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對華貿易救濟措施涉案產品一覽表(更新至2012年4月20日)》,2012年5月3日,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dd/201205/20120508104018.sht-ml,2015年11月16日。[MinistryofCommerceofthePeople sRepublicofChina,″TheInvolvedProductsListintheTradeRemediesCasesagainstChinaCarriedoutbytheUnitedStatesNow(updatedApril20,2012),″20120503,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dd/201205/20120508104018.shtml,20151116.][47]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美337調查中涉華大企業逐漸增多》,2013年11月18日,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ee/201311/20131100393629.shtml,2016年3月17日。[MinistryofCom-merceofthePeople sRepublicofChina,″China sBigCompaniesInvolvedinSection337InvestigationsAreGrowing,″20131118,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ee/201311/20131100393629.shtml,20160317.]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5年上半年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總體情況介紹》, 2015年7月21日,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dd/201507/20150701065572.shtml, 2016年4月13日。[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General Demonstrations of Trade Frictions China Suffer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5,″ 2015-07-21,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dd/201507/20150701065572.shtml, 2016-04-13.]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U.S.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Yu Gongde1Huang Jian’an2
(1.ResearchCenterofWorldPolit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20,China; 2.ZhejiangProvincial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ngzhou310007,China)
Re-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ame into power and it marks the major transition and critical turn of U.S. 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Chinese academia has shown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policy shif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U.S. re-industrializ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divergences about whether the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temporary expedient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or a strategic turn with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academia.This is mainly because (1)most existing studies analyzed U.S.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r are based on the plan and policie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ignored 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ncerns behind it; (2)most existing studies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brought by the long-term de-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only 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lack the overall grasp.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studies,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n the deep motivation and the decision logic of the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Firs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survey of the logic and connotation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long-term de-industrialization upon U.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four linked levels of economy,society,politics and ideology; Final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U.S.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This study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Safeguard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is the main goal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power is the force base to maintain American hegemon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2)It is the basic logic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that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s more like a cloak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just for pursuing its unreasonable national interests; (3)American power has been impaired systematically by the long-term de-industrialization as economic excessive virtualization,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ensions,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ideological crisis of the American dream.This situation has brought comprehensive and structural challenges to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s threatened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world.So the U.S. government had to consider and deal with manufacturing problems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vel.And these are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push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4)Far more than just an economic strategy,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is also a security strategy.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djustment. It contains the nature of strategic conflict and the meaning of strengthening trade protectionism to China; (5)R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only a temporary expedient to deal with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a strategic turn with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achieve the goal of U.S. re-industrialization because planning to do it and the ability to do it are two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s.
U.S.; re-industrialization; national security; impact on China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6.024
2016-06-02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7-03-02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BYY012)
1.余功德(http://orcid.org/0000-0001-6250-4923),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國際政治學博士,主要從事美國社會政治、中美關系研究; 2.黃建安(http://orcid.org/0000-0001-6646-4797),男,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浙江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社會學博士,主要從事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發展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