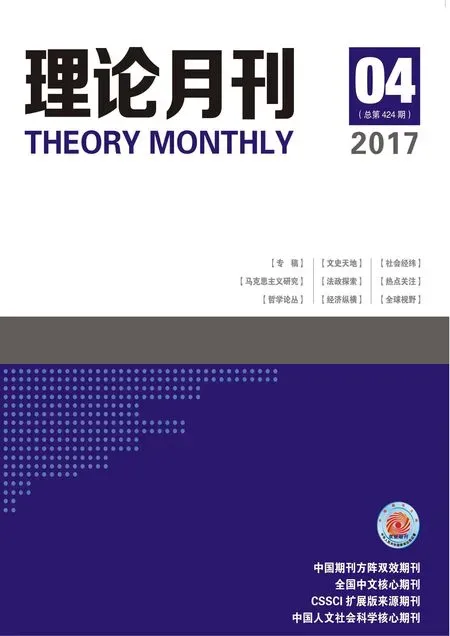晚清中國學校美術教育取向的歷史考察
——以社會為中心兼以學科為中心
□ 萬竹青,王昌景
(1.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系,上海 200241;2.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南京 210097)
晚清中國學校美術教育取向的歷史考察
——以社會為中心兼以學科為中心
□ 萬竹青1,王昌景2
(1.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系,上海 200241;2.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南京 210097)
晚清中國深刻的社會體制變革催化了學校美術教育的產生。在“西學西藝”理論影響下,晚清時期中國的教育思潮處于一種對西方的模仿期,美術教育領域同樣也呈現了對西方乃至日本不同程度的效仿,它們分別體現在洋務學堂、中小學堂、師范院校等不同層次的學校教育上,反映在課程標準、課程設置、教科書上。通過分析可以發現,晚清學校美術教育形成了以兩種方式為側重點的教育取向——“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以社會為中心取向和“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以學科為中心取向。
晚清;學校;美術教育取向;以社會為中心;以學科為中心
1 晚清中國特殊的社會狀況及教育背景
晚清,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體制變革。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中英條約》。不平等的條約使中國喪失了獨立自主權,社會性質由封建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在與西方列強發生多次戰爭后,簽訂了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成為晚清統治者應付外來侵略的唯一手段,也是其對于社會體制變革的力不從心的主要表現。這些條約的“簽訂”使得本來落后的晚清經濟、文化體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此后一段時間里,中華民族在國家主權、疆土、經濟與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都面臨著重重“矛盾與危機”。
縱觀晚清時期的文化教育,在“國家危亡”與“民族矛盾”雙重“危機”激化下,學制改革響應了朝野一致的“呼聲”。“光宣時代,當時無論新舊中人,莫不以教育為救國之要圖”[1]。無論是封建統治者還是革新的資產階級都認同教育是改造國家的重要出路。維新派人士康有為①康有為(1858-1927)字廣夏,又字長素,號更生,別署西樵山人。清光緒進士。愛國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學藝術家。官授工部總事,總理各國衙門章京。1898年領導“戊戍變法”。提出,中國之敗,敗在教育,輸在人才,在《請開學校折》中他寫道“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2]。內憂外患的清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也不得不尋求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策,探求富國強兵的方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應運而生,它們既是政治運動,也是教育改革運動。這些國人探索救國道路的艱難嘗試,雖沒有從根本上對舊中國的制度進行改革,但它們帶給人們的思想影響是遠大的——要想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不僅僅要繼承傳統的“儒家”學說,更要學習滿足工業社會發展的科學技術。因此,晚清這一特殊階段,中國清政府、資產階級紛紛提倡學習西方,以西方的技術來抵御西方的侵略,“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正如近代教育史學者舒新城所言,清末時期中國的教育思潮處于一種對西方的模仿期,這些教育思想可歸納為:方言思想、軍備思想、西學思想、西藝思想和西政思想。而這些思想中與美術教育相聯系最為密切的即是“西學思想”和“西藝思想”。根據文獻記載,當時西學所指的內容概要為:以經學、中國文學以外的各科統稱為西學①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學堂章程之學務綱要中,有一條題為《經學課程簡要并不妨礙西學》,意即如此。。其內容廣泛,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應用科學。此時相應的圖畫一科則在學堂里呈現兩種學科取向:即以“制圖技術”為主的應用科學取向和以“傳統繪畫”為主的社會科學取向。這兩種學科“取向”都同時受到了西方思潮的猛烈沖擊:一方面,外國的“堅船利炮”深深撞擊了中國保守的儒家思想學說,在民族危機下清政府為自救不得不學習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技術,將這種“理性的審視聲音”與“現實生命價值”的回眸共同表現在圖畫教育方面:即嚴謹的制圖技術;另一方面,西方帶來應用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中國傳統繪畫不同的社會科學,在圖畫上則表現為“西方繪畫體系”,這兩種敘事技法都是以西方世界視角、原生態地呈現給廣大受眾并被我們可以理性的追憶那種自身美術教育的思考和叩問。這一新興的繪畫系統與中國傳統繪畫體系在材質、技法、評價標準上都有所迥異,這些不同的特點亦給中國美術界以沖擊,使中國學者在全盤西化、中西合璧、保守主義間爭論與徘徊。
如果說西方教育理念通過塑造一系列的教育 “評判規則”并以晚清教育視角對當時社會弱勢群體的集中體現的話,那么,西學的思想又進一步分化為“西政”和“西藝思想”。“西藝原為西學的一部分……學與藝并無區別……甲午過后,因日人之屢欺我而對于其變法自強的情形有較深的了解,西藝思想又進一步,乃以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為西藝”“西藝思想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至二十九年(1903)之間即隱然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思潮。”“謂西藝均為中國古時所有,其內含有算學、天學、測量、化學、電學、光學、聲學、礦學、農學、學堂、賽會、重學、汽學、力學、畫圖學、輪車、輪舟、火器、自鳴鐘、儀器、機巧、鑄象、照相、鑄器等類。”[3]。從舒新城對西藝思想的詮釋可以看出,當時的西藝包含畫圖學,也就是各種機械、輪船的制圖學,其明顯傾向與應用學科取向。不論西學思想還是進一步細化的西藝思想都包括圖畫,可見這一時期圖畫是學習西方教育思想的最為重要的部分。
2 洋務學堂:“圖學”作為學習輪船機器等其他課程的“語言”
清政府向西方學習先進知識的重要標志,就是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洋務派主張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經驗,以改變中國的貧弱狀態,振興國力。他們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基本內容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省安慶建立軍械所②安慶軍械所是清朝1861年在安徽安慶建立的近代第一個以學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秀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式軍事工業企業,又稱“安慶內軍械所”,1864年遷至南京,后改名為“金陵機器制造局”。,用西洋的科學技術生產武器。后又于1865年,與李鴻章一道,借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局等軍事工業。
曾國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新造輪船折中談及建局意圖:“洋人制器,出于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扦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于翻譯甚為究心,先后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傳蘭雅、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制造之書,詳細翻出。現已譯成《汽機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采煤圖說》四種。……妥立課程,先從圖說人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4]
曾國藩認為:當時大規模地學習西方機器、輪船制造并沒有取得良好效果,究其緣由是因為語言不通不能很好地揣度意思,因而不能夠使西方技術在中國很快流通。因此在語言溝通有障礙的情況下,“圖學”作為一種學習語言,更為可視化、直觀化和普及化。清政府也更傾向于提倡用圖說和圖解的方式來介紹施工方案和工藝流程,以壯大本國軍事力量、促進工商業的方法,這樣也為當時的清政府提供了一個學習西方技術的良好“契機”。
這種良好的“機會”出現后,也在清政府的號召和感召下,清政府官員紛紛提出建議,例如增設實業學堂學習西方技術。“近年來風氣大開,一切工藝均效法泰西,誠自強之榮也……設工藝學堂以振商務……”[5]“洋務之所當講求焉,不同洋務則商務亦有所不明,何能與西商貿交往哉”[6]。這些學堂都重視西學對本國工商業的促進作用,并且將“圖學”作為其他“泰西課程”的解讀方式而視為重中之重。據文獻記載,洋務派所開設的實業學堂幾乎都開設圖學課程,有的配有專門的畫圖房或繪事院。1866年福州船政局設立,其教學科目除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地質學之外,還包括畫法,主要學習繪制船圖和機器圖。“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乃能依書繪圖,深明制造之法……擬請凡學成船主及能按圖監造者,準授水師官職”[7]。圖畫被提升到是否授予水師官職的評價標準。從1895年天津中西學堂的課程中亦可以看出當時學校對圖學課程的重視:第一學年,幾何學、三角勾股學、格物學、筆繪圖、各國史鑒、做英文論、翻譯英文。僅有7門功課里就包含一門“筆繪圖”,這一課程被視為與翻譯英文等課程同等重要。第二學年8門功課中包含一門“筆繪圖”。第三學年6門功課中包含一門“筆繪圖并機器繪圖”[8]。在提倡學習西方輪船、機器的主張下,圖學成為一種學習造船、機器等工藝流程的間接手段,其儼然成為實業學堂的必備課程和核心課程。

圖一船中電機圖:較電機器用銀線制《知新報》1897年第21期

圖二英機器報紡織機二十圖《萃報》1897年第8期
康有為曾在《萬木草堂藏畫目》中疾呼:“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畫,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可見,這一時期,圖學作為一門課程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強國力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內容”偏向于“實用”,注重技能傳授。洋務學堂提倡的圖畫教育更多傾向于以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為主要目標,其目的是運用工藝、設計制圖法來促進民族實業發展,提高器械、輪船繪圖技術來制造抵抗列強、保家衛國的武器。
3 中小學堂:載以“自在畫”和“用器畫”為內容的圖畫課程以“備職業之需”
3.1 《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從制度上肯定了“圖畫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
1902年,清政府派遣吳汝綸①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1865年中進士。歷任直錄深州、翼州知州。1889年退出政界。在保定任“蓮池書院”山長,并創辦了幾所外語學校,培養學生有1 200人之多。1902年應張百熙約聘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到日本進行考察,試圖以日本學制為參照進行國內基礎教育改革。管學大臣張百熙②張百熙(1874-1907),字野秋,湖南長沙人。早年擔任過光緒帝的侍讀。戊戌變法時,“濫舉康有為”,受革職留任處分。《辛丑條約》后,“抗疏陳打計”,積極提倡變法自強,主持學務,頗得人心。以日本考察報告為基礎草擬《學堂章程》,即所謂《欽定學堂章程》,亦稱“壬寅學制”。1904年,清政府在欽定學堂章程的基礎之上作了稍許改動,制定了《奏定學堂章程》,于1月13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頒布,也稱“癸卯學制”。
《奏定學堂章程》是近代第一個經法令頒布施行的學校教育章程。它從制度上規劃了整個國家的學校教育系統,對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方面進行了深化設計,對課程設置也作了詳細的規定。《奏定學堂章程》對中小學圖畫是這樣規定的:初等小學圖畫要義在練習手眼,以養成見物留心,記其實像之性情,教學內容為簡易之形體;高等小學圖畫要義在使知觀察實物形體及臨本,由教員指授畫之,練成可實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習于精細,助其愉悅,教學內容為簡易之形體、幾何畫;中學圖畫要義在于“習圖畫者,當就實物模型圖譜,教自在畫,俾得練習意匠,兼講之大要,以備他日繪地圖、機器圖,及講求各項實業之初基”,教學內容第一學年到第四學年,皆為“自在畫、用器畫”[9]。觀其教學內容,自在畫與用器畫為主要部分,李叔同曾對“自在畫、用器畫”兩個畫種進行了分類,自在畫分為兩種:西洋畫和日本畫;用器畫分為幾何畫、投影畫、陰影畫和透視畫[10]。這樣的解釋與西學西藝思想所談論的社會科學與應用科學不謀而合,這也恰恰證實了中國在向外國學習的過程中,不僅學習應用科學——即圖(用器畫),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社會科學——西洋畫和日本畫。
近代早期的學堂章程雖然深受日本和西方的影響,但它的頒布卻從制度上肯定了圖畫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圖畫課的對象不再局限于陶冶情操的官宦和士大夫子弟或者是作為“藝匠”的社會地位低下的庶民子弟,而是從全體社會出發,對小學、中學、實業學校、高等院校都作了規定,使全體社會人員都接受圖畫教育,為日后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打下了基礎;教學形式上從師徒傳授制轉型至班級授課制,教育形式的轉型是圖畫教育不再是少數人專屬的權利,而逐漸催生了教育全民化的萌芽,大大推進了整個社會的進步;教學內容上突破了傳統毛筆畫,加入了一些現代科學技術成分如幾何畫、用器畫等制圖課程。總之,在這一時期,我國中小學圖畫教育在國家制度保障下逐漸開展起來,在教學組織上實現了學校教育規模化,教學內容也越來越豐富。
3.2 教材集中于畫貼、范本和幾何畫、用器畫
清末時期中小學美術教材集中于毛筆畫、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和以備他日職業所用的幾何畫、用器畫。這些教科書最早的有1902年俞梁編、文明書局出版的《筆習書帖》三本,《新習畫帖》五本,《鉛筆新習畫帖》四本;張景良譯《幾何畫》一本;丁寶書編《高小鉛筆習畫帖》以及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謝洪賚編 《投影畫》一冊、徐詠清編《鉛筆習畫帖》八冊[11]。
據文獻記載,1906年4月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中關于美術的有:文明局印刷和發行的生徒用《毛筆習畫帖》三冊、生徒用《毛筆新習畫帖》四冊、教員用《毛筆新習畫帖》一冊、生徒用《初等鉛筆習畫帖》四冊、教員用《畫法教法規則》一冊、教員用《小學分類簡單畫》一冊,商務館出版、固化小學校發行的教員用《畫學教科書》一冊和同文印書社出版、武昌圖書館的《圖畫臨本》一冊。1906年學部第一次審定高等小學暫用書有:商務館印刷和發行的學生用《高等小學毛筆習畫帖》八冊、《高等小學堂用鉛筆習畫帖》八冊;湖北官書局發行的學生用《圖畫臨本》八冊、教員用《圖畫臨本》一冊;文明局印刷和發行的學生用《高等小學堂鉛筆習畫帖》三冊、教員用《高等小學幾何畫教科書》一冊[12]。除此之外,普遍流行于學校圖畫教育的還有: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初等、高等鉛筆畫貼》;1907年商務出版社的《鉛筆畫范本》《水彩畫范本》《鋼筆畫范本》等。
圖畫的實用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小學美術課堂。從當時的教科書可看出這種“以備他日繪地圖、機器圖”的技術傾向,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張景良編寫的《小學幾何畫教科書》,作者在序言中寫道:“我國言富強垂四十年而貧弱卒如此者,何哉,夫東西國之所以日臻富強者不第政治修明而工業發達之故,其間正局多數焉,然不明算數不精圖學,亦莫得而言工業……”。作者將東西國之所以富強歸結于工業發達,而工業發達與精通圖學緊密聯系,換言之,我國應加強圖學教育來發展工業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又如1906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課書用器畫》(孫鉞編輯,杜亞泉校訂)、1907年5月上海啟智學社郭德裕編輯 《最新用器畫教課書》、1908年2月北京旅京學堂出版的有日人白濱征編著的 《用器畫教本》、1908年11月北京編者刊出版的(日)竹下富次郎著(閻永輝編譯,閻永仁等校閱,閻清真總校)《新式中學用器畫》等用器畫教材中都對這種實用技術的目的有所說明。
以上教科書反映了清末階段中小學美術教育的整體面貌和教育取向。根據汪亞塵的回憶,“各地任圖畫教員的人,他們所持的教授法,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國粹畫,一種是西洋畫”[13]。而從1906年4月學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也可以看出這兩種類型圖畫的教育取向:初等小學的毛筆畫帖教科書占的比重為38%,其余為西方畫法和用器畫;高等小學的毛筆畫帖教科書比重17%,幾何畫的比例有所上升。總體看來,清末中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在吸取西方技法的同時也注重傳承本民族毛筆畫的優秀傳統文化;隨著年級的遞增,實用技能的傾向有所加重,正如李華興在《民國教育史》中所述“普通教育中的課程設置,除初小學生年級尚幼…高小就須考慮學生皆有謀生之計慮”,“自小學校高年級起應漸漸注重用器畫,使學生一方面可以得到精密,正確之思想及習慣;一方面能認識及制作簡單之機械圖及工程圖,以助工業之發展也”[14]。
4 師范院校:“泊來”之日本課程及師資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興學堂,一時患在無適當的各級師資,故首先注重辦師范教育,這就需要造就大量師資以應急需”[15]。中小學堂圖畫課程的開設,圖畫教材的編纂、出版、發行,使得早期學校美術教育趨于正規化。而中小學美術師資的培養則更多有賴于師范學堂,因此,師范學堂美術教育的興起成為必然。
20世紀初到民國前這一時期建立的師范學堂有兩江師范學堂 (1902)、天津的北洋優級師范學堂(1902)、通州師范學校①1902年,實業家、教育家張謇(1853—1926)創辦了通州師范學校,開中國私立師范學校之先河。該校設4年本科、2年簡易科和1年講習課,課程主要有國文、修身、教育、倫理、算術、理化、史地、博物、圖畫、手工、體操等。(1902)、浙江兩級師范學堂(1907)、廣東優級師范學堂(1906)和天津北洋女師學堂(1906)。這些學堂都相繼開辦圖畫手工專科,實行新式美術教育,以培養美術師資為目標。
4.1 師范學堂的模范:兩江師范學堂及其圖畫課程
近代最早建立美術師范專科的師范學堂首推兩江師范學堂。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兩江師范學堂創立于南京北極閣下,校長李瑞清②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號梅庵,梅癡,阿梅,晚號清道人等。1893年(光緒十九年),中舉人;1895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任兩江優級師范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后,隱居上海。是當時著名的書畫家、教育家,曾受到日本和西方美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兩江師范學堂創辦了我國高等院校第一個美術師范專科,所建立的新藝術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的藝術師資人才,對于開辟我國美術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拓荒作用。兩江師范學堂共計辦10年。此10年中,全辦優級,初僅設史地、數理化、博物等科,后添辦圖畫、手工為主科外,并以音樂為副主科,規定三年半畢業。共辦過甲乙兩個班,畢業生共有六七十人。教師除蕭俊賢等外,還有好幾個日本人。我國最早的一輩藝術教育師資,如呂鳳子、姜丹書、沈溪橋、吳溉亭等都是該校出身[16]。
兩江師范學堂美術師范專科以 “圖畫手工”為主科,“音樂”為副科。其中的“圖畫課”為:素描(鉛筆、木炭)、水彩畫、油畫、用器畫(平面幾何畫、立體幾何畫……正投影畫、均角投影畫、傾斜投影畫、透視畫、圖法幾何等),圖案畫、中國畫(山水、花卉)。西畫教師:鹽見競(日人)。用器畫教師:亙理寬之助(日人)、鹽見競。中國畫教師:蕭俊賢(字厔泉,湖南衡陽人)[17]。課程設置對應中小學圖畫課程,以自在畫和用器畫為主,而自在畫以西畫、中國畫為載體,用器畫以幾何畫、透視畫、圖案畫為載體,體現了中小學與師范教育課程的連貫性。
當時的師范學堂美術教材,是與中學大部分相同的,即如前文所述的西畫教育傾向的習畫帖和實用美術傾向的用器畫,以及日本人井村雄之助編的畫貼《洋畫講義錄》。這些書也是我國師范美術教育最早的教科書[18]。另有不同于中學圖畫課程的、適合于當時情境且較便捷的圖畫教習方法即黑板范畫。“清光緒末年各中小學校都設有圖畫、手工、唱歌課。記得我在高等小學里學的圖畫是臨摹,教師在黑板上用粉筆繪范本……這就是當時的圖畫教學”[19]。190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師范學堂用《黑板畫教科書》即證實了當時的教學方法——黑板范畫。

兩江師范學堂作為師范教育的成功典范,有利地推動了全國各地師范學校的發展,而培養的優秀師資又惠及了各地中小學校。正如姜丹書所說:“此輩專門藝術師資造成后,再分頭服務于各省,主教圖畫手工專科,如此輾轉造就師資,藝術教育始得逐漸推廣,而普及于一般中小學校。”
4.2 師范學堂多從日本引進師資
在師資方面,清政府更傾向于從日本引進師資以加強學校教育的力量。1902年,清政府派遣吳汝綸訪問日本,向日方正式提出延請教師事宜,日本接到請求之后,開始在國內師范學校的畢業生、師范教員中選拔,經過短期培訓之后,派往中國[20]。汪向榮先生根據日本教習中島半次郎在1909年11月間的調查基礎上羅列了一份表格,其中摘錄出來一些有關的美術教員的名單,從這些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清末時期日本學者散布于各個師范學堂中。
如兩江師范學堂(南京)的圖畫教師:山田榮吉、伊藤村雄、亙理寬之助;山西優級師范學堂(山西太原)的圖畫教師: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丸野野;南京高等學堂的圖畫教師: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棍原熊雄;江蘇兩級師范學堂(蘇州)的圖畫教師:村井里之輔;女子師范學堂(南通)的圖畫教師:森田政子;北洋師范學堂(北京)的圖畫教師: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安成一雄(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教員)等。
日本蔭山雅博的 《清末教育近代化過程與日本人教習》一書亦記載了有關日本美術教習在中國師范學堂的情況。1909年在中國就有8名日本教師任教于圖畫科目,2人擔任工藝科目的美術教學。之后的1907到1910年期間,先后有5名日本美術教師在兩江師范學堂任教,在以日本美術教師為圖畫、手工教學力量的支持下,兩江師范學堂圖畫手工科開辦不到5年時間就培養了兩屆共69名畢業生,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批美術教育師資隊伍,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開拓創造了條件”[21]。
日本師資對中國近代早期的師范學堂貢獻了應有的力量,他們所培養的中國近代最早一批美術師資促進了全國各地中小學堂的圖畫教育,使美術教育逐漸推廣。師范學校的建立和擴展促進了教育、經濟乃至社會的發展,正如賀拉斯·曼所說的那樣:“師范學校之重要,宛如彈簧一樣,在師范教育中聚縮著一股活力,它一旦舒張開來,就會推動各項事業。”
5 結論
20世紀美國美術教育家埃利奧特·W·艾斯納(Eisner,E.W.)①埃利奧特·W·艾斯納(E.W.Eisner)(1933-2014),斯坦福大學杰克·李教育學教授、藝術教授。曾在芝加哥大學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后在伊利諾伊理工學院設計研究院學習設計及藝術教育。196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艾斯納的美術教育理論被認為是一種本質論,又被稱為“以學科為基礎的美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Education簡稱DBAE)。本質論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成為主流。在他的研究中提到,歷史中美術教育的各種側重可以用一個三角形來表示,其中一個頂點代表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第二個代表以兒童為中心的觀點,第三個代表以學科為中心的觀點[22]。縱觀中外美術教育歷史,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呈現不同的美術教育取向,晚清美術教育形成了兩種方式為側重點的教育取向——“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以社會為中心取向和“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以學科為中心取向。
5.1 民族危機下,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以社會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取向
中國教育的特點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教育政治化。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為維護封建統治,倡導所有的學說都為“政治服務”,教育是科舉的附庸,學校亦是官員培訓所。中國士子所欲的思想、論述全是儒家經典:“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教學內容僅以四書五經、八股詞章為法定范圍,教育目標以人倫道德和培養官吏為唯一宗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外國變相侵略。故步自封的中國在與外國政治周旋的過程中認識到外國科學技術的先進之處,終于從全盤排斥到慢慢接受,進而主動學習。民間吶喊,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志士最有影響;政府方面,則以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鼓吹“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勸學篇》舉足輕重。全國各地洋務學堂的開設即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表現在美術教育方面,圖畫則作為一種應用技術科學被提到國家教育制度層面。圖畫、制圖技術被廣泛應用到工業機械設計、輪船制造、民族實業等社會各層面,其作為美術學科的一個分支對近代中國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將教育看成一種通過公立學校組織起來的社會機制,將文化傳統傳給年輕一代。這種觀點將學校教育計劃看成滿足社會需要的載體,如果社會需要更多科學家或者工程師,教學計劃就應該強調培養這些技能”[23]。從洋務學堂課程中可以看出,圖畫正是以機器制圖、輪船畫圖學等課程呈現出來,以提高軍事、工業技術為手段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中小學堂圖畫課程亦是在原有以陶冶情操為宗旨的基礎上增設實用主義美術教育目的,大力倡導增加振興國民經濟的幾何畫、用器畫課程,其課程開設的目的是以增強國力、繁榮民族實業為目的,因而可以看成是以社會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取向。圖畫的目標在于為社會培養更多的機械工程師、民族實業家。
5.2 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形成了以學科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取向
所謂西學東漸,泛指西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各種社會政治學說自西徂東、敷布中土的過程[24]。美術作為一種人文學科,亦深受西方的“影響”。它一方面表現為西方繪畫向中國的輻射與滲透;另一方面表現為中國吸納和消化西方繪畫,將西方繪畫融入中國繪畫,成為特定的中國本土繪畫。中國美術學科從保守的毛筆國畫技法逐漸接納和吸收西方的繪畫技法,使之更開放、更具有世界性。
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中國美術教育逐漸形成了以學科為中心的教育取向。“以學科為中心的教育計劃的目標、內容和教學方法重視學科的完整性,對人類的經驗和知識的運用,及其內在價值。在這種美術教育目標的觀點指導下,教師要重視美術本身的研究”[25]。晚清,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西方繪畫體系迅速涌入中國,一些學者對西方畫法進行了積極地探討。如1905年發表在醒獅雜志的 《水彩畫法》解釋了西方水彩畫——“西洋畫凡十數種。唯與我國舊畫法稍近者唯水彩畫。”,而1907年商務出版社便出版了針對中學的《水彩畫》范本;《圖畫修得法》[26]中對圖畫課程的內容作了總結:“圖畫之種類至繁綦賾。匪一言所可殫。然以性質上言之判。圖與畫為兩種。若建筑圖制作圖裝飾圖模樣等。又不關于美術工藝上者。有地圖海圖見取圖測量圖解剖圖等皆為之圖。多假器械而補助之成之。”又如1907年發表美術雜志上的 《西洋畫科》、1906年環球中國學生報上的 《美術通詮》、1908年實業報上的《西方顏料制作法》等多篇文章對西方美術教育體系進行了詳盡的詮釋和說明。這些史料證明,在“西學東漸”的驅使下,晚清中國原有的以毛筆畫為主美術教育體系不再孤立,而是兼容并蓄,打開懷抱積極地接納西方美術教育體系。而中小學、師范院校西畫課程的增加,使教師不得不對水彩畫、鋼筆畫、鉛筆畫等來源于西方美術教育體系的加以審思和研究,無疑,這段時間的美術教育體系較之前更加完整,美術學科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以學科為中心的美術教育更注重延續和發展美術知識與技能,以滿足人類社會物質、精神和文化的需求”。西方美術知識與技能,在中國晚清這一特殊時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和發展。
5.3 待發展的“以兒童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取向觀
艾斯納認為“以兒童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其目的、內容和方法的起點是:美術或者其它科目教育計劃的內容必須首先用于解開兒童潛力之鎖,教育內容是自我意識的工具,教師的首要職責是充分了解學生以幫助他們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才能、激發他們的創造性。”通過對奏定學堂章程和當時的教科書的解讀可以看出,在清末這一階段以兒童為中心的創造性美術教育取向在中小學階段尚未提及,而是更傾向于如上文所述的以社會為中心和以學科為中心的美術教育取向。我國美術教育家尹少淳認為,中小學美術教育的目的在于通過美術教育促進學生思想與道德的發展、情感與審美的發展、智力發展、人格與心理發展和個性與創造力的發展[27]。美國美術教育學家羅恩菲德(Viktor Lowenfeld)認為,中等學校和小學課程中的藝術教育在發展個人心靈、感情和關感的成長,注重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未來生活作好準備。在藝術教育里,藝術只是一種達到目標的方法,而不是一個目標;藝術教育的目標是使人在創造的過程中,變得更富創造力,而不管這種創造力施用于何處。假如孩子長大了,而由他的美感經驗獲得較高的創造力,并將之應用于生活和職業,那么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已達成[28]。顯然,清末時期的中小學美術教育聚焦于實業美術技巧的培訓,如《奏定學堂章程》所規定的幾何畫、用器畫課程,其目標為將來的職業做準備,而不是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其目的過于急功近利和片面,只注重當前社會的需求,而沒有從長遠角度看人與社會的整體互動關系。臺灣美術教育家黃冬富也認為“以今日觀點視之,仍然未曾考量兒童造形心理發展能力之配合”[29]。這一局限,在民國建立以后蔡元培的領導下得到彌補,美術教育漸漸踏上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道路上,美術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完善個人全面發展,以達到改善整個社會的目的。但艾斯納也認為,“美術教育對教育事業有獨特的貢獻,雖然在不同時間美術可能有需要被用來實現別的教育目的,這些其它目的應該被看作短期目標,這些短期目標對于實現只有美術可以達到的目的是有必要的。 ”[30]
[1]梁任公蒞教育部演詞[J].東方雜志,1917(14):3.
[2]陳學詢.中國近代教育文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10.
[3]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62.
[4]曾國藩著,李瀚章編,李鴻章校刊.曾國藩奏折[M].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1:394.
[5]政事:湖北擬設工藝學堂[N].集成報,1898(26):19.
[6]論川東設立洋務學塾[N].萬國公報,1892(10):47.
[7]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香閣,1902:62-68.
[8]皇朝經世文新編第六冊[M].上海:上海譯書局,1898:18-25.
[9]章咸,張援.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匯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54.
[10]弘一大師全集編委會.弘一大師全集:第7卷·圖畫修得法[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45.
[11][12]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170,40.
[13]莊俞,賀圣鼐.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M].商務印書館,1931:234.
[14][26]李華興.民國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84,23.
[15]姜丹書.我國五十年來藝術教育史料之一頁[J].美術研究,1959(1):55.
[16][19]吳夢非.五四運動前后的美術教育回憶片段[J].美術研究,1952(4):11,12.
[17]朱伯雄,陳瑞林.中國西畫五十年[M].北京:人民美術出社,1989:80.
[18]潘耀昌.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史[M].浙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20.
[20]張少君.中國近現代學校美術教育形成與發展時期師資狀況分析[J].藝術百家,2007(4):172.
[21]胡光華.20世紀上半葉來華外籍美術教授(習)與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J].中國美術教育,2003(3): 48.
[22][23][25][30]艾斯納(Eisner,E.W.).兒童的知覺與視覺的發展[M].孫宏,等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4:51,56,33,63.
[24]陳媛,周治軍.論近代中國大學教授群體的演變動力[J].江蘇高教,2008(4):34.
[26]息霜.圖畫修得法[J].醒獅,1905(3):87.
[27]尹少淳.美術教育學新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9.
[28]羅恩菲德.創造與心智的成長[M].王德育,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3:35.
[29]黃冬富.中國美術教育史[M].臺北:師大書苑發行,2003:252.
責任編輯 劉宏蘭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4.008
G633.95=52
A
1004-0544(2017)04-0053-07
萬竹青(1983-),女,江蘇連云港人,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生;王昌景(1966-),男,江蘇徐州人,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