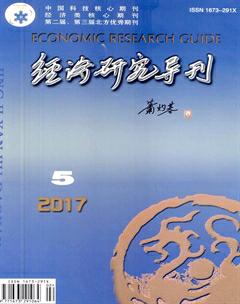隴海鐵路與近代關(guān)中傳統(tǒng)商業(yè)城鎮(zhèn)的衰落
郭海成
摘要:近代關(guān)中經(jīng)濟社會變動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即是城鎮(zhèn)格局的巨大調(diào)整,而這與1930年隴海鐵路的通達直接相關(guān)。大荔、三原與涇陽位處渭河以北,本為關(guān)中傳統(tǒng)商業(yè)中心城鎮(zhèn),但由于隴海鐵路線位于渭河以南,途經(jīng)華陰、渭南、西安,遂極大改變了區(qū)域交通體系。大荔、三原與涇陽由于遠離鐵路,缺乏在商業(yè)流通上極為重要的交通區(qū)位優(yōu)勢而日趨衰落,以至喪失了傳統(tǒng)區(qū)內(nèi)經(jīng)濟中心城鎮(zhèn)的地位。
關(guān)鍵詞:隴海鐵路;關(guān)中;城鎮(zhèn);衰落
鐵路交通的建立與區(qū)域城鎮(zhèn)格局調(diào)整是近代中國經(jīng)濟社會變動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關(guān)中亦不例外。隴海鐵路通達關(guān)中后,在鐵路沿線城鎮(zhèn)快速發(fā)展的同時,距離鐵路線相對較遠的傳統(tǒng)商業(yè)城鎮(zhèn),因在新的交通布局中處于不利地位,發(fā)展受到一定影響。以大荔、三原、涇陽為代表的傳統(tǒng)關(guān)中區(qū)內(nèi)經(jīng)濟中心城市,在關(guān)中城鎮(zhèn)格局中的地位趨于下降。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城市在區(qū)內(nèi)城鎮(zhèn)格局中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其步向衰落,而是表現(xiàn)為發(fā)展態(tài)勢較之鐵路沿線城鎮(zhèn)相對遲緩。
一、大荔的衰落
在隴海鐵路通達渭南之前,關(guān)中東部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是大荔,其素有“東輔重鎮(zhèn)”之譽。大荔位于關(guān)中東部黃、洛、渭三河匯流地區(qū),古稱“三秦通衢”、“三輔重鎮(zhèn)”,是古代出入秦晉的重要關(guān)隘和交通要道,成為兵家爭衡的戰(zhàn)略重地。大荔縣城距西安百余公里,周圍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物產(chǎn)豐富。商周時期,大荔為古芮國及同國所在地。秦時改為臨晉縣。三國時屬魏國,為馮翊郡治,開始成為關(guān)中東部的政治中心。大荔自東漢末設郡始,歷代沿設郡、州、府、署。漢、唐建都長安,大荔成為輔衛(wèi)京都的東府重鎮(zhèn)。大荔之名始于晉,其后地名變更較頻。清時為同州府治,統(tǒng)轄周圍10縣。清道光年間整修城池,周長9里余,高11米,上設炮臺48座。民國建立后,取消同州府。1930年設第八區(qū)行政專員公署于大荔,所轄10縣與清代相同。千百年來大荔或為郡治,或為州城,或州郡縣同治一城,素為關(guān)中東部政治經(jīng)濟中心。由于經(jīng)濟活躍,大荔人口中,非農(nóng)人口達半數(shù)之多。如光緒時大荔“業(yè)農(nóng)者十之五、業(yè)商者十之二、業(yè)讀者十之一、業(yè)工者十之一、業(yè)雜術(shù)技藝及無業(yè)之民十之一”。
大荔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對便利的交通區(qū)位。西周時期就有從鎬京通往山西的古大道,穿越大荔、朝邑兩縣。民國時期,先后有大(荔)韓(城)、大(荔)華(縣)等5條公路通過縣城。此外,黃河、渭河、洛河流經(jīng)大荔,形成航運的有利條件。三河在大荔境內(nèi)流程為253.15公里,其中黃河47.65公里、渭河84公里、洛河121.5公里,對大荔土特產(chǎn)的輸出、京廣雜貨的輸入,溝通秦、晉、豫三省物資交流方面,發(fā)揮過重要作用。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輸粟濟晉,即由鳳翔經(jīng)渭河東下,過大荔,入汾河,以達晉都(今山西襄汾)。隋時,開廣通渠,置永豐倉(即原朝邑縣南倉頭、倉西一帶),儲粟轉(zhuǎn)運,以濟關(guān)輔。清時,山西的煤、鐵、鹽通過汾水進入黃河運至潼關(guān),再入渭河趨洛河,于朝邑北陽洪、大荔太山頭上岸分銷。關(guān)中東部地區(qū)民眾日用所需之潞鹽、鑄鐵鍋、焦炭等,皆賴此航線運輸。民國時期,黃、洛、渭三河航運仍發(fā)揮重要作用,大荔設有航運管理處統(tǒng)理其事。1929年,大荔、朝邑發(fā)生饑荒,朝邑賑濟會赴豫西購糧,從靈寶裝船,自黃河逆流而上,經(jīng)渭河、洛河至北陽洪卸船,轉(zhuǎn)運賑糧千余石(每石280斤)。另據(jù)1930年陜西省渭、黃、洛三河航運總表記載,該年棉花、水煙、藥材、牛皮、牛毛、茶、鹽、煤、炭、煤油、布、鐵、柿餅、食糧、雜貨、京貨、面粉、麥、麻等19種物品的水運統(tǒng)計,渭河運量為5 260噸、黃河運量為34 784噸、洛河運量為3 910噸。1925年,大荔商會集資修建大王廟碼頭(由太山渡移設),碼頭上設有“同裕生轉(zhuǎn)運貨棧”、“同裕炭廠”、“涇洛河工程局材料股”,一度成為大荔輸出入物資的中轉(zhuǎn)樞紐。北陽洪亦是貨物周轉(zhuǎn)的重要碼頭。
大荔舊為同州府治,皮毛業(yè)極盛。唐開元以前,“同州皮貨”即廣負盛名,成為地方進奉朝廷的貢品。然大荔雖“以出產(chǎn)羊皮著稱于全國,其實本縣并不產(chǎn)皮,乃生皮自口外來此制熟,轉(zhuǎn)銷各省者”。之所以西北皮貨會運至大荔加工,與該地水質(zhì)適宜熟皮有關(guān)。據(jù)《大荔縣舊志存稿》載,生羊皮“唯同州硝水泡熟者,則較他處所制者逾格輕、軟、柔、鮮。”清道光時(1821-1850年),陜西巡撫歲以珠毛羔皮800張進貢京師。運集大荔的皮張,大部來自甘肅、寧夏、青海、四川等地,其中“老羊皮產(chǎn)于本省西安、延安、邡州;羔子皮并狐皮產(chǎn)于甘肅河州、西寧;平毛皮產(chǎn)于西番,由西寧進口;兔皮產(chǎn)于四川”H。大荔皮毛業(yè)最盛時,全縣有皮貨作坊150多家,遍及全城和周圍附近村莊;皮貨成品分長袍、馬褂、旗袍、女襖等,行銷北平、天津、上海等國內(nèi)各大城市及土耳其、英國等海外地區(qū)。皮貨銷售暢旺時,每年營業(yè)額達30萬兩左右。但民國以后,受戰(zhàn)事及天災影響,大荔皮毛業(yè)的發(fā)展歷受波折。“自民國十六年之役,遭圍城九月,城破之日,洗劫七晝夜,殺斃尤多;繼以天災與戰(zhàn)爭,頻年不已。小麥最高價,每擔增至四十元。經(jīng)此一再涂炭,元氣大傷,商業(yè)一蹶不振;皮莊由四百余家,減至二十家,錢莊四十余家,減至十家。”由于皮毛業(yè)為大荔商業(yè)支柱,因此,皮毛業(yè)的衰落帶累大荔商業(yè)的整體蕭條。“民十四以前,本縣商業(yè)甚形發(fā)達,商店達四五百家。”此后,一則受皮毛業(yè)衰落的帶累,一則“隴海鐵路經(jīng)過潼關(guān),北路商人多直往潼關(guān)購貨,不再以本縣為轉(zhuǎn)運之地”,大荔商貿(mào)趨于清淡,商店數(shù)量減少。1936年時“全縣計有商店三百六七十家”,商會“有會員五百七十余人,……下屬錢業(yè)、山貨京貨,皮業(yè)粟業(yè)、藥材業(yè)印刷書業(yè)等七同業(yè)公會”,“工會有會員一百六十人。”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大荔因地處河防前沿,大量軍隊屯駐于此,加之戰(zhàn)區(qū)西移、難民西遷來此,促使大荔呈現(xiàn)“戰(zhàn)時景氣”。1931年,大荔商號總數(shù)為199家,到1945年,激增為578家。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荔雖因“戰(zhàn)時景氣”獲得一定發(fā)展,但由于隴海鐵路通車后,關(guān)中東部商貨已大多運至位于鐵路線上的渭南、華陰、華縣進行集散,且渭南因交通區(qū)位優(yōu)勢的加強,工商業(yè)繁榮發(fā)展,成為關(guān)中東部經(jīng)濟中心,因此,大荔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二、三原與涇陽的衰落
隴海鐵路通車關(guān)中以前,三原、涇陽由于位處傳統(tǒng)渭北大道之上,且居于關(guān)中中部核心區(qū),因此,長期以來是西北與東南物資轉(zhuǎn)輸?shù)募⒅行摹?/p>
三原“位于涇渭之北,距長安九十里,為藥材商、煙草商、布商、茶商聚集之所。藥材、煙草則由甘肅生產(chǎn),在三原制造之以銷售于漢口、上海、香港各口岸;布匹則由湖北運來之木機布,以銷售于甘肅;茶則由湖南運來,以銷售于甘肅。三原實為各商經(jīng)過之場所,在商人的普通術(shù)語,謂之日‘過載碼頭。”㈣因此,三原長期為“陜西渭北之商業(yè)中心”。縣城城區(qū)分為南北二城,人口約5萬,“南城當城中心處,最為繁華,大廈櫛比,市廛甚盛,略有長安景象。”民國初年,渭北一帶植棉極盛,三原為最大之棉花市場,每年采買批發(fā)棉花達200萬斤。及至20世紀30年代初,三原仍為藥材及布匹之集散市場,陜北、甘肅之藥材集中于此,然后東運,湖北、河北之布匹由此轉(zhuǎn)銷甘肅。受藥材及布匹貿(mào)易繁榮的帶動,與之相聯(lián)系的銀錢業(yè)、鐵木業(yè)、油漆業(yè)、飲食業(yè)和糕點雜貨業(yè)等,生意亦較興盛。因此,三原又被譽為“小北京”。
涇陽“在三原西南三十里,長安之北六十里,亦渭北一商業(yè)中心”。早在戰(zhàn)國及秦漢時期,隨著鄭國渠、白渠相繼開通,涇陽農(nóng)業(yè)逐步發(fā)達,剩余產(chǎn)品交換日漸頻繁。藉“鄭白之沃,甲于關(guān)輔”,至唐代,涇陽以膏腴之地惠及京師,農(nóng)業(yè)發(fā)達,手工業(yè)、商業(yè)遍布縣城各街巷。清道(光)咸(豐)以后,由于涇陽西北殷實小康諸戶“多以商起家,其鄉(xiāng)之姻戚子弟從而之蜀、之隴、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更有甚者遠涉緬甸、越南、印尼、俄羅斯等國,進行商貿(mào)活動。除經(jīng)營淮鹽、川鹽、棉花以外,湖(南)茶、蘭(州)煙、甘(肅)寧(夏)皮貨等大宗商品也在縣城加工中轉(zhuǎn),涇陽成為南北貨物集散流通的重要樞紐之一㈣。
隴海鐵路通達關(guān)中前,三原、涇陽商貿(mào)業(yè)的繁榮,可以從該兩地厘金征收額占全省總額的比重上得以體現(xiàn)。厘金是清政府開征的一種商業(yè)稅,因其值百抽一,即貨價銀1兩征收稅額1厘,故有此名。負責征收厘金的機構(gòu)叫厘卡,遍設于各商埠碼頭、水陸交通要道。由于厘卡逢貨即行抽厘,因此,厘金征收數(shù)額的多寡,可以真切反映各設卡商埠的貿(mào)易活躍程度。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陜西全省征收百貨厘金為白銀458 224.714兩。其中,南路湖廣貨入陜途中的重要集散地白河、龍駒寨以及東北路京貨入陜后的重要集散中心大荔、涇陽、三原、鳳翔等地的厘金征收額,幾占全省總額的60%。其中僅龍駒寨一地即占到20%,三原、涇陽、鳳翔等地的厘金征收額也較大。而作為陜西省會的西安,厘金征收額反較前述各地低下甚多,僅占全省總額的2.3%,尚不及大荔,分別僅約為鳳翔、三原、涇陽、龍駒寨的38%、28%、23%、11%。可見,西安雖然是陜西省會,城市規(guī)模也較其他關(guān)中城市為大,且有政治地位上的優(yōu)勢,但它并不是一個商貿(mào)中心城市,而是主要作為一個消費性城市出現(xiàn)。真正的關(guān)中商貿(mào)集散中心則是位于西安以北的涇陽與三原,口口相傳至今的關(guān)中民諺“天下縣、涇三原”,即是對涇陽、三原其時經(jīng)濟地位的生動寫照。
但隨著20世紀30年代前后隴海鐵路的漸次西展,昔日經(jīng)龍駒寨輸入關(guān)中的商貨大部改走鐵路,直達西安再坐地分銷。“民國以前,隴海鐵路距陜尚遠,西北物產(chǎn)如皮毛藥材之類,以三原為集散地,水煙以涇陽為中心,輸出時,經(jīng)藍田、龍駒寨、老河口以至漢口而運銷外埠。輸入品如疋頭洋貨,亦循斯道。迨隴海路展至靈寶,藍田、龍駒寨復行旅不便,于是貨物改由火車裝運,涇原商業(yè)遂日漸下降,西安乃代之而興。”楊繩信也指出,1930年后渭南、西安、咸陽、寶雞一線的繁華,是在隴海鐵路關(guān)中段展筑及鐵路運輸次第開通后,方才借交通上的便利逐漸取代渭北大荔、三原、涇陽、鳳翔一線城鎮(zhèn)的商貿(mào)地位而獲得的。
三、結(jié)語
誠如隗瀛濤先生所言,我國古代大多數(shù)城市往往都是因地處交通要道上才逐漸發(fā)展成為通都大邑的,同樣也往往由于交通要道的變遷導致城市地位的衰落。隴海鐵路通車以前,位于傳統(tǒng)渭北大道上的大荔、三原、涇陽,均是關(guān)中地區(qū)重要的傳統(tǒng)工商業(yè)城市,不論城市規(guī)模,或是經(jīng)濟基礎(chǔ),均遠勝于其他一般城市。但這一城市格局因隴海鐵路關(guān)中段的建設而徹底改變。隨著鐵路通達后西安、寶雞、咸陽、渭南等城市的興起,鐵路城市帶形成,關(guān)中經(jīng)濟重心從渭北移向鐵路沿線地區(qū)。這一變化,不但凸顯了鐵路這一新興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國城鎮(zhèn)格局調(diào)整中巨大的導向作用,同時對于當今中國高鐵網(wǎng)絡建設及區(qū)域城市格局變動亦有著巨大的歷史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