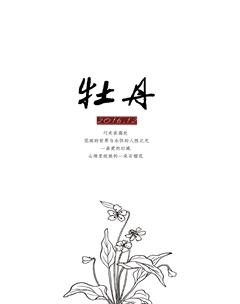槍打出頭鳥
史慧慧
《竇娥冤》是我國元代偉大戲劇作家關漢卿的力作,劇中竇娥表現(xiàn)出的反抗精神,猶如一只“出頭鳥”撕開了封建社會的骯臟面紗。本文首先論述該劇作為一只“出頭鳥”“出”在何處,其次分析“出頭鳥”被“槍”打中后存在的思想局限,最后試著找出這把“槍”的時代根源,以便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作品。
眾所周知,元雜劇《竇娥冤》中竇娥表現(xiàn)出的同不公命運作斗爭的反抗精神,歷來被人稱贊。在萬馬齊喑的元代統(tǒng)治時期,無疑是一只驚鴻烈鳥,一鳴驚人。
一、“出頭鳥”“出”在何處
(一)揭露了元代高利貸制度的剝削本質
元代統(tǒng)治時期,高利貸制度久盛不衰,它是社會底層人民苦難的發(fā)端,但凡沾上了高利貸,無不是家破人亡,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在《竇娥冤》中,竇天章就是因為向蔡婆借了二十兩銀子而無力償還本息,才把竇娥抵押給蔡婆做了童養(yǎng)媳。之后蔡婆婆也是因為向賽盧醫(yī)討要二十兩本利債而險些被殺,這才給了張氏父子可乘之機。可以說,高利貸制度是竇娥悲慘命運的始作俑者。《竇娥冤》直接揭露了元代社會底層人民飽受高利貸制度剝削的悲慘現(xiàn)實。
(二)諷刺元代社會底層地痞無賴魚肉鄉(xiāng)里的丑惡嘴臉
在元代社會,地主豪強奪人妻女,地痞無賴橫行鄉(xiāng)里,愈發(fā)猖獗,卻屢禁不止。《竇娥冤》中,張驢兒就是這樣一個令人發(fā)指的惡棍。他蠻橫無理,揣著骯臟的心思,逼迫蔡婆和竇娥做他們父子的接腳。這一無賴行為使竇娥原本就孤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緊接著,張驢兒又使奸計陷害竇娥,將其逼上絕路,造成了千古奇冤。關漢卿借張驢兒反襯出元代社會底層人民飽受地痞無賴欺凌的凄慘境遇。
(三)撕開了元代社會吏治腐敗的面紗
元朝的吏治腐敗墮落,民不聊生。《竇娥冤》中那位信奉“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人是賤蟲,不打不招”的桃杌太守,將貪婪和殘暴的本性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他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打碎了竇娥想要依靠“青天大老爺”為自己伸張正義的美夢。丈夫的去世,凄苦的寡婦生活沒有把竇娥壓倒。張驢兒的威逼利誘,她寧死不屈。但是,當披著“父母官”外衣的桃杌太守將她屈打成招時,竇娥心中的希望之火徹底熄滅了,腐敗黑暗的吏治制度把竇娥逼入絕境。一位本是安分守己的良家婦女卻橫遭禍端,甚至丟了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對封建吏治的辛辣諷刺。
(四)表現(xiàn)了竇娥的純樸善良、堅持反抗的斗爭精神
當純樸善良的竇娥受到張氏父子的無理逼迫時,她義正詞嚴地拒絕。當蔡婆婆欲要妥協(xié)于張氏父子時,一向尊重婆婆的竇娥毅然站出來反對,并對婆婆的妥協(xié)行為表示強烈不滿。面對酷吏的嚴刑拷打,她橫眉冷對,卻因為不忍婆婆受刑獄之苦而甘愿含冤招供。之后她在被押去刑場之際,因考慮到婆婆年老受不得刺激繞道而行。她在刑場上含恨控訴不公正的遭遇,喊出三樁血淚誓愿。這些都表現(xiàn)出竇娥作為社會底層婦女的覺醒,反映她作為被壓迫者的成長過程。“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即使是溫順的羔羊也敢于同惡狼一較高低,這是當時的統(tǒng)治者所不能忍受的。從中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
二、被“槍”打中后戲劇表現(xiàn)出的思想局限
(一)竇娥“節(jié)婦”形象和婦女解放的提倡相互矛盾
竇娥是一位被封建禮教馴化的溫順羔羊。她三歲喪母,七歲便被父親賣到蔡婆婆家過著寄人籬下的孤苦生活,之后禍不單行,正值17歲的花樣年華卻守了寡。但是,她仍舊恪守本分,“我將這婆侍養(yǎng),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順應口”,不發(fā)一字怨言,安守兒媳本分。所以,當張氏父子提出接腳之事,她為了維護自己的操守而誓死反抗。“我一馬難將兩鞍鞴,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卻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最后,竇娥在臨刑之前向婆婆表明自己對已亡丈夫的忠貞,“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祈求婆婆祭奠自己的亡魂。這些都表現(xiàn)出竇娥是一位被封建禮教禁錮的“節(jié)婦”,她將“貞節(jié)”二字當作自己言行舉止的道德準則。但是,這一道德準則卻是封建禮教束縛婦女思想和行為的工具,竇娥走不出封建禮教的怪圈,又何談自身的解放?
(二)竇娥對待天地的態(tài)度前后矛盾
竇娥是一位宿命論信奉者。“滿腹閑愁,數(shù)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此時的竇娥甘愿忍受凄苦的生活,因為她的心中始終希望得到天地的憐憫。但是,當那雙無情的命運之手殘忍地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淵時,她滿腔憤恨,“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堪賢愚枉做天”,字字泣血。然而,事與愿違,她信奉的天地最終還是把她送上了斷頭臺,無可奈何之際,她只能重新祈求“萬能”的天地應驗自己的三樁誓愿,以此來明志。竇娥對待天地的態(tài)度前后矛盾,她在現(xiàn)實中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她只能歸順于天地,但又終究逃不出宿命的藩籬。
(三)清官竇天章的塑造削弱了戲劇主題反封建的力度
在戲劇最后一折,作者又請出了一位肅政廉潔的竇天章,借他之手最終使竇娥冤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雖然這一“圓滿”結局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符合大眾的審美心理,但此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戲劇反封建的力度。無論是貪官還是清官,他們在本質上都是封建統(tǒng)治者維護封建秩序的幫兇,二者的區(qū)別在于貪官的行為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緒,妨礙了封建秩序的正常運轉,而清官卻充當了統(tǒng)治者和人民之間矛盾的“調停人”。封建官吏為民請愿的行為沒有脫離皇權中心,處于以封建秩序為半徑的圓圈。
三、“槍”指向何處
(一)男權社會下的封建禮教
在《竇娥冤》中,“節(jié)婦”形象的刻畫和解放婦女的提倡是背道而馳的。“節(jié)婦”觀念早已在勞動婦女心中根深蒂固。元代的封建統(tǒng)治者大力提倡封建禮教,用“夫權”“父權”等束縛女性的思想和行為,教化她們成為封建男權掌控下的犧牲品。“女不嫁二夫”“從一而終”“失節(jié)事大”的觀念成為女性行事的道德準則。再者,關漢卿作為封建男性的代表就更難超越自己的性別去維護女性的權益。所以,他看不到封建社會對女性的荼毒,也就不會為女性解放而發(fā)聲了。
(二)封建王權統(tǒng)治下的“宿命論”
關漢卿是一位干預社會現(xiàn)實,并試著找出解決方案的創(chuàng)作家。他敢于揭露封建制度的弊端,其反抗精神難能可貴。但是,在他的人生觀里,仍舊有封建“宿命論”的殘留。比如,竇娥將自己的悲慘命運歸結為天命使然,不可抵抗。“莫不是八字兒該載著一世憂,誰似我無盡頭”,“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回”。即使受了巨大的冤屈也只是悲憤怒罵,到了臨刑之際,她又重新祈求天地的憐憫,渴望天地應驗自己的誓愿。這一系列的態(tài)度變化表明了“宿命論”的觀念早已扎根于她的內心。
(三)封建秩序下的“君臣觀”
在《竇娥冤》的最后一折,關漢卿給了竇娥一個“圓滿”的結局,打走了貪官,迎來了“清官”,將讀者從沉重的悲劇氛圍中解救出來。這一結局讓人民重新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讓人民對那個“公正”的封建秩序重拾信心,從此又回到了甘當順民的軌道上。關漢卿雖然通過貪官桃杌的丑惡嘴臉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敗,但從“清官”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仍舊信奉封建秩序下的“君臣觀”。“清官”的為民請命實質上還是為皇帝開脫,只反了貪官,卻不反皇帝,不反封建秩序。
四、結語
悲劇的時代造就英雄的悲劇。在那個荒誕暴虐的時代,關漢卿秉持自己的學識干預現(xiàn)實的信念創(chuàng)造出來的《竇娥冤》,猶如一只勇敢的“出頭鳥”,在封建制度的風口浪尖上掙扎著、堅持著、創(chuàng)新著。雖然,用現(xiàn)代的眼光看待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分析直指封建制度弊端的《竇娥冤》,其作為中國古典悲劇的瑰麗之姿不可磨滅。在戲劇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它依舊熠熠生輝。
(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