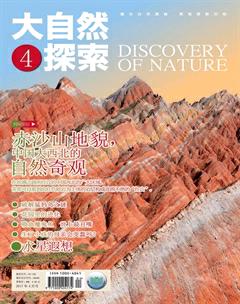向深海問藥
康慶玲
后抗生素時代,我們拿什么去對抗疾病?不過,在世界的水域中可能存在著新的藥物,它們只是等待被發現而已。
科學家發出警告稱,人類將面臨進入“后抗生素時代”的危險。一些細菌開始具備耐藥性,如此一來,抗生素正在喪失其對抗疾病的效力,會導致許多治療手段失效。如今,人們將尋找新抗生素的目光從陸地轉向了海洋。浩瀚的海洋中存在著諸多尚未為人所知的藥物資源,它們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等待被世人發現的那一天。
如今濫用抗生素飽受詬病,具有超強耐藥性的“超級細菌”的出現,讓人們對抗生素談之色變。譬如,2016年年初,美國兩名患者被發現體內存在對大多數抗生素具有抗藥性的大腸桿菌,包括對醫生作為最后手段的藥物也具有抗藥性。抗生素類藥物濫用導致抗生素已經逐漸對細菌失去了效力,這一趨勢令人擔憂。尋找新抗生素已迫在眉睫。
向深海探索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向自然世界探尋藥物來填充我們的藥品柜。譬如,阿司匹林就是從柳樹樹皮中提取的。到如今,科學家們卻又已經在病人和牲畜中發現,有的細菌具備對藥品治療的一定抵抗力。隨著抗藥性的增強,人們希望能在大自然“藥箱”中發現更多的有效藥物,找到可以治療疾病的藥物。
據估計,到2050年,如果人們不采取任何措施解決細菌抗藥性的問題,預計全球產生的醫療費用將高達69萬億英鎊。同時,還將導致每年1000萬人死亡的后果(即大約每3秒就會有1人死亡),這將大大超過癌癥和糖尿病的死亡人數。一旦某些具備耐藥性的細菌迅速蔓延,全球將籠罩在無法治愈的感染病陰影中。
從極地嚴寒的冰層,深海灼熱的熱泉,沐浴陽光的珊瑚礁到鮮為人知的內陸湖,覆蓋我們星球絕大部分的遼闊水域擁有豐富的水生物資源。其中,獨特的海洋環境,孕育出獨特的具有復雜化學防御系統的海洋生物(包括大量微生物)。海洋中的微生物總重量相當于2400億只非洲大象的重量。大約90%的海洋生物是微型的,有嗜黑、嗜鹽、嗜壓、嗜熱、嗜冷型,也有嗜酸、嗜堿、嗜重金屬型,還有特異內共生型等,其中有非常重要的抗生素資源。從海洋中,研究人員采集生物樣品,并對樣品進行培養、研究,發現了許多可能用于新藥研發的藥用生物。
執教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科學家和探險家特洛伊·墨菲教授對海底的沉積物、黏著在沉船殘骸的附著物以及體內存在特殊粘膠的海洋動物極為關注。不久前,他從美國密歇根湖帶回的一團泥漿中發現一種可生成兩個前所未知分子的海洋微生物化合物,對殺滅結核桿菌有著顯著的功效。
“在過去30年推出的所有新藥中約有一半是基于自然世界中發現的分子制成的。但是,已有的抗生素對細菌的作用已經窮盡,研發新抗生素迫在眉睫,可失敗率極高,這已不是什么秘密,剩下的細菌都太難對付。”墨菲說道,“我們很難找到一組能夠治療特定疾病的分子,且很難在人體極其復雜的生理環境中進行測試。”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墨菲正試圖使樣品收集過程更加智能化。這一過程可以說是近幾十年來藥物開發實踐中從未發生過的重大改革之一。墨菲指出,在原產地尋找分子是藥物研發的重要部分,因此他決定利用一種新資源:公眾。
與休閑潛水者的聊天讓墨菲產生了在沉船中尋找海綿的想法。這些其貌不揚的生物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原地一動不動。它們沒有器官,沒有明晰的組織,從流過身邊的海水中濾食,譬如細小的碎石和大量細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細菌構成了海綿生物量的30%或40%。
墨菲并沒有花費大量時間和財力親自去收集海綿,而是發起了一項全民科學項目,讓潛水者在潛水時為他收集小樣本。2015年夏天,他在美國五大湖分發出去很多收集工具,收到了40多份海綿樣本。墨菲希望在盡可能多的地區收集樣本,用以繪制海綿和細菌在湖泊中的分布情況。
墨菲在實驗室里對收集到的樣本中的抗結核病分子進行測試,檢測是否可將其用于新藥研發。即使它們無法用于制成新藥,但他相信它們仍會有可用之處。它們體內所含的天然抗生素能夠消滅結核桿菌,治療風濕和神經系統疾病。且對肺結核顯示出選擇性的抗菌活性,在殺死結核桿菌時,幾乎不會對其他細菌造成影響。 找出這些分子如何選擇性殺死結核桿菌可以揭示關于肺結核這一疾病本身的重要信息,且可能有助于研發有效藥物。
多樣化的海洋
20世紀50年代,生物勘探者首次勘探海洋的最初目標是珊瑚礁。這些聚集了多種物種的生態系統值得一探,它們已經生產了許多天然產品,其中一些可應用于藥物開發。
美國于1969年批準使用的腫瘤化療藥物阿糖胞苷最初是在佛羅里達群島的一處礁石的海綿中發現的。從加勒比海的海鞘中分離出來的化合物制成的抗癌劑曲貝替定于2007年在歐洲正式批準使用,并于2015年在美國批準使用。
在其他地方,研究人員正在尋找新的化學物質,甚至在海洋深處進行更進一步的尋找。 由賈斯·帕斯教授領導的國際團隊正在海底最深處的溝渠里尋找新的抗生素。“每個溝渠都可能有數百萬年的演變歷史。”他解釋說。帕斯和他的合作伙伴將無人探測器發送至海底最深處,帶回攜帶有獨特細菌的泥漿。近些年,在實驗室中使這些特殊生物存活的技術不斷發展,因此可以在實驗室進行實驗。他們做了近10萬次測試,試圖發現抵抗對多種現有抗生素抗藥性越來越強的ESKAPE病原體的化學物質。
帕斯團隊試圖鎖定兩種可以更大規模生產的化合物,并進行臨床試驗。到目前為止,最令人振奮的是,發現了可有效對抗神經系統疾病尤其是癲癇和阿爾茨海默病的化合物。
海洋藥物利用產生的惠益共享
2010年,《名古屋議定書》簽訂生效,使簽訂此類惠益共享協議成為法律要求。這一議定書的產生和實施,明確了深海資源的發現和利用的受益權利,明確了在海洋深處收集任何資源之前,研究人員必須與原產國簽訂書面協議,成果共享。但不是每個國家都參與簽訂了《名古屋議定書》,如美國。這是因為離海岸超過200海里(370.4千米)的海域屬于公海,很難從技術層面上定義屬于任何國家,因此對公海海域實施管轄在實踐中很難實現。此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涵蓋了包括深海采礦和鋪設電纜在內的一些活動,但它并未涉及生物多樣性。2015年3月正式討論修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試圖將生物勘探涵蓋其中,但目前仍未作出決定。77國集團認為,深海勘探發現屬人類共同繼承財產,每個人都可以分享其利用產生的惠益,這意味著不應該允許某一國家或某一公司單獨享受惠益。
依據美國和挪威主張的公海自由原則,任何國家可在公海自由進行生物勘探,如任何人可在公海隨意捕魚一樣。他們可在任何地方進行研究并享受研究帶來的利益。對此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團體都希望能得到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然而,似乎要幾年后,才能實現對公海生物勘探的監管。
生物勘探者需要加快進度。2016年夏天,世界各地均頭條報道了曾經生機勃勃的大堡礁如今變得黯然失色、荒蕪貧瘠。人類活動繼續威脅著海洋、河流、湖泊的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我們希望能在對地球上的水資源造成不可逆的污染和破壞之前找到我們所需的藥物和治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