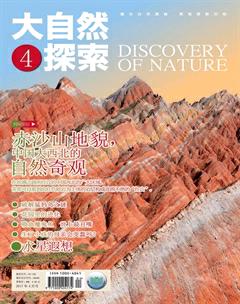破解猛犸島之謎
吳青
圣保羅島上的冰河期巨獸們,比大陸上的同伴多活了好幾千年。那么,它們為什么最終也滅絕了?
幾千年前的一天,在白令海中央一座小島上,一頭長毛猛犸象(也稱長毛象,簡稱猛犸)失足掉入一個無法逃出的坑狀洞穴,然后死在那里。2003年,美國賓州大學古生物學家格雷漢姆與同事進入這個洞中,搬起一塊巖石,結果發現了一根干干凈凈的猛犸牙齒。它呈長條狀,表面不規整。整個看上去,這根象牙就像是一根大面包。格雷漢姆回憶說,“它看上去就好像剛剛被從猛犸口中拔出來一樣。”
在自己的職業生涯里,格雷漢姆處置過數百只猛犸牙,但來自美國阿拉斯加州圣保羅島的這只猛犸牙卻很特別。它將讓格雷漢姆及一個跨學科專家團隊踏上一次探索之旅,去重建這頭猛犸的生存環境,并且破解一個奧秘。對于今天因氣候改變而面臨滅頂之災的動物來說,這個奧秘也意味深長。
當碳測年證明這只猛犸牙只有6500年的歷史時,這個奧秘就開啟了。這只猛犸牙(或者說這頭猛犸)竟然比在北美大陸上發現的任何猛犸都年輕好幾千年。格雷漢姆不得不思考:當大陸猛犸滅絕后,風吹雨打的彈丸之地——圣保羅島上的猛犸卻繼續存活了好幾千年,那么,最終是什么把它們也趕盡殺絕?
時光回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出生于英國的生態學家保羅,從圣保羅島希爾湖湖底采集到一個沉積芯,其中的分層揭示這個地方的沉積物記錄至少延伸到1.4萬年前。希爾湖距離格雷漢姆發現猛犸牙的洞穴僅400多米。因此,對于格雷漢姆的疑問,答案或許就藏在希爾湖湖底的黑泥中。
在發現這只猛犸牙10年后,格雷漢姆及其團隊重返圣保羅島,準備從新提取的沉積芯中找尋線索,破解這座小島及島上猛犸的歷史。
深入奧秘核心
圣保羅島是白令海中央一系列火山島中最大的一座。天氣給上島探索的格雷漢姆團隊造成了麻煩。他們一上島,雨水很快就變成冰雪,他們不得不呆在島上唯一的小鎮里。這個小鎮里住著該島500名居民中的大多數,其中絕大多數人是阿留申人。200多年前,他們的祖先被俄羅斯商人帶到圣保羅島上,捕獵北方海狗。
格雷漢姆團隊在鎮上等待云開霧散。這里有俄羅斯東正教教堂的洋蔥形圓頂,有色彩繽紛的房子,還有海鮮加工廠。土生土長于這座直徑65千米島上的北極灰狐,在格雷漢姆團隊的大本營外一點也不怕人。這個大本營是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一個研究站。
清晨,格雷漢姆團隊向著希爾湖進發。這座火山湖的邊緣被冰雪覆蓋。格雷漢姆團隊在30多厘米厚的冰層上鉆洞。隊員們把每節1米長的多節管子串接到取芯管上,然后讓這個裝置通過湖水一直伸進湖底。幾分鐘后,這個裝置被取回,其中包括完全按照沉積順序保存的沉積層。
在取芯管提取的泥巴里,保存著掉進、被沖刷到或者“定居”在湖底的物體的法醫學記錄。這些物體包括真菌孢子、植物殘片、古代花粉、火山灰、小型甲殼綱動物的殘留,甚至包括猛犸在湖中打滾時掉下的DNA。格雷漢姆團隊將使用這些證據構建圣保羅島幾千年來的氣候變化,確定島上猛犸的滅絕時間。
隊員們從沉積層下面開始,一米一米地取樣,然后把樣本放進塑料管中。隨后,這些管子被密封并放進睡袋中以避免凍結,因為凍結可能扭曲分層的細節。這項工作復雜、低溫而又費體力。到了一天工作結束時,泥巴在隊員們的衣服和頭發上凍成了殼。
每一米芯樣都讓我們回到越來越遙遠的從前。當一名隊員引導第六節芯樣進入一根管子時,他注意到泥巴從帶有布丁紋理的柔和褐色變成色調統一的黑色。科學家們推測,這一變化匹配的是差不多6000~8000年前的沉積物,而格雷漢姆發現的猛犸正是在這個時期死于洞中的。這意味著,如果猛犸DNA只存在于這節芯樣的下層而非頂層,那么這節芯樣就包括圣保羅島猛犸滅絕的時期。
猛犸最后陣地
自從上一次冰河期即大約1.2萬年前以來,圣保羅島的無樹凍原地貌鮮有改變。很容易想象這樣的場景:猛犸站在斜坡上,用長牙清理冰雪,尋找植被食用。入夏,它們踩踏著凍土地帶的小小野花,步履沉重邁向希爾湖——島上主要的淡水源頭之一。
科學家曾經估計,猛犸最后是在1萬~1.4萬年前從北美洲消失的。然而,如今的發現卻證實它們此后在圣保羅島上又堅守了好幾千年。在俄羅斯北極深處的弗蘭格爾島上,猛犸存活得可能更久。在那里,科學家發現了只有4000年歷史的猛犸牙。也就是說,當埃及人建立起第一座大金字塔時,弗蘭格爾島猛犸依然活著。
與弗蘭格爾島一樣,圣保羅島也是一座孤島。在上一次冰河期的高峰期,即大約2.1萬年前,圣保羅島是白令陸橋南部邊緣的一個火山活躍地帶。猛犸、劍齒虎、短臉熊及其他巨獸漫步于北美洲與歐亞大陸之間的通道。到了大約1.1萬年前,氣候開始變暖,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沒了這座陸橋。在大約2000年的時間里,該地區則轉變成了一座島。猛犸被困在了這座島上,但正是這種與世隔絕保護了它們——至少在一段時間里是這樣。
科學家對猛犸在上一次冰河期從大陸上滅絕的原因爭論不休。有人說,這是由于氣候改變。也有人說,其實是人類把猛犸斬草除根。就算在格雷漢姆團隊內部,人們對此也看法不一。有人指出,猛犸滅絕的時機差不多正好匹配人類遷徙到猛犸棲息范圍內的時間,這難道純屬巧合?在北美大陸上,人類的到來、氣候劇變和猛犸滅絕發生在差不多相同時間。然而,在人類到來之前,猛犸挺過了幾十萬年的氣候變化,一直徜徉在地球上。如此看來,如果它們滅絕的原因不是人類,還能是什么?但也有人指出,氣候才是猛犸滅絕的主要原因。雖然人類對于猛犸走向窮途末路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但猛犸和其他冰河期巨獸實際上本身當時已經在淡出歷史長河。不管有沒有人的因素,它們的滅絕都是必然的。因此,雖然一些猛犸在氣候轉變中存活下來,但它們每一次都被傷了元氣,最終的滅絕不可避免。
來自希爾湖的芯樣,不可能終結有關冰河期巨獸滅絕原因的爭論。圣保羅島的隔絕,意味著它與其他一些地方不同,島上猛犸沒有受到人類影響。沒有證據表明:在俄羅斯商人于18世紀后期登臨該島之前,有人來過此地。因此,至少是在圣保羅島上,猛犸滅絕的原因更可能是氣候改變,但棲息地縮小也可能是原因:隨著海平面上升,該島可能會變得太小,不足以支撐巨獸種群。
確定圣保羅島猛犸的終結,并非只具有歷史、古生物學和考古學意義。全球范圍內的許多物種目前正面臨同樣的壓力:氣候轉變、人類侵襲、海平面上升。氣候改變能否單獨導致物種消亡?或者,氣候改變的確是一個壓力因子,但與其他壓力因子結合,是否更容易造成物種消失?因此,發生在更新世末期即大約1.1萬年前的大滅絕事件,對我們分析目前的物種滅絕浪潮以及怎樣讓滅絕幅度降到最低來說,無疑有重要啟發。
在經過4天取樣(取樣一度被暴風雪中斷),格雷漢姆團隊已經有了180千克的泥巴。樣本被裝在45米長的管子里,運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實驗室。這個奧秘的第二章節即將展開。
猛犸象偵探
直到2016年5月,格雷漢姆團隊才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蘇達大學“國立拉庫斯特林核心實驗室”,與他們提取的希爾湖芯樣重逢。該實驗室員工已經將芯樣切成兩半,拍攝了高像素照片。格雷漢姆團隊將花3天時間,使用不銹鋼抹刀把芯樣切割成很小的一段一段的。他們將把成千上萬的這些微芯樣分裝進小塑料盒,帶回分布于整個北美洲的各自的實驗室。事實上,猛犸當初在整個北美洲都有分布。
美國加州大學科學家貝斯是格雷漢姆團隊成員之一。她第一個對芯樣做檢驗,因為她的團隊要進行的是最敏感的測試,稍不注意就會在處置樣本的過程中造成樣本污染。他們的工作是:尋找沉積層中的古猛犸DNA。
在一名研究生協助下,格雷漢姆團隊的另一位專家威廉姆斯要尋找猛犸的一種代理物——小莢孢腔菌。這種真菌生活在大型食草動物的糞便中。威廉姆斯還要尋找古代花粉顆粒,它們可能揭示希爾湖周圍當時的植被情況。
在美國阿肯色大學,科學家馬修及其同事將檢測芯樣中的硅藻、水虱及其他生物的殘留,目的是了解湖水溫度和透明度隨時間變化情況。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科學家杜安妮將尋找芯樣中的火山灰層,這些層次可能會被與該地區已知的火山爆發聯系起來。這一結果再加上對芯樣中發現的植物殘片進行碳測年的結果,將讓杜安妮團隊確定芯樣中各個層次的年代。火山灰層也可能確定火山爆發是不是造成猛犸滅絕的原因。
隨著芯樣的劃分,專家們各自散去。他們要花超過兩年時間分析和討論這些樣本,目的是確定圣保羅島猛犸滅絕時間和滅絕原因。
時間定了
貝斯團隊率先把芯樣中發現的未經分類的DNA片段與猛犸在世的最近親——非洲象的基因組進行了對比。兩者匹配。更讓他們高興的是,2015年,他們得以把希爾湖芯樣DNA與另一個團隊新近測序的猛犸DNA進行比對,結果與年代為5650年前~1.085萬年前的芯樣都匹配。1.085萬年前的芯樣是在圣保羅島上采集到的最古老芯樣。
為了排除隨機匹配的可能性,貝斯團隊把芯樣DNA與二趾樹懶的DNA進行了對比。在過去2萬年中,這種樹懶出現在北極圈的概率為零。為了進一步檢測檢驗結果,他們還把未分類的芯樣DNA與那些最可能污染樣本的動物(包括人)的DNA進行對比,結果都不匹配。這樣一來,貝斯團隊確信芯樣中的DNA真的屬于一頭猛犸。
與此同時,威廉姆斯團隊找到了他們尋找的小莢孢腔菌,還找到了另外兩種可能充當猛犸代理物、與分辨相關的真菌孢子。在這3種孢子里,有兩種從芯樣沉積層中消失,而這兩個沉積層相隔不到2厘米,其代表的時間間隔只有幾十年。古猛犸DNA消失于同一時間段。
杜安妮團隊辨識了一個芯樣火山灰層,它與圣保羅島3595年前已知的一次火山爆發匹配。這進一步增添了他們對確定圣保羅島古代事件時間線索的信心。通過上述跨學科的多方努力,科學家們最終確定圣保羅島猛犸滅絕事件發生在5600年前,前后誤差100年。對于史前滅絕事件來說,這可能是對時間的最精確測定。至此,科學家們開始著手破譯圣保羅島猛犸滅絕之謎的最后一部分:猛犸滅絕的原因是什么?
最終一擊
格雷漢姆以及團隊中其他多位成員首先排除了一些看似可能的原因,例如植被變化或對猛犸不友好的因素(例如人)。芯樣中的花粉顯示,圣保羅島上的草本植物被灌木取代,但這只是在猛犸滅絕之后。有一種可能是,氣候轉變導致島上植物群落構成發生改變,或者,只是因為猛犸不再踩踏地面,灌木生長不再受到壓制,所以灌木才異軍突起。
研究數據的確表明,圣保羅島猛犸滅絕時期的溫度比滅絕事件發生前有些升高。隨著更新世末期冰雪融化,海面上升,圣保羅島面積開始迅速縮小,直到大約9000年前。到了這個時候,圣保羅島土地流失速度減緩。大約6000年前,該島達到現有面積,比美國弗朗西斯科市小一些。島面積萎縮很可能導致島上猛犸數量減少,島上資源也變得不足。
但最終對猛犸來說的致命一擊,卻讓人大吃一驚。從大約7850年前開始,芯樣沉積層中硅藻和水虱種類及數量發生變化。其變化方式表明,湖水變得越來越淺,透明度越來越低。希爾湖開始干涸——這并不奇怪,就算氣溫上升幅度不大,也足以增加湖水蒸發。猛犸逐漸失去了主要水源。事實上,大象每天都需要新鮮的水,每頭大象要飲水70~200升,猛犸很可能也如此。
由于島面積減少,氣溫升高,或許再加上猛犸自己導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圣保羅島上的猛犸最終就因為饑渴而走向末日。格雷漢姆團隊由此就破解了圣保羅島猛犸死亡之謎。但這些猛犸為什么會比北美洲其他地方的猛犸存在得更久,這個問題更難回答。科學家認為,圣保羅島的隔絕能讓猛犸不受人類影響。但這個推測很難被證明。格雷漢姆提出,大陸植被變化方式可能與圣保羅島的不同。不管是哪種原因,圣保羅島猛犸的隔絕最終也帶來了不利的一面:當環境改變使得這座島不那么適合棲居時,猛犸群就無處可去,只能坐以待斃。
對于今天島上生物種群的脆弱性來說,猛犸滅絕無疑是一個警示。格雷漢姆指出,通常情況下,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氣候變化,但在圣保羅島上它卻并非是不重要的。雖然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對其他地方的其他物種來說,也有其他限制因素,例如棲居地喪失和食物變得難找。對圣保羅島猛犸滅絕原因的研究表明,許多島上生物種群——不僅僅是在白令海,而且是在全球各地——都可能因為氣候改變而陷于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