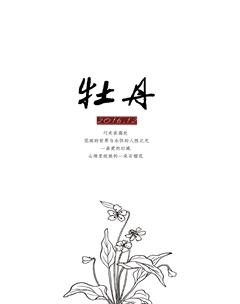淺談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中的鄉土意識
孫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土作品中,鄉土呈現出三類狀態:以往充滿魅力的家鄉、實際中黑暗的家鄉、意識中未來的家鄉。在這三類相異狀態下的鄉土所引起的離愁別緒中,潛藏著鄉土文人“得到伊甸園—遺失伊甸園—重返伊甸園”的思維,同時讓鄉土小說在表達方面也不盡相同。
在我國當代文學歷史中,很少有其他的小說種類像鄉土小說一般能夠長盛不衰。從魯迅被冠以“鄉土作家”之后,歷代大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家都認為自己是鄉土小說作家。其寫,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格調迥異,側重點也呈現出差異性,然而他們卻共同造就了鄉土小說寫作的黃金時代,為沉悶的文壇注入了一針強心劑。筆者在下文中將淺談20世紀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中的鄉土意識。
當新文學時期邁入第一個10年階段,《中國新文學大系》就誕生了。這是由各編纂人寫成的導論,對10年的文學作品的特性進行闡述。當中,作為當時的社會主流寫作類型,鄉土文學開始被界定與研究。
例如魯迅,其是從自身的角色特點——遠離家鄉、僑居城市來進行寫作的,其寫就的鄉土文學包括故鄉的記憶、文章的情感格調、離鄉的感受等。此處,尤其令人關注的,是鄉土文學中的離愁別緒,已經不單純是我國唐代詩句中所描繪的客居異地的對家鄉的思念,這種思念只是外出的人們因異鄉與鄉關的地理間距所引發的,而鄉關這個概念是凝定的,缺少時間的波動,它由三類時態,即過去、現在、以后,以此來影響鄉土文學創作。因此,在鄉土文學里,擁有三類相異時態的鄉土描繪景象:一是過往的、目前已經消失的、讓作者極為掛念的家鄉;二是暗黑因素繁多、招人厭惡的家鄉;三是期待中的新家鄉,寄托了作者對家鄉的思念與執念。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這種以三類時態抒發思鄉情懷的離愁別緒中,存在一個鄉土的伊甸園—失樂園—重新擁有樂園的思辨思維。其實,這是一種潛在的邏輯。在發展期的鄉土文學中,還要以心緒或感情作為引導,還沒有升華到明朗的理智認知。發展一段時間后,這類潛藏的邏輯轉換成了理智的思辨邏輯,當初隱約的思想情感,演化成濃郁的鄉土緬懷情感,對既定區域形而下的鄉土懷念升華為對整個國家當前存活模式與以后命途的形而上的研究,鄉土文學的思維與感情韻味形成,讓鄉土文學的根基更為牢固,并由此而誕生鄉土文學的創作熱潮。
從發展期鄉土文學的趨勢與涵義來看,魯迅在二三十年代的歸納與評論可謂一語中的。然而,其對鄉土文學內藏的進步潛能還沒有進行研究,也并未預估到以后鄉土文學創作將成為潮流。所以,雖然是魯迅先生最早開始給出鄉土文學的定義,其僑居首都并首先描述了故鄉的情景,然而魯迅沒有承認自己創作的文學是鄉土文學。筆者揣度,魯迅所寫的作品中思鄉的離愁別緒還處于感受態勢,不能囊括其思想。但是,其曾指出許欽文為其第一個短篇作品集起名為《故鄉》,并指出其作品隸屬鄉土文學范疇。根據這種想法,當魯迅自己的作品問世后(《故鄉》),其實在潛移默化中也變成了鄉土文學作者。實際上,魯迅以鄉土為闡述對象的小說,正是鄉土文學的一種。魯迅自身,加上任職于《淺草》的廢名、沈從文等,均為二三十年代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
魯迅的《故鄉》,開頭便闡述“我”超過二十載后重新返回家鄉時的所見所聞。在作品中,在“我”的潛藏意識中,家鄉早已改了容貌。印象中到處可親可愛的家鄉被時間的洪流埋葬在了“我”的意識中,其情景無法再追尋。當“我”聞知媽媽提到童年時期的好友閏土時,這情景又探出了頭。魯迅在描寫其和閏土的往事時,包含“我”與閏土的交際與友情編織的回憶圖像。而魯迅另一部小說《社戲》,其印象中的場景變為了現實,寫的是“我”與一些家鄉伙伴聽社戲、盜羅漢豆的有趣事件。這所有的內容,在魯迅的小說中,已經不單純是對過往人事的懷念,而目的是在于構建一個人們相互間、人與環境間一派祥和生機勃勃的人類的精神家園。
這樣的境界,就是已成過往的家鄉的象征。
但是,不管是《故鄉》或是《社戲》,這過往的家鄉的美的畫卷,卻是目前家鄉近況與城市生存環境造就的。饑餓、苛捐雜稅、兵災、官僚導致的不堪負重的人生景象,讓閏土變得木訥、神經質;讓豆腐西施這種農村美女失去了原來的恬靜與樸實的品質,變得兇惡,只為自己打算。人們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打破了以往家鄉的一派祥和的氛圍。而在另一部《社戲》中,“我”的兩回城市聽戲與少年時代聽戲的強烈反差,并非來源于戲劇,而是來源于聽戲所呈現出的人文環境——城市與鄉村人們間的隔閡,其為當年極富人情味的家鄉籠罩上了一層陰影。
暫且不探討“我”印象中的家鄉的魅力,文人對從村莊到城市生存環境普遍的感覺正在失真,這也是鄉土文學中關于以往家鄉的相同的心理背景。這類對生存環境惡化的感受,致使鄉土文學更多地成為了批判文學。王任叔的《疲憊者》、許欽文的《瘋婦》等,是有關普通人物悲慘遭遇的闡述,其都體現出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垂死掙扎;王魯彥的《菊英的出嫁》、許杰的《慘霧》等,記錄了包含水葬、冥婚、鄉村打斗等鄉村的迷信行為,闡明其阻礙了我國文化的發展。而王魯彥的《黃金》等,則將重心轉移到家鄉的當代流變,因為當代文化的入侵,鄉土圈子內人物間的關系變成了罪惡的錢財貿易,不得不讓人感嘆世風日下。而魯迅的鄉土小說,如《祝福》《阿Q正傳》《離婚》《風波》,已經不單純是對家鄉人物的窮苦命運的描述,而是直接指向家鄉人物的內心世界,希望通過自己的描寫讓更多的人關注鄉土人物的精神世界。
以上所闡述的小說呈現的家鄉情景,著眼于家鄉目前的生存模式,并未發現有過往的美夢,也并未出現有關家鄉未來的美夢,進而讓鄉土文學中一部分作家被冠以寫實派的頭銜。鄉土文學中的寫實派,到30年代,如茅盾、張天翼等作家,從普通的家鄉痛苦現狀的描寫過渡到對鄉土的社會階層的解析與評論,進而演變成普羅文學,已經超越了普通的鄉土小說。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也有另外一部分文學家,如廢名、沈從文等,依然無比眷念以往的家鄉。這樣的情況,來源于作家對當前家鄉與寄居大都市的生存形態感到雙重不滿。這部分文學家是家鄉夢的追尋者,同時又極力否定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廢名前期的鄉土小說內,滿是類似魯迅《故鄉》中的悲涼,而《莫須有先生傳》的精神歷練,也是廢名一直所尋求的道。文中講到,源于城市人的粗俗,莫須有先生才有了遁世與隱居的意圖。而盧焚也是對家鄉感到厭惡,從而產生避世而居的念頭,結果讓人極為絕望;沈從文離開湘西的初衷,是源于其在20歲以前對家鄉的印象,沈從文撰寫了家鄉的黑暗現狀,讓其猶如身處阿鼻地獄。來到城市以后,沈從文發現其面臨的城市生活情景,又產生了對自然本性的普遍失望。城市人生與家鄉場景的互參,讓沈從文的寫作風格開始定型。
正是這類對目前的家鄉與城市人生境況的雙重絕望,讓這部分文人極為眷顧以往的家鄉。《竹林的故事》已經昭示出廢名的避世意圖,鄉土意識強烈的作家們,在這種劇烈的反差中思考人生,不得不說極為中肯。
綜上所述,不管家鄉與以前的樣子有何區別,重新返回伊甸園、重新建設伊甸園均表達了文學家對故鄉的愛。從科學的視角來講,都是空中樓閣。而正是這類空中樓閣,成為中國鄉土小說的指引燈塔,讓鄉土文學家不至于迷失方向。筆者認為歷史上對這類想法全盤否定的狀況必須改變,將其當作鄉土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這部分鄉土文學家“洗清冤屈”。
(河北衡水市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