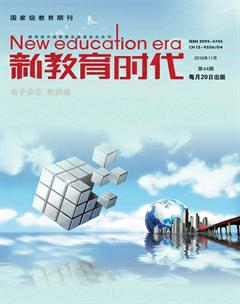試論建安文學及其繁榮和發展的原因
摘要:本文論述了建安文學繁榮和發展的基本狀況,并就其繁榮和發展的主要原因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指出時代的社會生活、社會意識、經濟發展、文學發展等是基本原因。建安文學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建安文學繁榮發展主要原因
建安是漢獻帝劉協被曹操迎到許昌后建立的一個年號。建安時期即公元196到公元220年間,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執掌著東漢政權。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建安文學即指建安時期到魏初一段時期的文學,主要是指北方的魏國的文學。
建安文學時期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其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建安文壇作家大量涌現,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菜琰是其代表作家。二是詩歌、散文、辭賦以及文論等多種文體都得到了發展而以詩歌的成就最為顯著。繼《詩經》以后,四言詩再次放出光彩;緊接著{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開始興盛并獲得我國詩歌史上五言詩的第一個偉大豐收。五言詩是建安作家普遍運用的詩體,它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嚴格意義上的七言詩也正式出現,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詩。漢代的樂府詩主要是敘事,建安詩人學習創作的樂府詩則已從敘事向寫景抒情方向發展了。曹操的詩全是樂府歌辭。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他以樂俯古題寫時事的做法對后代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題新事樂俯和白居易的新樂府都有很大的啟示。曹操二子和鄴中七子也都用樂府舊曲改作新辭,寫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樂府詩,很是出色。曹操,魯迅謂作“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散文只用簡潔樸素的文筆把要說的話自由地寫出來,卻自有鮮明的個性。他的“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表現了建安散文的新風貌,對魏晉散文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辭賦是漢代最發達的文學形式。然漢賦多鴻篇巨制,內容習于為文造情,形式行文俗套,辭多碓砌,千篇一律。建安作家改造了漢賦,多作抒情小賦,為情造文,各有個性和風格。王粲的《登樓賦》是其代表作品。建安文學樹立了開展文學批評的優良學風。曹丕的《典論*論文》為我國第一篇文學理論批評專論。他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總之,建安文學繼承了前代文學的優良傳統,并能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了重要一頁。
建安文學為什么如此繁榮和發展呢?前人對此,亦有論述。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又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社會生活的發展是文學發展的客觀基礎。文學隨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展。首先是文學內容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社會生活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就給文學提供了新的表現對象、新的社會內容。東漢王朝經過黃巾大起義后已名存實亡,各豪強軍閥紛紛擁兵割據,在長期的混戰中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建安詩人大都經歷過漢末長期亂離,對現實生活有切實感受。如曹操本人即為亂世英雄,其部分樂府詩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其“薤露行”、“蒿里行”被明代文學家鐘惺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曹植則“生乎亂,長乎亂”,長期隨父轉戰。他的《送應氏》、還有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阮禹的《駕出北郭行》、菜琰的《悲憤詩》等,或寫征戰之苦,或述社會之亂,或記難民之流難,或訴孤兒之苦楚,或敘個人之遭遇,從不同側面,給我們描繪了自董卓之亂到赤壁之戰19年大混亂所致亂世之情。他們以悲憤的筆觸,描繪過洛陽都誠“斬截無孑遺,”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長城腳下“死人駭骨相撐拄”。蔡琰《悲憤詩》悲憤交加地敘述了她被掠入胡到歸漢的痛苦經歷,重現了戰亂的慘狀。建安作家不僅是亂世的悲歌者,而且是國家統一的熱烈追求者。他們慷慨歌唱要求實現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直抒為實現這種理想而建立功業的雄心壯志和英雄氣概,充滿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如曹操的《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老驥自比,吐露了自己老當益壯的斗志。曹植的《白馬篇》:“父母且不顧,何言妻與子。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描寫了一位聱鏊戰疆場的青年戰士的形象及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陳琳、劉楨等人的作品也洋溢著積極進取的精神。社會生活的發展不僅給文學提供了新內容,同時也促使文學新形式的產生。建安文學五言詩的成熟運用,七言詩的定型,抒情小賦的發展,文學批評專論的出現等都給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增添了光彩。
文學的發展往往受到其他社會意識的強烈影響、尤其是政治思想的影響。漢末社會的巨大變動也引起了社會思想的變化。漢代自武帝以來,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這時,為了適應新的現實的需要,“廢黜百家,獨尊儒家”局面打破了,名、法、兵、縱橫家等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思想界呈現出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這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統治階級或統治者的愛好文學和對文學的提倡以及對文人的重視和延攬對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也有一定的作用。這里不妨引用前人的著述來加以說明:“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啷;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七子除孔融外都和曹氏休戚與共,形成了一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集團。
經濟是文學發展的最后的決定性的因素。文學的高度發展往往有其社會經濟根源,或者是作為經濟繁榮的結果,即由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或者是由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即為經濟繁榮發出的呼聲。漢末由于軍閥混戰,繁榮的中原變得一片凄慘。“至少是一個英雄”(魯迅語)的曹操,對現實有較清醒的認識,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強兼并,禁止豪民轉嫁租賦于農民,廣興屯田,用軍事組織把廣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廣羅“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發展了生產,統一了北方,社會生活較前安定,為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樣的環境中,建安文學由漢末品評人物的風氣,由人及物,促進了文學批評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的《典論論文》把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看到了文學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價值。他還分析了詩賦奏書銘誄等文體的特點,評價了建安諸子。曹植、王粲、徐干、應揚等的書記論文中也都夾雜著不少關于文學問題的卓見。這種文學批評對提高作家地位、掃除文人相輕的惡劣風氣、促進文學創作的自由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文學的發展還有其自身的規律。文學在發展過程中還有其自身的繼承和發展的規律,這既表現在內容上又表現在形式上。建安文學亦是如此。建安作家繼承了周代《詩經》和漢代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時代的動亂社會現實,既富于憂國之思又有著濟世的宏愿,慷慨悲涼、語言剛勁、形成了俊爽剛健的風格,后世譽為“建安風骨”,對中國文學發展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曹操繼承了《詩經》四言詩的形式,其他作家普遍采用《古詩十九首》趨于成熟的五言詩形式,使五言詩逐漸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漢代的大賦,以鋪陳排比的手法、堆砌辭藻、富麗堂皇,多以帝王貴族的宮苑、巡游、聲色等豪華生活為題材,為統治者服務。“或以抒下情而通諷渝”,然其效果甚微,揚雄嘗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故東漢后開始出現抒情小賦。建安作家多用此體,使賦也得到運用。總之,建安文學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有其鮮明的特色,后世對它的稱頌是高而不為過的。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簡介
董迎春(1959.01-)男,漢族,湖北荊州人,本科,荊州理工職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