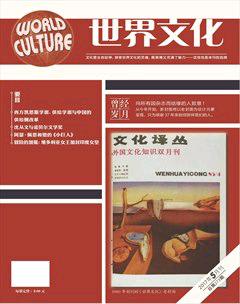《聞香識女人》:美國“嬰兒潮”一代時代精神與當代美德主義的沖突
謝天海
《聞香識女人》是國內影迷耳熟能詳的作品。本片出品于1992年,由好萊塢著名編劇波·戈德曼編劇,馬丁·布萊斯特導演,在中國擁有大批擁躉,被視為眾口一詞的佳作。然而,這部電影在國外影迷和影評者對其評價中兩極分化非常嚴重,五星級評價數量眾多,一星差評同樣俯拾皆是,批評該片時間冗長,結構拖沓,過分煽情和理想化的聲音不絕于耳。是什么導致了本片在美國觀眾中的評價如此褒貶不一·筆者看來,除去美國多元文化觀念造成的審美觀念不統一之外,這部電影當中更多地顯示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社會風氣向專業化和美德主義轉化與60年代以來盛行于美國的“嬰兒潮”一代時代精神之間的沖突。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這部電影的人物塑造與情節沖突,揭示這兩種價值觀念沖突對于美國90年代乃至當今美國社會的影響。
斯雷特中校:失落的20世紀60年代的精神代言人
影片中的斯雷特中校,是一名越戰退伍老兵,曾是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副官。在一場訓練事故中炸瞎了雙眼。退伍之后,身體的殘疾再加上對時代的不適應,使他心灰意冷,最終決定到紐約這座他所鐘愛的城市進行一次“享樂之旅”,在拜訪自己的親屬,在高檔酒店進餐,與美女共度良宵后,結束自己的生命。

斯雷特的遭遇表現出了美國嬰兒潮一代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變遷過程當中的境遇。“二戰”勝利后,美國成為了世界政治的主宰,大量歐洲富翁因躲避戰亂移民至美國,所攜帶的資金使美國經濟空前強大。對于未來的樂觀判斷使美國國民生育意愿強烈,大批兒童出生,史稱“嬰兒潮”。一般認為,嬰兒潮開始于1946年,結束于1964年前后,據估計,這一期間出生人口總數超過了七千五百萬人。嬰兒潮又可細分為早期與晚期,1946年到1955年這一階段被稱為早期嬰兒潮,人數在三千八百萬人左右。斯雷特應當屬于早期嬰兒潮一代。
從意識形態來說,早期嬰兒潮一代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叛逆精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們的少年時期經歷了戰后軍政府時代。無論是羅斯福、杜魯門還是艾森豪威爾政府都帶有濃郁的軍人政府特征。加之 “二戰”后開始的東西方對峙所引起的冷戰,美國國內政治局面非常嚴峻,50年代中后期由國會議員麥卡錫提出在美國境內進行共產主義調查,導致政治空氣緊張,保守主義盛行。這對于早期嬰兒潮一代思想影響巨大。
從20世紀60年代這一代人成年后,一股自由主義熱潮席卷了美國全境。反對保守的社會制度,強調種族、性別平等,追求個人理想自由,尋求自我人生的價值,成為這一時代的標簽,大量校園青年走上街頭,聯合起來,抗議社會保守主義。與此同時,反文化運動中也同樣反映出對美國立國的清教主義思想與道德的全面挑戰,很多青年開始反抗傳統節制欲望、努力工作的清教生活作風,追求感官享受,脫離家庭,回歸自然,性解放與神經麻醉劑濫用也成為反文化運動的標志。
在激進的社會氛圍之下,美國政治也發生了變化,軍隊領袖讓位于青年一代,約翰·肯尼迪以其年輕、熱情、富于理想主義的形象,成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青年的偶像。在總統就職演說中,他號召美國公民為了自由和國家安全,放棄黨派、地域和種族差別,共同為了全人類理想而努力。在肯尼迪的推動下,普世主義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嬰兒潮青年的心中。

此外,越南戰爭成為影響這一代人的關鍵因素。作為美國冷戰全球戰略亞洲計劃的一部分,越戰始于1955年,由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動。肯尼迪上臺后,將越戰描述為“支持伙伴,反對敵人,克服困難,以保證生存和自由”的戰爭,在任期間大規模擴大在越駐軍。肯尼迪遇刺后,繼任者林登·約翰遜延續了其越戰政策。在政府宣傳影響下,早期嬰兒潮青年將參加越戰視為追求人生理想,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參加越戰不僅能夠讓他們成為國家英雄,將美國精神傳遍全球,而且令他們能夠晉升乃至成為國家領袖,而神秘的東方又能夠滿足他們環游世界的夢想。然而,隨著越戰的進行,無論是美國本土公民還是戰場上的士兵,越來越發現這場戰爭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戰爭使大量士兵葬身異鄉,巨大人力、財力投入使得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大量越戰報道使人們越來越懷疑戰爭的正義性,很多美國公民,特別是晚期嬰兒潮公民,認為越戰“只是一場為了有錢人利益進行的戰爭”。很多人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撤軍,在公眾壓力面前,美國政府于1975年結束了越戰。
斯雷特身上清晰地體現出20世紀60年代精神與90年代美國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他沉浸于舊日的輝煌,張口閉口不離“我和林登(約翰遜)在一起的日子”,憤世嫉俗,目空一切,脾氣火爆,臟話不斷,對于所有人頤指氣使。另一方面,他耽于享樂,嗜酒如命,追求豪車美女帶來的快感。這種強硬和享樂主義態度背后掩飾的是他對現實深切的無力感,既不肯承認自己觀念過時,也無法屈尊接受他人的關愛。乖張固執的性格,加重了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隔閡。在他人眼中,斯雷特代表的20世紀60年代精神完全成為不合時宜的象征:他的侄女對他雖然崇拜有加,但更多地則是寄予同情;而他大哥比利的兒子蘭迪則代表了90年代人對反文化運動更為極端的看法。在他看來斯雷特完全是家族中的害群之馬,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和各種風流韻事是他缺乏責任心,行事荒唐的可悲注腳,而他的悲劇則因酗酒所致,咎由自取。不管怎樣,作為一名恪守20世紀60年代和越戰精神價值觀的嬰兒潮一代,斯雷特已經完全淪為社會的邊緣人。
查理:20世紀90年代美德主義下青年的成長與困惑
故事另外一個主人公查理,來自偏遠地區俄勒岡州,出身于小商販家庭,憑著學習勤奮和家庭支持,依靠獎學金來到了別爾德這所具有精英主義傳統的學校,一心希望通過優秀的成績和品德表現進入哈佛大學。一次,他無意中目睹了喬治以及其他幾個富家子弄臟校長新汽車的惡作劇。為了讓查理說出實情,校長為他提供一個免試進入哈佛大學的機會。面對誘惑,查理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應該接受校長的提議,講明事實的真相,還是應該和那些自己并不相熟的同學站在一起,堅定地捍衛伙伴之間的忠誠。
查理的困境看似是個人選擇,實際上反映出20世紀90年代整個美國社會道德觀的變化,尤其是在美德主義影響下個體對群體的責任問題。所謂美德主義,是指社會根據可操作標準,例如智商或者標準成績測試等考試,衡量個人能力,任命相應工作并給予相應地位、薪酬和待遇的方式。美德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提出以德行來管理國家的方式。資本主義興起以后,隨著宗教神權勢力減弱和封建等級制解體,人們的社會地位逐漸趨于平等,社會需要采用新方式選拔任用人才。基于各級學校教育產生的考試和測評機制,以文憑代表智力和才干的選才方式,逐漸被社會認同,成為資本主義人才制度的基本原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德主義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隨著六七十年代社會動蕩的結束,戰爭陰云逐漸散去,80年代末東歐解體冷戰結束后,戰爭時期的價值觀,包括領導力,忠誠和伙伴觀念重要性下降。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趨于專業化,對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要求越來越高,技術門檻越來越成為社會評價個人價值的關鍵因素。美德主義不僅影響到科學領域,同時也影響到社會政治,越來越多的各行業的精英與專家成為政治領袖,“技術專家政治”一詞應運而生。隨著1991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的政治精英比爾·克林頓當選,美德主義在美國社會達到了頂峰。如果說,肯尼迪的當選開啟了美國反文化運動的閘門,克林頓的當選則可以視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美德主義政治制度的發端。
美德主義制度有其自身的優越性,根據候選人的智力水平決定其社會責任和相對待遇,避免了等級、種族以及性別等方面的不平等,防止社會階層固化,給更多像查理一樣出身寒門的學子以出頭之路。然而,將美德主義作為政治和社會標準存在諸多缺陷。首先,美德主義建立在對被評者的個人判斷之上,這也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更多是競爭而非合作關系,過度強調美德,會使社會個體關注自身發展而陷入利己主義,忽視大眾和群體利益。同時,美德主義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片面追求個人在評價體系內的表現,包括成績、智力以及業績等量化數據,忽視對于人生當中一些無法進行量化的內容,包括幸福、快樂、個人尊嚴和榮譽感的追求。最后,美德主義常常導致精英主義,使優秀人才向社會最優秀資源富集,形成封閉的小群體,忽視大眾的廣泛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查理遇到的困境其實是處在精英主義體制支配下的年輕人對人生價值的困惑。對他來說,能夠進入美國最優秀的高等學校是成為精英的必由之路,因此具有無窮的吸引力,然而,他受到良知的驅使,知道自己的機會是以出賣“同伴”為前提的,違背了他自己尚不明確的生活信條。這種矛盾感在他遇到斯雷特后,變得更加尖銳起來。對查理來說,斯雷特的“享樂之旅”對他來說意味著一次“成人禮”。在查理眼中,經受過戰爭和國際政治洗禮的斯雷特身上散發出難以抗拒的勇氣、優雅和經驗的魅力,他以20世紀60年代人特有的熱忱和理想主義態度,向查理展示出個人價值判斷、尊嚴以及勇氣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查理也漸漸學會了如何像一個男人一樣,遵從自己的內心,面對眼前的困難抉擇。
斯雷特的演講與故事的結局:20世紀60年代精神對當代的啟示

毫無疑問,電影的高潮出現在結尾處,校長以及校紀律委員會對破壞校長汽車事件進行的問訊,抑或稱為審判。喬治受到富翁父親的庇護,幾乎不可能受到懲罰,查理因此成為唯一受到校長盤問的對象。查理通過與斯雷特共度幾日,深深受到后者人格魅力的影響,雖然并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還是決定像個男人那樣,堅持自己的立場。校長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又不能追究其他搗亂分子,決定開除查理。陪同前來的斯雷特看到查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忍耐不住,發表了令全場震撼的講演。
斯雷特中校的講演除去那種懾人的氣勢以及華麗的修辭外,真正打動人心的是其中深刻的內容。首先,他怒斥校長處事不公,趨炎附勢,只會依仗權力,欺凌弱小。然后,將矛頭轉向了學校的傳統,說別爾德高中所謂的傳統已經死亡,培養領袖的搖籃已經落下。緊接著,他沉痛地警示在場師生,查理擁有正直而純潔的靈魂,決不會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出賣別人。最后,他深刻地指出,查理正走在一條正確然而艱難的道路上,他來到了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選擇,他號召紀律委員會的人應當成全他繼續走下去,這是一條光明之路,所有人將會為他的未來而驕傲。
這段講話不啻于對當代美德主義諸多弊端的一篇檄文,無論是失落的傳統還是已經落下的搖籃,都可以視為被背棄的肯尼迪式美國精神。那種愿意保護同伴,為自己行為負責任的團結精神,越來越多地被明哲保身,甚至以出賣伙伴的方式獲得榮身之路的精致利己主義所替代;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查理堅持自己理想,勇于承擔責任的做法,自然成為被人孤立乃至排擠的少數派精神。查理人生的抉擇,同樣也代表了整個一代受到美德主義時代精神驅使的美國青年的抉擇。此刻的斯雷特宛然化身為特洛伊預言家拉奧孔,即便被巨蛇殺死,也要向所有人發出不要相信希臘人木馬的災難警示。他冷眼審視著這個被物質和專業化奪去激情與勇氣的世界,雖然遭受社會的排斥,但依然能夠受到良知的驅使,發出天鵝之音。

幸運的是,影片給了整個事件安排了一個光明的結局。斯雷特的講演在在場的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回應,校長和校監會最終做出決定,不再追究查理的責任。影片安排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校監會成員之一,美麗的唐斯女士,受到斯雷特中校演講的感動,主動上前與斯雷特聯系,表現出對斯雷特的好感。唐斯的外表樸素大方,那蘇格蘭花呢外套和蓬松的棕色長發,明顯帶有20世紀70年代回歸自然服飾風格的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雷特敏銳地聞到她用了一款名為“石園之花”的香水,這款香水始創于1934年,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非常流行。從這些細節中觀眾可以看到,60年代價值觀在嬰兒潮一代中并未逝去,而在新一代青年當中依舊激起新的共鳴,斯雷特并未獨行。
結論
行文至此,本片在美國觀眾當中引起爭議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爭議的核心在于20世紀60年代精神在當今美國社會是否還有價值。客觀地說,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發展,民主制度高度普及、專業主義高度發達,美德主義價值觀以及其導致的精英主義制度成為社會支配力量。人們在高度理性的指引下,很難再次重現60年代那種充滿變革、激情、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社會風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六十年代精神在美國社會徹底消失。進入21世紀以來,明顯可以看到,以奧巴馬為代表的高學歷、高智商的精英主義政府,雖然表現出超人的智慧、修養和理性,但民眾質疑之聲不斷,其漸漸成為虛偽和偽善的代名詞。而在最近結束的大選中,特朗普表現出的直言不諱乃至有些不拘小節的性格卻大受歡迎,依稀讓我們感覺到斯雷特中校的影子。也許,在美德/精英主義把持美國社會二十年后,又有可能看到激情和熱血在美國社會再次回潮?《聞香識女人》的片名給我們一種有趣的暗示,如果把美德主義視為人類所仰仗的視覺,用來建立有章可循的理性秩序,那么理想主義和激情不妨可以比作嗅覺,雖然難以名狀,但是那一縷馨香,始終縈繞于你我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