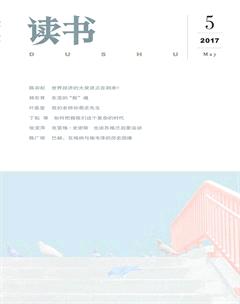帝國的制度遺產
霍曉立
“聯邦制是我國的專利。制憲者將‘主權的單一原子一分為二,我國公民由此具備了州與聯邦的雙重權能,兩者均免受對方的侵擾。這是制憲者的天才創造。我國憲法創立了一種在形式和設計上史無前例的政治體制。它建立了兩套政府機構,兩者都同創造、維持它們并受它們統治的人民各自發生直接的關聯,各自相互知悉并保持默契,各自產生相互的權利與義務關系。”[U.S. Term Limits, Inc. v. Thornton, 514 U.S. 779, 838(1995)(Kennedy, J., concurring)]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的上述見解是美國法律人關于聯邦制起源的經典論述,即聯邦制是一種全新的創造物,它是制憲者們在美利堅國族“創世紀”的制憲會議上“頭腦風暴”的成果。然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憲法學教授艾莉森·拉克羅斯(Alison LaCroix)的《美國聯邦制的意識形態起源》(下稱《起源》,下引此書只標注頁碼)一書卻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
拉克羅斯將聯邦制的起源上溯到制憲會議前的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英國和法國為了爭奪在歐洲和美洲的霸權地位,在北美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七年戰爭”。在北美殖民者的支持下,英國最終打敗了法國及其盟友西班牙,但它自己也由此債臺高筑。為了償還戰爭債務和支付北美駐軍的軍費,英國議會先后通過了一系列對北美殖民地征稅的法案,這引起殖民者的普遍不滿。從一七六四到一七七四年,帝國官員和北美殖民者先后圍繞英國議會對殖民地的立法權和英帝國的主權歸屬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辯論。
一方面,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之前,英國王室和議會并不重視對北美殖民地的經營。長期以來,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名義上的和表面化的。英國王室和議會一般僅限于管理北美的大西洋貿易和航運等外部事務,而很少參與殖民地的內部治理。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的“印花稅危機”中,殖民者據此主張英國議會有權管理航運、貿易等帝國事務,但無權插手征稅、立法等殖民地事務。有些更為溫和的殖民者還細分了內部稅和外部稅、以汲取財政為目的的稅收和以管理帝國貿易為目的的稅收,以此作為劃分殖民地議會和英國議會立法權的標準。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在關于英帝國主權歸屬的爭論中,殖民者甚至指出北美各殖民地是通過英國王室頒發的特許狀或憲章而建立起來的,它們與英國議會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法律關系。北美各殖民地和英國本土一樣都是獨立的“國家”,它們之間通過共同的國王聯結成為一個帝國。因此,殖民地議會和英國議會是相互獨立和平等的。
另一方面,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之后,議會主權逐漸成為英國政制理論的核心信條:議會享有至上的、絕對的、不受限制的和不可分割的主權,因為不同層級的政府不可能共享或分割同一政治空間,“主權內的主權”于文理不通(14頁)。因此,帝國官員認為,如果殖民者肯定議會可在某些情況下對其行使權力,那么他們就不得不承認其受制于議會的主權權威。
北美殖民者與帝國官員針鋒相對,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就是主權是否可分。盡管殖民者內部對此問題的具體主張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認同這樣一種主權理論:兩級政府并存于英帝國內部,兩者以其所管轄事務的性質為界,分別享有相應的立法權限。由于兩級政府分享各自的政治空間,這種可分割的主權理論也就不會陷入“主權內的主權”的困境。拉克羅斯認為,北美殖民者的可分割的主權理論是對傳統的單一主權理論的革命性變革,至此“可分割的主權既不再是文理不通的謬論,也不再是偶然性的實踐,而成為一種根本性的政治原則”(101頁)。在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辯論中形成的可分割的主權理論正是聯邦制意識形態的主要思想來源。
在拉克羅斯的論述中,一七六四至一七七四年的政治辯論是聯邦制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一七八七年的制憲會議則是其中的第二個階段。前者提出了兩級政府的立法權力按照其管轄事務性質劃分的理論設想,而后者提供了兩級政府的立法權力在實際運作中重疊或沖突的解決方案。也即,一七八七年憲法將可分割的主權理論予以具體化和制度化了,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聯邦法院依據“至上條款”審查州法的司法審查制度。
北美獨立之后,基本的政治秩序并未隨之建立起來。由于邦聯國會無權、無錢和軟弱,各邦不聽號令、各自為政并相互攻訐。制憲會議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合理劃分兩級政府的權限,授予聯邦政府更充分的立法權力和協調兩級政府權力沖突的權威。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起草的《弗吉尼亞方案》是制憲會議討論的藍本,其中第六條規定:“聯邦國會有權基于其判斷,否決各州議會制定的違反本憲法的一切法律。”然而,麥迪遜提出的聯邦國會否決權方案最終未能寫入憲法。但緊隨其后,制憲會議通過了《新澤西方案》所提議的一項條款,即聯邦國會制定的一切法律與其簽訂的一切條約“在效力上高于各州立法”,各級法院得遵守上述“最高法律”。這就是憲法第六條中的“至上條款”的最初版本。拉克羅斯認為,由聯邦法院實施“至上條款”以協調兩級政府的權力沖突,在功能上是聯邦國會否決權的替代機制。
但是,這兩種方案之間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聯邦國會否決權隱含著“兩級政府權力的混淆”。聯邦國會審查州法,就是將其權力的觸角伸向州議會管轄的事務或領域,這也就不存在立法主權的分割了。與此相反,聯邦法院實施“至上條款”卻仍將恪守主權分割原則。“本憲法和依本憲法所制定的合眾國法律,以及根據合眾國的權力已締結或將締結的一切條約,都是全國的最高法律。”因此,聯邦法院受制于憲法的聯邦權力列舉原則,這是其憲法義務。本質上,憲法至上取代了聯邦至上。至此,美國聯邦制的意識形態最終形成:“兩級政府并存和立法主權分割是理論原則;權力重疊與沖突是實踐常態;管轄事務的性質是劃分兩級政府權限的最終判準。”(7頁)
美國法律人習慣于將聯邦制的起源聚焦在一七八七年的制憲會議上,而拉克羅斯則將其放置于拓展的時間框架內。但她并非將聯邦制的起源上溯到一七八七年之前的年代或世紀的第一人。在此之前,美國歷史學界已有相關制度史或思想史研究。其中制度學派關注十七、十八世紀英帝國多層級政制結構,并主張其與美國聯邦制之間存在連續性。共和主義學派則關注十八世紀后半期思想轉型,并將聯邦制視為共和主義觀念在政制結構問題上適用的結果。拉克羅斯曾在該學派大本營哈佛大學歷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起源》一書即由其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此書無疑打上了意識形態研究的印記,但她試圖將分割主權觀念作為分析的核心,以恢復“聯邦制思想本身的獨立性和特殊性”(5頁)。然而,拉克羅斯關于聯邦制起源的研究卻遭遇了共和主義學派旗手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的質疑。伍德在為《起源》寫作的長篇書評《自下而上的聯邦制》(Federalism From the Bottom Up)中,首次詳細闡述了“共和主義路徑”在聯邦制起源問題上的見解,并從內容上和研究方法上對拉克羅斯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伍德指出,聯邦制意識形態的主要來源是北美殖民地內部的鄉鎮自治實踐,以及由此生發出的人民主權觀念,而非英帝國對殖民地“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殖民地對英國議會權威“自下而上”的反制所引發的政治辯論,以及由此形成的可分割的主權理論(伍德,728頁)。北美殖民者繼承了“英格蘭長期的地方自治傳統”,他們直接或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間接地參與鄉鎮和殖民地的日常管理,這種長期的實踐經驗還養成了殖民者“從未授權人民選舉的代表享有人民的完全權威”的觀念(伍德,728頁)。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北美殖民者以“事實/真實代表制”激烈地反對帝國官員所主張的“實質/虛擬代表制”。因此,他們與帝國官員爭論的焦點不是主權是否可分的問題,而是英國議會與殖民地議會何者代表他們的問題。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人民取代英國議會成為北美殖民地的主權者,而聯邦制就是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在作為其代表的兩級政府之間分配權力的結果。由此可見,伍德采用的是北美殖民地鄉鎮自治和人民主權觀念的下層視角,而拉克羅斯用的則是殖民地與英帝國政制結構的上層視角。聯邦制意識形態是復雜的,其思想來源也是多樣的。二人的觀點并無對錯高下之分,有的只是視角的差異。
伍德對《起源》的研究方法的批評也許更值得玩味。在他看來,雖然拉克羅斯認識到聯邦制思想與十七、十八世紀多層級政府的制度實踐之間的內在關聯,但是她只是將這種制度實踐作為聯邦制意識形態起源的背景或“史前史”。《起源》的時間框架是從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危機”開始的。不論英帝國的分權政制還是殖民地的地方自治,都是外在于《起源》的歷史敘事的,因為它僅僅關注“表達制度實踐的思想觀念”(5頁)。然而,十七、十八世紀的“早期殖民者在行動中實踐著聯邦制,即使它沒有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證成”(伍德,708頁)。因此,在伍德的論述中,“自下而上的聯邦制”開始于十七世紀初期的鄉鎮自治。也就是說,即使英帝國的分權政制或殖民地的地方自治沒有思想觀念形式的自我表達,歷史學者也可以從制度實踐中發現其“實踐邏輯”。
但問題在于,英帝國的政制結構是否也實踐著聯邦制的“實踐邏輯”呢?伍德因為研究視角的差異,拉克羅斯則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都沒有論及這個問題。而且,《起源》為了凸顯聯邦制意識形態相較于單一主權理論的革命性,避而不談英帝國的制度實踐。也就是說,它不關心單一主權理論“在客觀上是否正確”(5頁),即它是否符合英帝國政制的“實踐邏輯”。與此相反,伍德卻營造出了“殖民者實踐著的分權政制與英國單一主權觀念之間的背離與對立”。
有趣的是,拉克羅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那種認為英帝國的政制結構是聯邦制的觀點毫無根據。北美殖民者確實生活在多層級的政府結構中,……關系到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立法都來自鄉鎮或殖民地議會,而非英國議會或樞密院。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上述這些地方性權力始終是在英帝國權威的陰影之下運作的。所有調整殖民地農夫之間交往的立法或者解決商人之間爭議的裁決,都有可能被英國議會廢止或被樞密院否決掉。……(因此,可分割的主權理論)只是可爭辯的和充滿雄心的論點,而并不一定是對英帝國政制結構的真實描述。”
這段似是而非的論述似乎陷入了不可知論,但是它卻表明了拉克羅斯在英帝國的政制結構與聯邦制之間的關系問題上的看法,即英帝國的政制結構既實踐著單一主權的“實踐邏輯”,也實踐著分割主權的“實踐邏輯”。究其原因,英國本土的議會主權觀念與北美殖民地的分割主權觀念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的碰撞,源于英帝國政制結構本身所內存的這兩套相互沖突的“實踐邏輯”。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之后,英國新興的強調中央集權的國家觀是與傳統的強調多中心治理的帝國觀相悖的。當英國本土的議會主權觀念漂洋過海來到北美殖民地,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癥候。其根源就在于,英國的國家建構與帝國建構在十八世紀英帝國的時空結構中同時發生,兩種“實踐邏輯”的沖突不可避免。
(Alison LaCroix,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Fed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