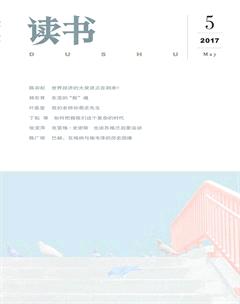政治的文化解釋
胡鵬
在中國,官員有時被稱為父母官,而西方人通常稱之為政客,不少西方人常常對政客進行調侃和嘲笑,許多中國人則對官員十分尊敬和期待。對于同一公共政策,同一家庭的成員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這些現象的背后都閃現著文化的影子。在政治生活中,文化時常出現。一九九三年的 《曼谷宣言》 提出了著名的“亞洲價值觀”,此后被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進一步宣傳和推廣。“亞洲價值觀”的提倡者認為亞洲地區持有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如重視家庭、尊重權威、決策中強調共識、社會群體高于個人等,由此產生了與之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安排。文化也很早就引起了學者的注意,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就是一個典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實證主義政治文化研究興起,產生了如《公民文化》《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化與后現代化》等諸多經典著作,與此同時,跨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態度調查也開始出現,其中包括涵蓋全球大部分國家的世界價值觀調查、全球晴雨表調查。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主流的政治學期刊已越來越難看到以政治文化為主題的文章,相關的學術專著也越來越少,新一代的研究者轉而分析政治態度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政治文化”一詞越來越少地被提及。學者戴維·萊廷(David Laitin)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尖銳地指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沒有為后來者開辟更為廣闊的空間,相反,政治文化研究越來越走下坡路,逐漸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邊緣領域。在政治文化研究低迷之際,長期研究中國民眾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學者史天健(Tianjian Shi)跳出國別研究的舊有路徑,在二○一五年出版的遺著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以下簡稱“史著”)中,提出了一個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為本領域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政治文化的兩種分析視角
生活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與文化相關的詞:文明、文化、道德、價值觀、符號、態度、觀念、觀點。政治文化的定義一直是本領域的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其中大致有兩種視角:實證主義視角和解析主義視角。實證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人的內心態度的分布。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和維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一書中將政治文化定義為“人對政治現象的心理評價”,而一國的政治文化則是該國所有成員對政治現象的評價的類型及分布。將政治文化界定為民眾內心的態度為實證測量政治文化提供了認識論上的基礎,研究者因而可以采用跨國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一國受訪者的政治態度,并通過分析特定政治態度的分布推斷一國的政治文化類型。與之不同,解析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反對將文化視為個人的心理認知和評價,在這些研究者看來,文化為人的行為提供意義,具有集體和公共性。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提出:文化是表演的文件,它提供的意義是公共的,并不存在于人的頭腦中。格爾茲把文化定義為純粹的符號系統,他的經典說法是:“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而文化就是這些網。”解析主義的文化研究者主張將政治文化的分析聚焦在社會話語流上,同時通過關注政治行為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形態。
在史著中,史天健試圖綜合實證主義者和解析主義者的看法。在對文化的認識上,他呼應解析主義研究者的觀點,即文化賦予社會行為以意義。他指出:文化約束乃至決定行為者對自身利益的界定,而不簡單地增加或減少某些行為的成本或收益,不應被看成另一種類型的政治資源。將政治文化定義為個人對政治現象的態度的類型和分布,一方面忽視了文化的公共屬性,尤其是外在的文化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無視政治文化與其他領域文化之間的內在共通性。史天健主張采納解析主義的文化認識論,但在文化分析的方法論上,他又與實證主義者站在了一起。他不贊同通過分析人的行為來解析文化規范,因為人的行動與其表達的意義并不相同,行為的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并不能賦予行動(Actions)以意義,只有行為模式背后的文化才能賦予行動以意義。作者也不認同通過深描和解析來分析文化,在他看來,一個政治文化的操作化定義依然是可得的,研究者進而可以進行測量和比較,并發掘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書中,政治文化被定義為“一系列的規范組合(a body of norms),它規定一群人行為的準則,并將該人群與其他人群顯著區分開來”。
史天健綜合解析主義的文化認識論和實證主義的文化分析方法論,試圖溝通兩派,將解析主義視角對文化的認識納入實證主義研究的框架中來。但應該看到,兩者存在很強的張力:解析主義視角強調文化的集體性,注重情境、文本和話語,在這些研究者的眼中,文化研究是探索意義的闡釋性學科,不存在一般規律;而實證主義方法論強調簡潔性、有清晰的測量、有明確的因果鏈條,目的在于發現規律。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張力的普遍存在,最為突出的是解析主義的文化認識論與實證主義的問卷調查方法互不匹配。遵循解析主義對文化的認識,文化研究的中心工作是分析這個社會存在哪些社會規范,以及這些社會規范之間的關系如何。解析主義視角強調,在研究一個社會的文化規范時,不能帶著自己的先驗認識進去,需要研究者深入到這個文化情境中去體會,然后通過“深描”(格爾茲語)勾勒出來,民族志和話語分析是常用的方法。相比,問卷調查則不甚合適:首先,問卷設計發生在調查之前,問題和選項的設計往往反映的是調查者,而非被調查者的文化價值觀,削足適履的狀況常常出現。其次,問卷調查的時間太短,調查的執行者只是在向受訪人詢問標準化的問題,無法關注和體會當地的文化環境、符號和行為。在解析主義視角看來,文化符號、儀式和社會行為等非個人態度層面的東西,才應是文化研究關注的核心內容。最后,雖然作者反復強調文化不等于個人態度,但在實證部分,他依然走的是沿著態度去反推規范的存在,然后由規范去反推文化傳統的路子,這依舊走向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影響表現在民眾的政治態度上,而不是解析主義視角強調的集體層面的東西,如是否存在符合儒家文化傳統的儀式、符號、行為等。
緊接著,一個社會存在多少規范,不同社會中的規范是否可以對比,本身就值得深入分析。但在本書中,作者先驗性地認為中西方存在顯著的政治文化對比,同時把孔孟儒家學說與西方社會契約論學說看成東西方政治文化的代表,背后的假定是中西方內部的政治文化規范差異較小,這無疑值得商榷。如中國除了有孔孟儒家學說傳統,還有社會主義學說、自由主義思想等,幾者并不能等同,裴宜理、唐文方等學者的作品都展示了這點。作者也沒有通過經驗證據展示:持集體主義利益觀和等級權威觀的民眾在現實中真正受到儒家傳統的影響。進一步,即使是單一文化傳統,如儒家思想,其內部也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學派推崇不同的典籍、版本和觀點,對同一現象往往也會有不同的判斷,提出不一樣的規范。將幾本典籍或一兩位思想家的話語當成是整個儒家學說的代表,可能忽略了該文化傳統內部的復雜性。實際上,對于一個社會而言,不同文化規范的存在是正常現象,值得分析的是:這些文化規范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又對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造成了什么影響。
政治文化與個體行為
為什么政治文化分析要關注規范(Norm)?史天健認為:政治文化從表面到深層,由態度和看法、規范、價值三個層級的內容組成。價值和規范關涉正確與否,而態度和看法則是對具體人物和現象的看法。價值和規范更為深層、更有持久性,態度和信念則更為表面、更易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態度和信念的出現受價值和規范以及人與對象的互動的影響。如人應該尊重父母,這是一個規范,而現實中人對父母的態度,則受到這個人所處的規范以及個人與其父母之間實際相處互動的影響。作者進一步認為:政治文化分析應該集中于規范而非價值,理由是價值屈指可數,而且規定的是一般性的理想結果,它們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中引發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行為后果。愛國主義在他看來就是一個典型,因此價值與行為之間往往難以建立直接關系。與之相對,規范更為具體,允許或禁止個人在特定的環境中做出特定的行為。作者對態度和信念與價值和規范進行了精彩的區分,但在價值和規范的關系上,其論述卻很難讓人信服。且不說愛國主義是不是價值觀尚值得討論,愛國主義作為價值觀在不同的環境中引發了不同的后果,并非由于其本身沒有明確的行為導向,而是源自愛國主義與其他價值的結合。如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結合,會引發一種行為導向,與其他價值結合,又會引發另一種行為導向。實際上,規范與價值的區別并沒有作者說的那么大,所有的文化規范都是一定價值的具體體現,有著清晰內涵的價值都有著清晰的行為導向。以作者強調的利益觀和權威觀為例,個人為中心的利益觀和契約式的權威觀的背后更多的是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而集體主義的利益觀和等級式的權威觀的背后更多的是服從和秩序的價值。
在諸多文化規范中,作者認為核心的是兩點:一是對自我利益的界定,大致可分為兩類—以“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觀”和“以集體為中心的利益觀”;二是權威觀,即如何看待個人與國家權威之間的關系,也有兩類—“契約式的權威觀”和“等級式的權威觀”。不同的利益觀和權威觀會影響乃至決定個人對政治現象的判斷和看法。如對于政府興建公共工程,“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觀”的持有者往往關注公共工程建設過程中是否全面保障了個人的利益,同時質疑工程的興建是否為官員的自身利益服務;而“以集體為中心的利益觀”的持有者則更看重公共工程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益處;“契約式的權威觀”持有者會追問公共工程是否經過了民眾或民意機構的同意,整個過程是否符合法律和程序;而“等級式的權威觀”的持有者則更傾向于尊重并信任政府的決策。作者同時指出,文化規范在兩個層次上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一是個體層次(Individual Level),一個人內心中的規范取向影響自身的行為,違反心中的規范會引發心理內疚或負罪感,作者稱為“內在的規訓系統”(Internal Policing System);另一個是集體層次,文化規范決定他人和社會對個人行為的評價,遵守者受獎勵或平安無事,違反者則遭人非議乃至受到懲罰,這被稱為“外在的規訓系統”(External Policing System)。內在的自律和外部的約束會相互影響、相互強化。我們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這種狀況,如小說《白鹿原》里的族長白嘉軒推行鄉約,他帶領族人在祠堂背誦鄉約,希望這些規范深入人心,指導并約束族人的行為,對于違反鄉約的兒子白孝文當眾鞭打,予以懲戒。但現實經驗也提醒我們:個人對文化規范的變遷同樣有顯著影響。理性、反思、批判精神的存在,以及個人與現實政治、社會的互動能改變人的態度乃至價值觀,進而使一部分人脫離既有文化規范的束縛和影響,乃至成為新的文化規范的創造者。從源頭上看,文化規范的創立本身就源自一些偉大思想家的個人創作,儒家學說即源自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貢獻。回到《白鹿原》的例子,《白鹿原》的人物并沒有完全沿著族長白嘉軒設定的規范生活,黑娃挑戰了傳統的婚姻制度,而陸兆鵬則加入了共產黨,最終把革命帶到了白鹿原。過度強調文化傳統的延續性和結構性影響會使我們難以解釋文化規范的變遷。文化的變化雖然緩慢,但在人類社會中時常發生,需要文化研究者認真對待,而一個個體與文化規范的互動分析框架也許能推動我們更好地理解文化的變遷。
政治文化與制度
討論政治文化,不能不將政治制度一并帶入。為了解決制度與文化“雞生蛋、蛋生雞”的難題,史天健采取了兩步走的策略:首先將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狀況分割開來,論證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在證明文化規范并不會隨著制度、經濟增長等物質現象的變化而顯著變化后,接著探究它如何影響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雖然面板調查數據不存在,但他認為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提供了一對理想的比較案例:兩岸有著相同的儒家文化傳統,但雙方的政治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別很大。
通過兩組共計六個問卷問題,作者分析兩岸民眾對自身利益的認定和對權威的態度,他的結論是雖然兩岸分治了六十多年,但兩岸民眾在利益觀和權威觀的認識上依然十分相近。具體來看:大部分兩岸民眾將集體利益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同時傾向于服從權威,而且這些偏好并沒有因時間變化發生太大改變。作者認為:在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迥異的情況下,兩岸民眾仍持類似的文化規范取向,這證明文化獨立于制度、經濟增長等物質條件。而文化獨立于政治制度、經濟社會狀況的原因在于文化規范本身具有黏性,態度和信念易受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但深層次的規范則更為穩固和富有彈性。人對某個規范的認同越深,就越難以改變。當外在的環境和規范系統發生改變時,人往往不會改變自己內心中的規范取向,而會責怪外在環境的變化,并主張回歸到舊有的規范系統,作者將其稱為“文化反沖假說”(Cultural Backlash Hypothesis)。作者進一步提出:規范的習得與人的社會化程度密切相關,其中教育的影響尤其巨大。教育程度的提高雖然增強了人的認知能力和獲取信息的能力,但同時也使人更長時間、更深地受到已有文化規范的影響,作者認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反而越有可能成為原有規范系統的守護者。在后續的章節中,作者探討文化規范對人的政治信任、政治參與和對民主的理解的影響。他發現:與持“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觀”和“契約式的權威觀”的民眾相比,持“以集體為中心的利益觀”和“等級式的權威觀”的民眾更容易信任政府,尤其是相信政府的意圖;同時這些民眾眼中的民主并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而更接近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作者稱為“衛護型民主”(Guardianship Democracy)思想,即民主并不體現在一定的政治程序之中,如選舉,而體現于實質的結果上,如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在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下,中國大陸當下的政體保持強有力的韌性。
史天健富有沖擊性的觀點挑戰了流行的現代化邏輯,并主張文化規范顯著影響政治行為乃至政治制度。但仔細推敲其邏輯和經驗證據,可以發現不少地方都值得商榷。首先,教育使得人們更深地受已有文化規范的影響,這個因果關系的前提是某一種文化規范在教育中占據主導地位,具體而言,即是儒家傳統思想在兩岸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兩岸的教育系統都在傳播儒家傳統思想,這無疑與現實不相符;接著,教育的背后是政治,政治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決定了教育的內容,如大陸學生需要上公共政治課。作者強調教育對文化規范延續的顯著作用,無疑會引發制度主義者的質疑,即一定的政治制度決定了教育的內容,再影響了文化規范的延續。如果這個邏輯可靠,那作者試圖論證的文化獨立地位就可能大打折扣了。進一步,書中對數據的處理和解讀也值得進一步討論。作者認為兩岸民眾在利益觀和權威觀方面的認識差距不大,但細看兩岸民眾在這六個問題上的回答,可以發現臺灣民眾接受“以集體為中心的利益觀”和“等級式的權威觀”的比例均低于大陸民眾,六個問題平均下來要低10%左右,直觀而言,兩地民眾文化規范認同相近的結論恐怕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一個與之相對的競爭性解釋是:兩岸本身的文化傳統差異并不大,但是由于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兩岸的文化差異逐步拉大,雖然至今依然有相似之處,但相似性已經在降低。最后,如上述指出的那樣,作者先天假定儒家思想對當今兩岸社會有顯著影響,沒有考察兩岸社會中到底存在多少種文化規范,因此在從個體態度推導到文化規范的影響時就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數據分析顯示:“以集體為中心的利益觀”讓人更加政治消極,“等級式的權威觀”則出人意料地讓人更加政治積極。作者的解釋是因為在等級式權威觀的人的眼中,政府擔負著為民眾排憂解難的責任,而即使是在政治抗爭中,參與者的目標也是“勸諫式”(Acts of Remonstration)的,目的是提醒政府自身承擔的責任,而非更迭政府。這個解釋與作者自身定義的“等級式的權威觀”相沖突,在這種權威觀下,民眾應該更加相信并支持政府,抗爭性的政治參與并不受鼓勵。相比,學者唐文方強調的社會主義傳統,尤其是群眾路線的影響,解釋力可能更強。在對有關民主含義的回答的處理上也有類似的問題,“政府允許民眾表達自己的意見”“政府考慮民眾的利益和訴求”等回答很難被認為源自民本思想的影響,因為這樣的回答在非洲的調查結果中也普遍存在,同時,受訪人對民主的理解可能是多向度的,如既要求民主有好的程序,也要求其有好的結果。
通過把規范性價值帶入實證主義的政治文化研究,史著在何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與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的關系上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這體現了作者對政治文化的長期關注和推進本領域研究的努力。本書啟發我們從文化的角度解釋政治制度和政治現象,如分析一國的政治轉型和發展,不僅要看精英層面以及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因素,也需分析影響民眾的政治態度和相應的政治行為。比較政治文化研究,不能想當然地設計一套全球通用的調查問卷,用來測量不同文化規范下民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而應首先了解當地文化規范的種類和內涵,然后因地制宜地進行測量和分析。作者綜合解析主義文化認識論和實證主義文化研究方法論的嘗試固然可貴,但如上討論的那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這些商榷的目的在于刺激大家進一步思考并探索這些問題:儒家文化在今天是否還有顯著的影響?它的影響體現在什么地方?“亞洲價值”真的存在嗎?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能厘清嗎?政治文化研究尚有廣闊的空間。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