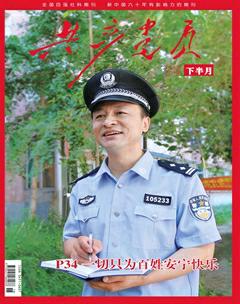老紅軍張泉:每道傷疤都講述著一個故事
張泉,1920年出生,1931年加入紅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曾服役于紅四軍、新四軍、華中抗日大學、黑龍江省軍區、解放軍169師、東北軍區撫順兵役局,后任撫順礦務局機關處長。離休前系撫順礦務局機關處長。
童年時,他是村里的兒童團團長,手拿銅盆藏在樹上站崗放哨,為紅軍傳遞情報;少年時,他參加了紅軍,是調皮的“紅小鬼”,過草地時曾因過于疲憊,在行軍路上睡著了,三個戰士輪流背他追趕部隊;青年時,他是指揮若定的軍事主官,洞房花燭夜跨上戰馬奔赴前線打仗;人到老年,他成為“故事王”,為年輕人還原真實的長征。戰爭年代14處受傷的身軀上,每道傷疤背后都有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今年96歲高齡的張泉,他的一生都在長征……
敲銅盆為紅軍傳遞情報
1920年,張泉出生在安徽省,自小體格健壯。10多歲時,張泉組織30多個同齡孩子組成了兒童團,張泉任團長。
有一次,一個紅軍團在村里住下了。為提防敵人突然襲擊,張泉帶領的兒童團主動承擔起放哨的任務。他安排兒童團團員沿著出村的山路散開,每人拿著一個銅盆和一個木槌爬上樹頂。張老回憶說:“站得高看得遠啊!兒童團能第一時間發現敵情。”
傳遞情報,兒童團有自己的暗號。“發現三四十個敵人敲一下銅盆,發現四五十個以上敲兩下,發現七八十個以上敲三下。村外一里地以內,樹上全都有兒童團團員,一個接著一個往回傳消息。”
有一次,敵人的車輛朝村口開過來。有規律的敲盆聲從第一棵樹傳到第二棵樹,再傳到第三棵樹……沒等敵人進村,收到情報的紅軍已經在村口埋伏好,將敵人一網打盡。
1930年年末,紅軍一個師駐扎在張泉所在的村子。元旦那天,在張泉家中,李自亮師長跟張泉開玩笑說:“你們跟我走吧,什么時候再打到你們村,你再回來。”見張泉似懂非懂地點頭,李師長又故意說:“算了,不帶你們了,帶著你們還得派人保護。”
一聽這話,張泉趕緊站了起來:“我要報名,我要當紅軍!”聽說張泉報名參加了紅軍,30多名兒童團員也都報了名。“小鬼,你們記住,你們是1931年的陽歷年,也就是1月1日當的紅軍。”李師長挨個兒摸著他們的頭,鄭重地說。
“記住了,我們是紅軍!”張泉握緊拳頭,喊了出來。這句話,像一句口號,也像一句誓言,至今回響在張泉的耳邊。
長征路上險些掉隊
當了“紅小鬼”,日子卻不像想象的那樣風光。張老回憶說,由于年紀小,吃不了苦,自己沒少給部隊制造麻煩。
長征途中,部隊常常要日夜兼程,才十四五歲的張泉體力吃不消。有一次,連續趕了三天路后,晚上還要跑步前進,張泉累得挪不動腿,兩個眼皮直打架。“那時候年紀小啊,就盼著自己摔一跤,這樣就可以趴下睡一覺了。”想著想著,他眼皮一沉,竟然真的趴在地上睡著了……
等張泉醒來時,大部隊已不見了蹤影,只有排長和3個戰士站在自己面前,嘴里還喊著“小鬼”。怒氣沖沖的排長說道:“你這個小鬼,怎么能半路睡著掉隊呢?知不知道你把首長嚇壞了!”
原來,當時的“紅小鬼”張泉是首長的勤務員。平日里,首長一聲招呼,機靈的張泉就會遞上水壺。可這次,正在趕路的首長連喊好幾聲“小鬼,給我拿水來”也沒人回應,首長這才發現張泉不見了,趕緊命令同行的排長回去找。
排長帶著3個戰士原路返回,邊走邊喊“小鬼”,不知走了多遠,聽到喊聲的張泉才從睡夢中醒來。“排長說:‘小鬼你怎么能半路睡著掉隊,你把首長嚇壞了!我說:‘我不是睡著了,我是摔倒趴下了。”對于張泉的“狡辯”,排長又好氣又好笑,吩咐3個戰士輪流背他趕路,這才追上了大部隊。
長征途中時常餓肚子
正在長身體的“小鬼”,飯量自然大,再加上每天都在趕路,肚子常常餓得咕咕叫。但在荒無人煙的草地上,能吃的東西實在有限,紅軍平時只能碰上什么吃什么。“春天、夏天就拔野菜、捋樹葉,到了冬天連野菜也沒了,有時候一天也見不到一口吃的。”
每當遇到田地的時候,看著田地里的莊稼、蔬菜,張泉常常饞得直流口水。但是張泉明白,紅軍是紀律嚴明的隊伍,絕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有一次,走到一片地瓜地前,張泉拔不動腿了。首長看出了他的心思,對他說:“想吃就去挖吧,記得把錢放在地里。”“后來老百姓有經驗了,看見紅軍經過,就去地里找錢。”張老回憶說。
艱苦的環境中,香甜的窩頭、饅頭都成了奢望,“別說吃了,連看都看不到”,生茄子、野菜、榆錢都成了可口的飯菜。嫩綠的榆錢用開水煮了,或者烀熟,就能填飽肚子,可老榆錢卻苦澀得難以下咽。“吃不上飯的時候,老榆錢用手搓一下就吃了,實在是餓急眼了。”
洞房花燭之夜上馬出征
張老家的客廳里掛著一幅婚紗照:年輕英俊的新郎表情堅毅,溫文爾雅的新娘輕輕依偎在新郎身邊,潔白的婚紗美麗素雅。照片里這對年輕的夫妻就是年輕時的張老和老伴,而這張珍貴的婚紗照是10多年前兒女找人用電腦技術合成的。
1949年,張泉經人介紹,認識了當時身為文藝兵的老伴。兩人結婚那天,年輕的戰士圍在新房里鬧起了洞房,可正在這時,情報員一聲響亮的“報告首長”讓熱鬧的人群安靜了下來。“報告首長,前方來電話了,說發現敵情,您看怎么辦?”
“告訴前方,我一個小時之內肯定趕到支援!”話音未落,張泉已跨上戰馬奔赴前方,一去就是一個多月。等戰斗勝利結束,張泉回到家中,一推門,坐在床上的媳婦頓時大聲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她是氣的還是嚇的,她說她以為我回不來了。”
戰場上失去了4根手指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來的。”摸著頭上、臉上、胳膊上、腿上深淺不一的傷疤,還有缺失了4根手指的左手,張老緩緩地回憶著。
“左臉上這個洞是一顆炸彈爆炸時彈片崩的,頭上這個傷是子彈打的,胳膊上這幾處都是彈片擦傷的。”張老挽起袖子,挨個數著傷疤,每道傷疤都在講述著一個驚心動魄、死里逃生的故事。
戰爭年代,張泉全身14處受傷,其中5處在左胳膊上。張老說,臥倒的時候,左胳膊在最前面作支撐并保護著頭部,所以往往首當其沖。戰爭年代,戰士受傷似乎像發燒感冒一樣成了尋常事,幾處較淺的傷口,張老已經不記得是怎么留下的了。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左手上的傷。一場戰斗中,沖在最前方的張泉遭到敵人瘋狂掃射,左手不幸被機關槍打中,除大拇指外的4根手指骨頭全部斷裂,只剩一點肉皮連著。戰場上醫療條件極為有限,隨行的醫護人員只為他進行了簡單的包扎。“當時一點沒感覺到疼,可能是被打麻了。”張泉帶傷繼續戰斗,直到戰斗結束后才被送到醫院。當醫生解開被鮮血浸透的紗布時,發現他的4根手指已經全部壞死,須馬上截掉。
就這樣,張老永遠失去了4根手指。戰爭結束后,他被定為三級傷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