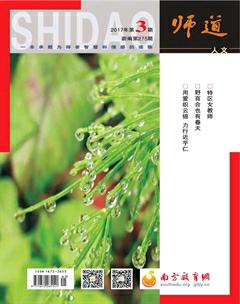特教:揭示教育本質的地方
王祥連
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說:“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和認識的堆積”,“教育的過程首先是一個精神成長過程,然后才成為科學獲知的一部分。”教育不是知識的堆積,而是一種喚醒。教育本身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如果一種教育未能觸及到人的靈魂,未能引起人靈魂深處的激蕩,那么就不能被稱之為本真的教育。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捫心自問,自己每天的教育是否真正觸及到人的靈魂,是否只是“理性知識和認識的堆積”——恐怕,我們連自己的靈魂也沒有怎么觸及到。也許,我們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不斷循環往復必做的事務、該教的課務而已……至于“喚醒靈魂”,或許從未真正想過!我們關心的只是知識的傳授、分數的獲得、成績的提高、績效的考核……至于“觸及靈魂”,先是退而次之,終究忽略之吧,因為“觸及靈魂”只有被喚醒的“靈魂”自己知道,其他人并不關注與重視,更不能換來“績效”考核與認可!于是,我們的教育——離“績效”越來越近,離靈魂越來越遠,最后以致于我們教育者的靈魂似乎也離自己越來越遠,于是我們進入了連自己也說不清的職業與靈魂的雙重深度倦怠!作為教育者,我們天天從事教育,因為從未真正思考與觸及教育的本質,天天從事沒有觸及教育本質的教育,焉能不失去教育的本真與自我靈魂的本真?
然而,在特校并非如此。因為特教工作者面對的是一個個特殊的靈魂,是一個個被沉睡的上帝不小心忽略的特殊的靈魂。他們的教育使命與目標非常清晰與明確:面對與呵護這些特殊的靈魂,喚醒他們——融入社會,獲得生命的尊嚴。
讓被上帝忽略了生命尊嚴的特殊孩子,在這里(特校、特教)得以被喚醒,重獲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尊嚴,能夠以人應有的尊嚴生活(融入社會)。這是特教工作者核心價值觀所在。他們對此,無比清楚、明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校(特教),是真正揭示教育本質的地方,是我們普教工作者須從中獲取教育的良知與本真的地方。以上認識,來自于自己對特校(特教)身臨其境的切身體悟。
進門:一句問好帶來的感動
2016年6月16日,我作為南京市基礎教育專家培養對象高級研修班學員之一,走進了南京市育智學校的大門,第一次零距離接觸與切身感受特殊教育。
在我最初的想象里,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學校呢?在普通小學工作26年的我,心中有一種莫名的忐忑與傷感。我猜想:那里一定是生命的尊嚴被遺忘的角落;那里匯集的是一些卑微的弱小的生命,是一些僅從外表上就能看出生命之不幸的個體的集合……
走進南京市育智學校大門,迎面就是不大的操場,高矮大小參差不一的孩子們正在運動,有的打羽毛球,有的跳繩,有的踢足球,有的在奔跑……一個白字紅底的巨大橫幅自然吸引了我的視線,上書:“同在一片藍天下,關愛每一個孩子!”
“老……老……老師……好!”一個高個子男生從我面前穿過,差點與我撞個滿懷,他趕緊不太好意思地用含混不清的聲音努力而認真地向我問好!
“你好!你好!”我趕緊回應。心中不由一震:并非如我之前所想!“生命自有尊嚴——我真不該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不由在心中自責,亦為這個孩子剛才的一句問好而欣喜不已!
課堂:簡單而溫暖,因為照顧到每一個孩子
以人為本,因材施教——在這里的課堂真正得以落實。從南京市育智學校一個不大的功能室的后門悄悄地走進去,里面正在上課。七、八個高矮大小參差不一的孩子圍坐在條形桌南北西三面,東面是黑板與顯示屏幕,老師正站在中間上課。
這是一節手工制作課,老師先放視頻給孩子們看,視頻中老師邊動手示范演示邊指導講解。看到老師在視頻中,孩子們都“哦”“哦”地發出興奮的呼聲,一個孩子樂呵呵地大聲說了一句“老師,你在電視里!”其他孩子又是一陣歡呼,我們在后面聽課的老師也都笑出聲來。孩子是善良與天真的,他們看到老師在視頻中,要說出來,表達他們的快樂……
課上得極其簡單,接下來就是教師發材料讓孩子們一一認識。再下來,就是一步一步動手制作。跟著老師一步一步地完成,老師每講解、演示一步,都要停下來,留下足夠的時間細心觀察并詢問每一個孩子:“做好了嗎?會做嗎?”
有一個孩子開始搖頭,向老師說“老師,我不會做!”老師走過去,手把手地細心地做給她看……又有一個孩子說不會做,老師又來到這個孩子身邊,慢慢地教他……
“老師,我做好了!”一個孩子發出勝利的高聲的歡呼,聲音高得嚇了我們一跳。老師用手指放在嘴邊,作出“噓”聲動作,示意他小聲點,然后表揚他做得好……
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這樣的課堂不就是讓每一個個體有尊嚴地生活的過程嗎?這個過程就是最好的教育!
之后,從說課與評課中,我進一步了解到:特校的教育、特教的課堂,特別注重學生實際學情與智力水平具體狀況的評估。一般學生入校時會出示醫生給出的智力水平測試結果。但特校老師們還要做學生各領域發展現狀的具體評估,這樣便于找到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找準起點,教學時會更加清楚學生的所能所需,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最大程度避免誤判與誤差。因為這些孩子差別實在是太大了,這是客觀的先天差異所決定的,不按照每一個體各自的水平與速度進行教學是行不通的!他們認為,對特殊孩子的教學評估就如同醫生看片子、看檢驗報告一樣重要,否則就無法對癥下藥——無法施教……為此,特校課表中還有專門的“個訓課”——針對不同個體發展需要,專門進行個別化教育與康復訓練的課。特校的課堂形式與體制上是班級授課制,這是為了形成一個群體,為了孩子間的交流合作能力發展與融入社會的需要。而在課堂上最大程度地依據學情評估的因材施教與個訓課的個別化教育,則是進一步針對個體發展需要而特別設立……還有“走班”——實際也是體現對個別化需求的重視與支持。
目中有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大愛無言,大象無形……在這里顯得無比重要與真實,并且真正地落實與體現!正因此,讓人感到教育本真的溫度與溫暖,人性的光輝與光彩!
課程:為了每一個孩子真正融入社會而開設、開發
“生活即教育”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他認為“生活即教育”,生活與教育是同一過程,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生活也不能脫離教育。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應有什么樣的教育,教育的內容應根據生活的需要。
確實,教育的本真不需要驚天動地,只要實實在在;教育的本真不需要刻意追求,只要真真切切。教育無處不在,教育隨時隨刻。在特校,這樣的理念得到了最好的落實——從特殊學生實際需要出發,真正開設適應學生需要的課程。
一是表現在對于國家課程的校本化、個體化。即使是國家專門為特殊孩子培智之用的教材,到了各個特殊學校,依然無法“照本宣科”直接執行。用特校教師的話來說:“時代在變化,孩子在變化,課程也必須因時而變,因人而變。國家編寫的教材是1993年的,但這幾年中重度智障學生越來越多,不太適合了。所以各特校都要編寫真正貼近學生的校本教材!況且,每個班的這幾個(十來個)孩子的差異實在是太大了,不考慮個別差異的教學,是根本無效的!”因此,跟從事普通教育的教師不同的是,特校教師課程開發與設計的意識是極強的,把課程轉化為適應自己對本班每一個孩子評估的水平,是開展教學工作的前提。
二是著眼于孩子們“融入社會”需要的校本課程的開發。在南京市育智學校,我了解到:為了特殊孩子能夠得到提高和補償,學校設置了下午的訓練課程,如自理、發飾、手工、園藝、足球、棋類等,拓展孩子們的課外休閑項目,提高孩子們的動手能力。他們的理念是: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特校課程的設置與開發也應該與時俱進,就是為了讓孩子“融入社會”這一教育目標的實現。不僅是生活課程的開發、設置,還有相應的教具的開發和教法研究與創新,以期學校所開設、開發的活動課程、訓練課程等真正富有成效。
請看,南京市育智學校一則活動報道:“沐浴晨光,迎著秋風,南京市育智學校在9月1日上午舉行了‘迎接新學期,文明伴我行開學典禮。新的學期,學校迎來了新的同學與老師,烈日炎炎也抵擋不住大家對新學期的向往和期待,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高年級的哥哥姐姐們給一年級的小朋友送上了祝福卡片;少先隊員代表與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暑假生活,希望自己能在新的學期里更進一步;校長也給同學們提出了新學期的要求,希望孩子們在新的學期里,要守秩序、愛勞動、愛運動,遵守八禮四儀。新的學期,新的起點,希望同學們能在新的學期里學到更多的本領與知識,讓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更加充滿信心!”——在這則報道中,我們根本看不到特校孩子生命的弱勢,而是每一個體在平等地感受著與享受著生活的尊嚴!“讓智障兒童有尊嚴地生活”——南京市育智學校的辦學理念不就體現在這樣的教育過程之中嗎?眼前不由浮現出他們學校會議室里書寫的《世界人權宣言》中那句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發展人的個性。”我不由再次想起杜威的名言:“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
研究:追求專業性、科學性與教育的理想國
特校教師對于專業性與教育的科學性的渴求程度是我們普教老師達不到的。這是他們工作需要所決定的。與特教教師交流中發現,她們反復強調專業性對特殊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與支撐作用。
她們認為,特殊教育——愛心是必須的,是基礎,但光有愛心還遠遠不夠。因為特殊孩子的教育,一般的方式方法對于他們根本無濟于事,所以更需要專業!如同醫生,光有愛心與耐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愛心與耐心,并不能救人一命!
比如,有學生會因為吃飯晚了一會而打滾、大哭,攻擊靠近的人——在普通學校,我們可能呵斥批評,或者請家長來配合制止。但特校老師不這么認為,也不會這么做。他們必須要針對個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針對這種個案,他們一般會做情緒行為功能性評估,了解原因與表現以及結果,針對評估制定策略。評估完了,他們會做“IEP”(源于美國聯邦政府于一九七五年頒布《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在各項立法要點中最受特殊教育家關切的一項是“為每一位障礙兒童維持一項個別化的教育方案”。“個別化的教育方案”簡稱“IEP”)。他們強調、注重與追求的是:對某個學生的具體情況的評估與認識只是基于那個學生,換作別的學生即便同樣的情況也可能不是同樣的問題,所以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這就是特殊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簡單問題的復雜性的表現與特點。譬如以上“學生會因為吃飯晚了一會而大哭打滾,攻擊靠近的人”可能是情緒問題,也可能是為了引起教師的關注等等方面的問題。
針對不同情況的評估與認識,制訂“IEP”(個別化的教育方案):如果他們認為該孩子是情緒出現問題,無法表達(這個孩子這樣的表現其實就是因為其不會表達),那他們針對性的個別化教育方案就應該是:對其不合理的行為不予理睬,當然確保安全的情況,說明發脾氣沒用;然后等其平靜后對他說飯晚點了,給予其鼓勵,讓其第一個打到飯!這也就是負強化與正強化,認知指導。當然最簡便的辦法是以后飯盡量不晚點,改變環境。改變不了孩子時,就改變環境,給予支持……若另一個孩子同樣的表現,經評估確定是另外的問題(譬如不是情緒表達問題,而是引起教師關注或其它什么問題),那就會是另外的“IEP”……
特校老師的專業性在于:更需要從科學(有時可能是醫學)的角度,開出符合不同個體實際情況的教育方案!
我們還了解到:為掌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給予學生最需要的支持,南京市育智學校的老師們曾參加了“腦癱兒童動作康復”專業培訓(邀請重慶市向陽兒童發展中心的郭蘇晉老師專題講學與培訓),通過培訓,老師們增加了相關的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對腦癱兒童進行再認識,明確了針對腦癱兒童進行康復訓練時的操作原則、方法及注意事項。此外,還有“自閉癥孩子教育”等各項專業培訓等等。
特別驚訝的是,在南京市育智學校聽到他們學校的全國“十二五”規劃課題“智力發展障礙學生教育康復模式的實踐研究”中期匯報。
初次看到這個課題,就被課題名稱中的“康復”一詞吸引——心中一動:能“康復”嗎?后來得知,“康復”一詞在特殊教育中被經常用到。如,腦癱孩子需要動作康復等。特校教師們自己都知道完全康復是不可能的,他們所用“康復”的意思就是我們理解的“改善”之意,但他們喜歡用“康復”一詞。我想:他們是在追尋教育的理想國,滿懷期望、永不放棄與失去教育創造生命奇跡的夢想——讓所有孩子的身心得以“康復”,讓所有被上蒼所忽視的特殊孩子的靈魂得以“喚醒”,讓生命的尊嚴在孩子們真實的世界中“醒來”。“康復”——身體的康復、精神的康復、靈魂的康復、生命尊嚴的康復(這些孩子本應與常人一樣擁有生命的尊嚴、靈魂的自由,應該復原而讓他們重新擁有),這就是他們的特教夢、教育夢—所追尋的教育的理想國!
行文至此,忽萌生一個愿望與想法——普教工作者應該多去特校觀摩、聽課、感受、學習、研討,去發現與感悟教育的真諦!因為我覺得:特校是教育的圣地,那里揭示了教育的本質與本真,詮釋著教育的真知與真理;特校教師,較之我們——更知教育的艱難困苦、辛酸苦辣,也更知教育的偉大與崇高、光榮與夢想!
(作者單位:江蘇南京市溧水區實驗小學)
責任編輯 黃佳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