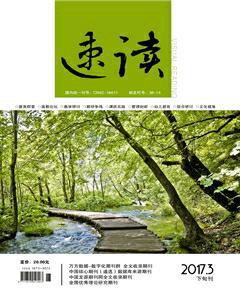英美后現代主義小說的特征
陳濤
一、文本的本體論概念
從認識論、反映論的角度來看,現實主義小說和現代主義小說的作家都非常重視在小說中反映現實世界。后現代主義小說作家卻對此不感興趣,后現代主義小說向本體論發生了轉型。傳統小說竭力想告訴讀者作品是關于現實世界中某人某事,后現代主義小說家更加感興趣的是自己在語言中創造一個世界。他們拒絕事實密度,反對傳統小說對于現實世界中方方面面具體細致的反映。納博科夫談《洛麗塔》的創作時指出,整個文本創作可以看成是他和英語談了一場戀愛游戲。
Donald Barthelme的短篇小說《氣球》又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作品的結構就像拼貼畫。題目沒有社會、道德和心理的指向。第一段沒有后現代主義小說的影子。作者故意賣關子,呈現出神秘要素,營造精彩曲折的氣氛。這恰恰是對傳統小說開場白的戲仿。小說家通過作品探討哲學理念。假設和否定的原則貫穿整個作品中,不斷出現建構與解構,肯定與否定,通過否定理念產生不確定性。從傳統意義上看,這部作品沒有情節:一個巨大的氣球在一夜之間覆蓋了曼哈頓的四十五個街區,并且存在了二十二天。紐約人對它產生各種回應、評論和爭論。形式和內容、主題與技巧等觀念都被消解,這種消解給了作品一定的意義:它沒有意義,只有意義的形式。這戲仿了傳統觀念的要求:小說必須要有邏輯指向和道德指向。從本體論概念來看,氣球不是關于任何一個故事。它通過刺激人們的想象和爭論來發現紐約人的自我,這些想象和爭論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從而產生不確定性。敘述者角色的多元反映了后現代主義藝術的多元:他是講故事的人、觀察者、評論者、和氣球的擁有者。但是他似乎是超然的,與氣球沒有關系,不給我們滿意的答案。讀者受敘述者的影響,又扮演著什么角色呢?我們在作品中一段一段尋找文本之意義,不斷建構和解構意義,正如作品中的紐約人不斷在尋找氣球的意義。作品提供了讀者和觀察者心理經歷的可能性。
二、語言自治
后現代主義小說不受傳統話語限制,處處體現出作品和作家的自我分析、自我反省、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后現代主義小說家不考慮語法,他們運用自己的語言進行創作。以喬伊斯為例,他的《都柏林人》可以看作是與現實主義的告別,《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是其早期現代主義作品,《尤利西斯》高度體現出現代主義作品的特點。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開始了后現代主義藝術創作,代碼和符號用得鋪天蓋地。
唐納德·巴塞爾姆的代表作《白雪公主》,用松散的片斷拼貼的手法再現了格林童話《白雪公主》。它不再講故事,不再敘述,已退化成一種語言斷片的隨意組合。像其他后現代主義小說家利用幾何圖形來表現事物,以獲得一種直觀的效果一樣,巴塞爾姆也在《白雪公主》中用豎排的6個小圓形來表示白雪公主身體一側的6個美人痣。如《白雪公主》中一段沒有標點符號的人物獨白,其語言支離破碎。這段無意識,或“他者”說出的話,表現的是白雪公主在幻覺中與王子保羅的幽會。從形式上看,《白雪公主》呈零散、任意、平面、取消意義、取消深度狀,似乎是完全無目的的語言游戲,因為讀者不能從作品形式上找到走向意義深度的向導。然而,這種游戲只是假象,是無目的的目的性,而目的性是要求讀者參與才能完成的。
三、小說與批評的邊界話語
福爾斯有意將20世紀與19世紀對立,將時間推移了100年,當時的英國受到達爾文主義影響,社會充滿了懷疑和矛盾沖突。作者在小說的前幾章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風格進行創作,但是在書的第12章結尾處作者提了兩個問題:誰是莎拉?她從哪里來?這種質疑對于讀者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第13章作者竟然跳了出來,與讀者直接進行交流討論,小說應該如何進行創作。小說的結尾是開放性的:比如第44章設計成查爾斯可以與歐內斯蒂娜結婚,生了7個孩子,產生一個美滿幸福的結局;又比如第60章設計成查爾斯可以和莎拉和解,在有愛情的基礎上以情人的關系浪漫地生活在一起,拋棄歐內斯蒂娜;或者像第61章設計成查爾斯可以同時放棄歐內斯蒂娜和莎拉,自己獨自一人過隱士的生活。這種沒有結尾或者是多重的結尾,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小說相對于傳統現代主義小說的自由。作者放下身價,與讀者討論小說的創作,也讓讀者感覺親切。這體現了敘事自由、女性自由和時代自由的原則。
作者的藝術風格是介于現代主義小說和后現代主義小說之間的。人物本身就是作家,在寫作品結尾時他提出了三個問題:①小說必須承認其虛構性和隱喻的無效;②選擇忽視此問題或者否認其關聯;③建立另外某種可接受的小說、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后現代主義小說家考慮這三個問題,顯示出他們對于文本構建的強烈意識。這時他的現實生活中的情人突然出現在作品中,打斷了讀者的閱讀,產生了“短路”,這個人物就不再僅僅是小說中的角色了。但是這種猛烈的反差模式不能再作品中過多出現,不然對于讀者產生的沖擊就過大了。
四、游戲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系
對于后現代主義小說家而言,現實世界是多樣和不確定的貝克特的小說《莫菲》出版于1938年。它不是特別正宗的后現代主義小說,但是已經出現了后現代主義小說的藝術變化了。小說開始部分敘述莫菲被七條圍巾綁著,但是讀者只能數出六條圍巾,那么第七條圍巾到哪里去了?又是誰在敘述這個故事?莫菲為什么被圍巾綁著?一個人怎樣能夠綁到如此程度?這些都體現出信息的缺失。小說第二章開頭通過列出事實和數字的清單來描述Celia這個人物,體現出對于傳統文學描述的戲仿,顛覆傳統小說女主人公外貌描寫。傳統小說家喜愛描寫人物信息,如果人物是一個善良的好人,就會被描寫成外貌非常美好的人。但是后現代主義小說家拒絕這么做,他們通過戲仿和挖苦來挫敗有教養的讀者。
貝克特早期的小說作品中,最重要的三部曲系列是《莫洛瓦》《馬龍之死》和《無名氏》。《無名氏》中的主人公一個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談論人生,體現了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他的困境是在欲望和主張之間晃來晃去,這表明他有欲望,但是遭到外界阻壓。在小說《瓦特》中,貝克特使用了類似漢語中的“做人難、難做人、人難做”的語言游戲。對于現代主義小說家而言,選擇就不能避免有遺漏。后現代主義小說家卻通過窮盡安排組合的各種可能和顛覆文本的連續性,來拒絕選擇之義務。
Julio Cortaza的短篇小說“Continuity of Parks”游戲現實與小說之間的關系。小說的標題非常巧妙,沒有道德指向,不進行說教,卻很現實。Parks是現實與想象的混合。讀者同樣參與作品建構,我們面對的是兩個公園:一個是商人讀小說時房屋周圍生長著橡樹的環境;另一個是他閱讀的小說中的一男一女所處的森林環境。故事的開頭和傳統小說一樣非常具有現實色彩,提供足夠信息介紹主人公。詳實描寫他寫委托書及其商業活動。作者有意布局,將現實與虛幻無縫結合。作者即使不顧現實世界的規則,也要遵守小說創作的一些規則。如果不寫一些讀者熟悉的可以接受的小說背景,作品就會失敗。這部作品僅有兩段,各自功能不同。第一段介紹背景、人物和謀殺計劃;第二段一步步詳細描述謀殺過程,直到讀者突然意識到非常急劇的現實與虛幻的轉換。兩段相互指示,相互補充。作品中主人公閱讀小說的現實,受到另外一個現實的入侵:被閱讀的小說中的人物的現實,即小說中的人物跳入了他的世界,而他將像所閱讀的小說中的受害者那樣,被謀殺。作者通過消解現實與幻想之間的區別來戲劇化現實的邊緣,情節的突然轉換質疑著現實的本質。后現代主義小說作家在進行藝術創作時呈現多樣的現實,體現出他們對于現實與小說之界限的關注和探索。
五、激進的形式主義
英國小說家B·S·約翰遜對于喬伊斯非常尊敬,認為他是小說界不斷革新實驗的愛因斯坦。對于后現代主義小說家而言,小說中發生了什么故事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小說是如何寫的。后人中又有多少人會追隨小說家繼續在作品中進行革新創作。文學始終在不斷運動著。盡管它不斷受到工業、信息時代和大數據等的挑戰,小說卻一直在進化發展和自我發現。約翰遜認為生活并不講述故事,生活是混亂、流動和隨意的。他指出作家只有通過嚴格仔細的挑選,才能夠從生活中提煉出一個故事,而這樣的故事卻不是真實的。他個人認為講述故事實際上是在講述謊言,真相與小說是對立的。他的小說《旅行的人們》全書共9章,使用了8種不同的風格,第一章和第九章使用同樣的風格以保持全書的循環統一,其余7章有7種不同的風格。這就是一種革新實驗。他還借鑒了斯圖恩在《項狄傳》中的創作技巧,使用隨意樣式的灰色書頁表示一位老人在心臟病發作之后的無意識狀態,然后用規則的灰色書頁表示他處于睡眠狀態,之后的黑色書頁表示人物死了。
他的小說《不幸者》是一本活頁散裝小說,讀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將全書松散的各章重新排列,任意組合,可以從任何一章開始閱讀,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止閱讀。讀者可以關注自己每時每刻的體驗和感覺。小說的創作與作者身患癌癥的好朋友密切相連,這樣能夠反映出材料的隨意性,體現出癌癥病人時時刻刻隨意思考人生和疾病的特性。在《柯里斯蒂·馬瑞自己的復式計帳》中,主人公以投毒等方式報復社會,當他認為社會對于他的不公平程度高時,他就用更加可怕的方式報復社會,取得復式計帳的更加高的分數,把帳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