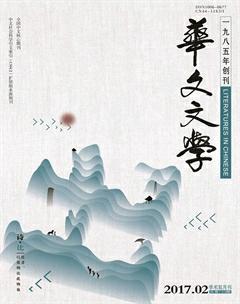漢語文學研究近著序言二則
摘要:此文是朱壽桐為新出版的兩本論著所寫的序言。其一是莊園的《個人的存在與拯救》,作為她的博士生導師,他指出該書為解開高行健創作的價值之謎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學術思路,他還對高行健浪漫的“大孤獨”進行了精彩獨特的闡發。其二是程國君的《〈美華文學〉與北美新移民文學研究》,他認為該論著將《美華文學》定義為“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刊物”,乃是在華文文學范疇內突出這個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學”品質,體現了深到而敏銳的學術自覺。序言中,朱壽桐對“漢語文學”和“漢語新文學”這兩個概念體現的學術前景充滿自信與欣慰。
關鍵詞:漢語文學;序言;朱壽桐;莊園;程國君
中圖分類號:I1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7)2-0005-07
一、踽踽獨行于漢語文學世界
——莊園《個人的存在與拯救》序
從較為理想的社會角色方面而言,文學研究者也許是最難擔當的角色。人們有理由要求他們的作品充滿文采,洋溢著感性的情緒甚至是施雷格爾式的激情,因為他們研究的是文學,文學既然不言而喻地包含著這些內容,文學研究成果理所當然地也應擁有這些因素。當然人們更可以要求文學研究者的文字充滿理性,在理論的講求中帶著哲理的光澤與萃思的精彩,于是黑格爾式的思辨亦是應有之義,因為文學所必然承載的各種哲性理念必須在文學研究中作出響應。即使都具備了這些是不是就可以了?未必。文學創作的世界并不僅僅呈現情感、靈性的色彩以及理論、哲思的光澤,它是那樣的豐富,那樣的駁雜,那樣的多層面和多向度,這一切都可能成為社會閱讀對于文學研究者學養與經驗的要求。于是,人們也同樣有權要求里爾克的研究者在學術文字中帶有尼采式的瘋癲與佯狂,要求所有悲劇的研究者在學術敘述中參詳著莎士比亞式甚至是哈姆雷特式的憂郁。
莊園選擇了高行健作為她的研究對象,書稿寫出來了,出版以后就有可能面臨人們的這些要求。高行健的文學世界幾乎什么都明確擁有,既帶著浪漫的甚至是空想的激情,帶著與靈異的感性相伴的悟解與性靈,又不乏深刻的理性思考甚至終極性的人生追問,更兼具社會關懷歷史審視和現實批判的熱忱。他的早期詩集被命名為“游神與玄思”,表現的正是這種多層次、多維度、多方位的精神承擔。這樣的承擔過于沉重,使得他不得不從他所極為關注也極為倚重的現實社會中抽身出來,悉心營造荒誕幻想中的文學世界,將他的人生體驗投放在某種超驗的幻構中以求更加充分更有深度的表現,于是他的作品基本上無法拒絕尼采的誘引與召喚。盡管在與尼采的對比中他更傾向于卡夫卡。這位歷來重視現代性追求的漢語文學家①認為,尼采標志著“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終結”,“而真正宣告現代文學的誕生的應該是卡夫卡”:“卡夫卡把現代社會中人的真實處境做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種種社會關系中,乃至于在家人之中,人不過如同一個蟲子,這么渺小可憐,別說主宰世界,連自己的命運都把握不了,莫名奇妙。毫無緣由,卻受到審判。”②這正是他對“現代性”的理解,也是他的作品自始至終作“現代性”追求的基本精神內核,體現并包含著一種卡夫卡式的荒誕與恐懼。然而這并不是高行健的全部。或許他寫作《車站》、《野人》等戲劇作品的時候會滿足于卡夫卡式的這種荒誕的描述與恐懼的表現,同時當然也帶有尤涅斯庫式的狡智與巧構。不過當他寫作《靈山》、《一個人的圣經》這些令他贏得更大成功的小說時,他一定沒有遠離尼采,就像執意追求“現代性”的他從來沒有遠離過浪漫主義一樣。尼采的魅力在于他的精神坩堝效應,將康德的悲劇哲學,叔本華的意志論哲學,瓦格納的頹喪音樂,歌德所創造的浮士德式的狂歡,還有盧梭式的孤獨漫步,浪漫主義的暴虐與反叛以及現代主義的自我標高與否定,全都化融于自己“查拉圖斯屈拉”式的思維和囈語之中。高行健的后期小說顯然比他前期的戲劇更接近尼采,特別是更能體現尼采的這種坩堝效應。
以高行健小說“現代性”為主題的莊園的這部研究專著,對高行健所進行的上述現代性思辨做出了更加充分的學術揭示。莊園做過記者,文筆洗煉而表達精到,對于高行健作品中的情感分析與靈性解剖顯然較能勝任;她長期編輯學術雜志,理論修養有相當的積累,對于高行健作品中的人生玄思和社會悟解也差可傳達與詳擬。然而,卡夫卡、尼采式的荒誕體驗與極端表達,與我們也與莊園所擁有的正常的人生和文學研究相距甚遠,由此可見,研究對象擁有怎樣的資源,就相應地對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提出類似的內涵要求,在當代社會文化實踐中可能并不現實。也許莊園意識到了其中的道理,從而也意識到自身從事高行健研究的可能性,她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寫成了這部論著,努力實踐著與從情緒個性、精神氣質到思維境界都和自己距離甚遠的研究對象進行對話的學術夢想。
莊園的這部論著又是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系統、全面而有深度地論述了高行健小說的現代性追求及其思想、藝術與美學的結果,將高行健的戲劇創作、理論思考和小說創作貫通起來一起,探尋出作家現代性追求的核心要素乃在于個性與自由。自由是一個老題目,在文學歷史發展的每一步,自由都會成為文學家反抗現行社會秩序和文學秩序的貫通武器,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莊園從理論上把握住了高行健創作的特質:他是在反抗或者抗衡現代社會公認秩序以及文學通行秩序的意義上實施并完成自己的現代性追求的。這是一種建立在現代性意識層次上的自由意識,較之于向古典主義秩序爭取的浪漫主義自由,具有更明顯的時代色彩,現代風貌和更加深沉的姿態,更加現代化的內涵。這是對自由的現代主義所進行的理論闡釋,顯示著這篇論文重要的理論貢獻。
以這樣的理論思考,作者重點考察了高行健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四個方面內容,分別是他的存在的荒誕感,瘋癲的女性書寫,以及拯救與逃亡的心性,還有就是文學與自由的辯證。所有這些內容都是當代中國經驗中最為集中的現代體驗,體現著各種形而下與形而上的文化質量。作者通過對《靈山》、《一個人的圣經》等小說的精當而有力的分析,準確地揭示了作家隱含在作品中的各種層次的文化特質,為解開高行健創作的價值之謎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學術思路。
由此出發,我們的研究思路還可以從一個浪漫型現代作家的孤獨體驗著手。我們面對的高行健是一個孤獨者,盡管他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個特別幸運的孤獨者,他獲得了象征著永恒成功的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獲獎沒有得到祖國的祝賀,更不用說歡呼,他的孤獨可想而知。即便十幾年以后的現在他仍然是個孤獨者,因為為他而起的掌聲依舊沒有在自己的故國得到響應。任何響應的歡呼如果不是通過他最熟悉的文字和鄉音發出,由此引起的孤獨感就不會消失,而屬于他的寥落的掌聲常常是沖著他早期的戲劇作品而去,他后來的嘔心瀝血之作依然似乎仍然是他“一個人的圣經”。
他的現代性體驗在這種深刻和厚重的孤獨中完成,他踽踽獨行,飄萍斷箏,天涯海角,孑然一身。這是一種大孤獨,屬于強者十分在意并努力追求的那一種。強大的靈魂往往不愿意輕易走出這樣的孤獨境地,甚至不愿意減弱這樣的孤獨感,這就是現代性的浪漫感。感受到孤獨不斷地哭訴,猶如當年的盧梭、繆塞和郁達夫,那是一種浪漫的情懷。而孤獨漫步者的沉思目的在于尋求解脫,或者尋求沉溺,宣泄孤獨往往為了蕩滌靈魂的塵垢,欣賞孤獨往往為了表達自由的心志,這便是現代性的孤獨感和浪漫性。于是,現代性的追求中孤獨與自由相伴而行,同樣具有現代精神的田漢塑造過一個羨慕“萬里一生孤”的少年形象,同樣具有更徹底的現代精神的魯迅為文壇貢獻了追求孤獨的浪漫性的涓生:他立意于拒絕哪怕是來自愛情的羈絆,向著冒險的人生孤身前往。這樣的人物及其表現既浪漫,又唯美,當然也相當現代。高行健比一般的漢語文學家更懂得現代性的浪漫與孤獨:他將孤獨當作常態而不是人生異態,他善于在孤獨中感受真實,感受真情,在孤獨中感受日常,感受俗常甚至庸碌。他的小說經常離不開粗野的描寫,那就是力圖向人們展示他所體驗的孤獨人生的俗常與庸碌。當他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定非常痛苦。這時候如果有人指責他的創作猶如當年弗·施雷格爾的《盧琴德》遭遇到的指責一樣,他的孤獨感會成倍增加。于是,盡管他已經摘取了文學皇冠上的明珠,然而他仍就是一個孤獨的化身。他孤獨地寫作,孤獨地繪畫,孤獨地排戲,孤獨地沉寂在較少人喝彩的境界。
然而他也在孤獨中體驗到了自由,那種只有通過孤獨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自由是痛苦的,因為孤獨。靈魂的自由經常通過人生的痛苦來獲得。養尊處優,鮮花掌聲確實可以令人備感榮耀,但那樣一種狀態往往會要求以犧牲某種意義上的自由為代價。高行健在無邊的孤獨中返回到一種與自己靈魂直接對話的自由,或者一種向著無物之陣直接表述的自由,這是他的幸福,從無邊的孤獨中所能夠體驗的幸福。
這樣的自由是現代的,它擁有現代性的唯美。莊園的論述未能涉及高行健的唯美視角,這不是她的錯失,因為高行健那種全然屬于現代性的唯美情懷掩藏得很深。一個久炙法蘭西文化的作家不可能對唯美無動于衷或漠然置之,只不過他可以通過自己精神境界的坩堝效應將其溶蝕得看起來蕩然無痕。一個人孤獨地向著“靈山”默默前行,一切世間的污泥濁水在此過程中不斷沖洗著他的靈魂,這樣的意象結構就是一種唯美的結構。只有像高行健這樣浪漫到骨子里的文學家才會去咀嚼這混合著污濁的美感。浪漫之力將一切的美感都自由地填埋在垃圾中,然后讓唯美的囈語攛掇靈魂的飛升。遺落下來的所有丑的垃圾都是人體皮囊,都是生命中無法忍受之重。一切用于呈現的美都是危險的,一切的美都是純形式的,純靈魂的,純理性的,于是作家選擇了抽象,選擇了宗教,選擇了靈山以及哪怕只屬于一個人的圣經。
高行健在孤獨中尋覓和享受自由,在自由中創造唯美,那是一種被抽取了質地感的美,通向抽象的美,這種美就是表像的自由,就是哲學的自由,又與靈魂的孤獨鏈接在一起。這就是我們可能認知的高行健,既是他的人生狀態,也是他的創作內容,融合著他的現代理念,熔鑄著他的現代情感方式。這是不是高行健真切的樣貌?不敢說。作為漢語新文學世界一個獨特而卓然的文學存在,高行健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認知和闡述,上述這種認知和闡述至少可以聊備一格。有信心的是,這樣的認知都可以從莊園的這部論著中獲得啟迪,而莊園對高行健確實下了長期的功夫,這一點連德高望重的劉再復先生也予以明確肯定。
也許讀者會注意到,無論我的序文還是莊園的論著,都傾向于將高行健定位為漢語新文學家,而盡可能避免確認他是中國作家還是法國華文作家。的確,高行健及其文學存在的地理定位或國族定位原本就是一個問題。作為一位長期旅居法國的中國人,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曾經在許多人那里被認為是十分尷尬的事件。我在主持《漢語新文學通史》③的編撰工作時,即將高行健的獲獎作為近百年漢語新文學歷史的終結點,題目也標示為“尷尬的諾貝爾獎”。其實,只要承認了漢語文學或漢語新文學這種學術概念,這樣的尷尬就會立即解除。無論獲獎主體是否身在中國還是身屬法國,這一重要獎項絕不是獎勵給獲獎主體所在國家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對一種文學語言以及相關人生經驗精彩傳達的褒獎,具體地說是對漢語及其所依存的經驗世界的肯定。盡管這樣的獎項對于外國文本而言總須借助于翻譯載體,但作品原語及其對原語文化資源進行成功表述的可能性以及由此產生的精彩效果才是其成功的基本依據,各種人生哲學與普世價值之類都必須通過上述語言資源加以呈現。于是,高行健的獲獎是漢語新文學的獲獎,這里的榮譽如果難于在國家版圖上落地,則完全可以在漢語文學這樣一個文化版圖上生根開花。高行健和莫言,他們都是在漢語新文學的語言文化平臺上向世界呈現了自己的色彩斑斕,他們都是漢語新文學世界的文化英雄。我們應該拿出足夠的真誠與熱忱研究他們,以學術的成果和力量向他們致敬。
二、深到而敏銳的學術自覺
——程國君《〈美華文學〉與北美
新移民文學研究》序
程國君教授擅長于研究文學社團和文人群體,先前研究新月派,再后來研究臺灣女性作家群的文學創作,現在又研究《美華文學》雜志與北美文學家群體。再三的學術成功使他嘗到了文學群體研究的甜頭,他在文學群體研究的領域開辟出了一條適合于他自己的個人化的學術道路。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相對于作家作品研究而言,文學社團或文人群體、文學期刊的研究頗見難度。這不僅僅是因為文學社團、文人群體以及文學期刊編著集體是由眾多作家個體組合而成的,一個綜合體在規模和構成方面總會比一個單體更其復雜,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學綜合體的社團或文人群體,它們是一個有鮮明個性的“雜多”。千萬不要以為將一個個作家個體進行簡單相加,就可以得出一個“雜多”型文學社團、文人群體或文學期刊的基本狀貌。魯迅先生說得好,“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里面的,始終都是豆。”④這正道出了文學社團和文人群體難以付諸簡單研究的真諦。
毋庸諱言,一個再統一再簡單的文學團體,其內部的組成人員往往都帶著各自的文學個性,文學傾向,文學風格,他們集合在一起并不能按照我們簡單的想象那樣立即會統一為一個社團共同的個性、傾向和風格,這就需要研究者千方百計在這種“雜多”的個性鏈接中尋找出文學的共性和文化的共性。其次,文學社團、文人群體往往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在這樣的持續期間主要成員或重要成員會常常發生構成性的變化,使得文學社團和文人團體的組成更為復雜,文學社團、文人群體包括文學雜志編輯集體的研究必須適應這樣的復雜性。再次,文人群體或一個文學性的雜志,其構成人員和承載內容往往并不一定局限于文學方面,例如程國君教授研究的新月派,簡單地說是新月詩派,可實際上這個社團包括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甚至還與職業軍人有關系,要想全面把握這樣的文人群體,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無異于一種嚴峻的挑戰。
程國君教授的《新月詩派研究》雖然避開了新月派人員構成成分的“雜多”,但并未回避新月詩派詩學傾向復雜,詩人志趣“雜多”的事實形態,并未對新月詩歌群體進行簡單化的學術處理。他的研究盡可能將學術觸角展開到新月詩歌的各個層面,盡可能覆蓋到新月詩派的全體成員,所留下的論述死角越少越好。毫無疑問,新月詩派這個文人群體不是豆莢,其成員之間的詩風差異遠遠多于他們的文學共性。程國君教授善于在他們諸多差異之中尋求“最大公約數”,得出了“生命詩學”的準確而精彩的學術概括,體現出程國君教授在學術上敢于挑戰、不怕繁難的勇者風范。
在收獲了新月派研究的成功與喝彩之后,他的研究轉向海外華文文學。不過他仍然關注文人群體,這回他選取的研究對象是《美華文學》雜志,以及圍繞著這個雜志的北美華人作家群體。文學雜志與文學社團研究固然有明顯區別,但都可以在文人群體意義上進行學術定義,因而擅長文人群體研究的程國君教授依舊顯得游刃有余,長袖善舞。他的學術開拓依然在處理文學團體不是“豆莢”的復雜現象方面得到了透辟的顯示。
文學雜志研究的關鍵當然在于弄清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稍長的文學期刊免不了包含復雜的沿革,變衍,重組等運作,特別是在海外,同人化的期刊往往由于背景資金的不穩定,主干人員的流動性,以及讀者、作者隊伍的頻繁更新,其編輯策略和文學傾向、文化選擇都會出現種種異數,這一方面增加了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另一方面也為相關的學術研究增加了難度。程國君教授的研究緊緊抓住《美華文學》所具有的種種復雜性展開,連同這個雜志編輯集體和作者群體的演變,雜志發表內容構成的豐富與變化,特別是圍繞著這個重要雜志涌現出的重要華文作家及其各自的志業與成就等等,所展開的學術陳述與學術分析詳密、生動而富有深度,與文學雜志構成的復雜性、豐富性頗相匹配。
其實,內部構成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是一個雜志社或文人群體發生種種運作的基本動因。研究者要將這種歷史運作的內在動因揭示出來,則不能單單依靠一本雜志或一般平行出版物的讀解,尚須研讀和征引大量背景材料,研究各個成員的心志脾性,人際關系及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相互影響。這正是程國君意識到的學術要求,因此他專辟若干章節,專題研究《美華文學》作家群中的重要骨干,將這個文學雜志所屬的作者群體、編輯集體及其他們之間交叉、聯合構成的文人群體,組合成漢語文學世界引人注目的文學存在,通過自己的學術闡述,調動幾乎所有重要的美華文學的資源積累,呈現出當今漢語文學發展中無法或缺的北美板塊,所取得的成就與這個研究對象的存在幾乎具有同樣的意義。
程國君非常清楚,《美華文學》這樣的文學雜志、文人群體與一種文學社團的運作極為相像,因而必須將這個文學雜志當作一個文學社團來研究,這樣才能立體地展示其豐富性、生動性。一個豐富而生動的文學群體有著自己鮮活而獨特的文學作為,有著自己鮮明而成熟的文學志趣,有著自己特別而精致的文化關系、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有著屬于它自己的故事,它的得意,它的輝煌,它的艱難,它的各種各樣的尷尬與無奈,也就是說,一個文人群體,文學社團,幾乎就是一個獨立的文學機體,審美機體,一種有生命的文學生物,一個具有立體性的文學存在。對于這樣的學術對象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的立體思維,需要學術解析的生命感性與理論思維的活性,以免將這種鮮活的對象通過研究反而變得僵死不活。程國君的研究通過多向度學術審視和多維學術處理,非常精彩而且精致地完成了這樣的學術任務。他把握住《美華文學》作為自由出版物的自由特征,努力還原其所具有的自由多樣的文學實驗運作與成就,將這個文學生物描述得相當豐富而充滿活力:“自由出版物產生自由多元的文學。自由出版物開辟了自由多樣文學實驗的園地。所以,在這個刊物上,我們既能夠看到東方主義立場的文本,也能夠看到西方主義立場的文本,耶穌、圣誕以他本真的面貌出現,濃郁的復活節顯示著上帝的存在,假洋鬼子成了主角,東西文化競相亮相。”他注意到《美華文學》的作者,雖然大多來自中國大陸,但他們的自由意識和多元視野決定了他們很少單一地選擇中國或東方立場,而是常常從美國或西方文化立場出發進行寫作,是他們“改變了早期華文創作詆毀西方或美國的立場”,他們以自己的開放性、包容性帶著自己的文學站到了“一種新的文化坐標”之上。這個文學生物由此擁有了自己的靈魂,自己的血脈,自己的品格,因而也享有自己的自由。
文學雜志的研究需要緊扣歷史背景。特別是在海外,不同的經濟背景、政治背景、社會文化背景,對于哪怕是文學雜志的編輯指向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美華文學》這樣的文學雜志往往處在典型的次邊緣狀態。一方面,它是有自身追求的文學生物,且與人們的心靈創造和文化情感表達的愿望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人群都是一種精神上的剛性需求,因而它不可能真正處于邊緣化的狀態。但是,另一方面,它畢竟處在北美的社會主流結構之外,其作為文學雜志和漢語文學創作的載體,相對于主流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生活而言又不得不自處邊緣狀態。相對于一定的創作對象甚至閱讀對象而言,它的主流狀態非常鮮明;而相對于它所處的那個始終活躍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而言,它又不得不自處邊緣,綜合起來,它所體現的只能是次邊緣狀態的文化。程國君的研究非常準確、非常深刻地把握到《美華文學》的這種次邊緣文化形態,作者在《緒論》中就明確勾勒出這樣一種屬于《美華文學》自身的文化形態:“移民文學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美華文學》實際上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因此,以《美華文學》雜志為主或作為一個突破口,把現代化與移民現象結合起來,并從當前涌動世界的全球化及其理論方法來展開北美新移民文學研究,不僅具有重要文學價值,而且也具有的重要的文化價值與意義。”因此,作者既注重文學文本研究,又注重文化研究,從現代性、全球性及其文化價值功能這三個方面確認這個文學雜志及其圍繞它的文學群體的次邊緣特性,使得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意義得到了精準而有分寸的學術闡示。
次邊緣的文化狀態不僅是把握《美華文學》文學群體的學術門鑰,也是研究海外漢語文學與當地華人社會之間關系,海外漢語文學與屬地漢語讀者之間關系,以及海外漢語文學與中國本土讀者之間關系的不二法門。程國君的研究充分地、立體地、全面地揭示了這種種復雜的文化關系。他從次邊緣狀態的文化特性出發,論定了這種文人群體和雜志編輯機構的文化意義及其在海外同胞心目中的價值地位,同時緊密聯系到相當一部分美華文學作品在國內讀書界和文化界的巨大影響,并從“新移民”群體的“跨文化寫作”這樣一個次邊緣文化現象解釋這樣的現象:“跨文化寫作是新移民文學的一個首要特征。像《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人在紐約》這類展現中西文化相遇及其復雜人生體驗與感受的書寫,在新移民文學里是一個最為常見的主題,也是一個恒常主題。《美華文學》雜志的相當多的文本,其小說創作,散文創作,詩歌創作和美術、攝影、書法,也多是表現這一主題的。從中國移植到美國,從東方文化移植到西方文化語境里,個體人生命運會發生極大的變化,原因就在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這實際上正是勾勒并凸顯了《美華文學》及其文人群體的次邊緣文化狀態,它的文學顯現往往是跨文化寫作。
程國君教授對于《美華文學》以及北美漢語文學寫作的研究相當自覺,自覺到他在理論感性方面已經感受到“中國文學”加上“華文文學”的概念面對其次邊緣文化狀態在學術和文化表述上的諸多不便。他覺得需要用“現代漢語文學”這樣一個綜合性更強的概念指認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這個特定的文學整體。在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程國君便指出:“與現代漢語文學的主要發展地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文學刊物相比,(《美華文學》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是典型的自由出版物——是美國自由文化語境下的自由出版物,是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刊物。這也決定了它推動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獨特向度。”程國君分明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他們擁有統一的文化傳統和美學慣性,統一的語言基礎和文化趣尚,截然分成兩塊或者更多的確不便于學術和文化的論述。他選用“現代漢語文學”加以概括。錢理群先生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他曾寫過《現代漢語文學走過的路》一文,曹萬生還編著過《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這樣的命名反映出一種可貴的學術自覺:突破國家、地區的人為區隔,將世界范圍內的漢語文學視為一個整體,即將通常所說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統一為整一的文化審視對象。這是一種歷史理性的體現,也是文學學術發展趨勢的要求。事實上,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都會貫注五四新文化的偉大傳統,體現新文學統一的語言新質、文化素質和審美品質,它們以一種整體的形態和魅力向世界文學展示自己的作用力和影響力,這時候,用國別文學和地區文學強行將它們分割開來往往顯得非常勉強,因為它們早已形成了漢語的“文化共同體”,在任何時候任何意義上都不妨被稱為“漢語文學”。只是,為了區別于傳統漢語寫作,故而需強調“現代漢語文學”。而我在《漢語新文學通史》以及相關的文章中選擇“漢語新文學”概念,只是考慮到“現代漢語”作為學科概念和學術概念已經非常穩固、成熟,“現代漢語文學”的表述面對過于強大的“現代漢語”概念會產生一種語感上的依附感,于是在“漢語文學”之間加一個“新”字,喚起我們曾一度非常熱衷使用的“新文學”概念。其實,使用這種學術表述的“初心”與“現代漢語文學”的概念選擇完全相通。在相當多的學術場合,我們確實需要將中國現當代文學與臺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整合為一個獨立而統一的整體,這時候我們不妨使用“漢語新文學”或“現代漢語文學”概念加以表述。這不僅僅是一個概念的選用問題,更是一種學術理念和學術倫理的選擇。程國君教授在這種迫不得已的學術選擇中使用了“現代漢語文學”,在他的研究中體現出學術理念的自覺性和學術倫理的嚴肅性。
不過,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著名專家,程國君教授仍然希望將華文文學概念貫徹到底。在前引論述中,他將《美華文學》定義為“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刊物”,乃是在華文文學范疇內突出這個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學”品質。這種學術感覺顯然是準確的,雖然處身于美國、加拿大這樣的“異國”,雖然在西方文化語境的籠罩之下,它的語言特質、文化和文學素質與傾向仍然可以被界定為“中國文學”。這種處身“異國”的“中國文學”認知當年胡適先生也有過。上個世紀50年代,周策縱等在美國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白馬文藝社,在漢語新文學寫作方面顯得尤其活躍,胡適對此倍加贊賞,稱“白馬社是中國的第三文藝中心”。⑤另外兩個中心則是在中國大陸與臺灣。胡適當然不會真的將在美國發生的文學現象算作中國的文藝,而且還是中心意義上的中國文學,他在這里想要表達的意思是,白馬社是那個時代漢語新文學寫作的第三個中心,足以同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文學界并列。當他將這樣的意思表述為“白馬社是中國的第三文藝中心”時,他的心目中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明確的國體概念,而只是漢語文化和文學的另指。在較為口語化的表述中“誤”將漢語表述為“中國”,所邏輯性地顯示的是國族意識的淡泊,以及漢語分量感的加重。程國君教授將《美華文學》定義為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正體現了這樣的文化邏輯和學術感興。
這樣的邏輯與感興體現了一種學術文化趨勢:必須盡可能淡化國族文學的地域屬性而更多地強調文學語言的“文化共同體”特質,借取準當而精短的“漢語新文學”或“現代漢語文學”概括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助力,將內涵更加豐富,力量更加集中的“中國文學”因素全面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考量之中。
① 這些年我和一些學者朋友倡導“漢語文學”和“漢語新文學”概念,力圖避免對文學家身份作國際和地域的規定。顯然,高行健屬于最適合以漢語文學家稱呼的作家,甚至以耳熟能詳的“華文文學家”稱呼他都有些不倫不類。參見:《漢語新文學倡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高行健:《論創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3頁。
③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頁。
⑤ 據周策縱回憶,見王潤華:《被遺忘的五四:周策縱的海外新詩運動》,《文與哲》2007年第10期。
(責任編輯:張衛東)
A Preface to Two Recent Studies 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Macau] Zhu Shoutong
Abstract: This is a preface, written by Zhu Shoutong, to the newly published two studies, one being The Survival and Redemption of an Individual by Zhuang Yuan. As her doctoral supervisor, Zhu points out that this book provides a clear route of thinking on the mystery of value in Gao Xingjians writing and he himself also gives an excellent and unique explication of Gao Xingjians romantic‘great solitude. The other book is A Study in‘American-Chinese Literatureand Migrant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by Cheng Guojun, whose definition of‘American-Chinese Literatureas‘a Chinese literary magazine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is thought of as bringing forth the qualities of‘Chinese literatureas an object f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reflecting a sense of academic consciousness that is acute and profound. In the preface, Zhu Shoutong expresses his full confidence in and pleasure with the academic future reflected in the two concepts of‘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and‘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preface, Zhu Shoutong, Zhuang Yuan, Cheng Guo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