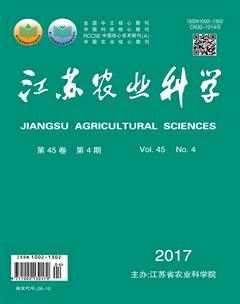我國刺鰍生物學研究進展
趙子明++劉美劍
摘要:刺鰍是一類小型經濟魚類。對大刺鰍和中華刺鰍的分類學、生理生態學、繁殖學、營養學、分子遺傳學等進行了綜述,以期為2種刺鰍的種質資源保護與開發提供系統的基礎資料。
關鍵詞:大刺鰍;中華刺鰍;生物學;研究進展
中圖分類號: S917文獻標志碼: A[HK]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04-0009-04
刺鰍屬鱸形目(Perciformes)刺鰍科(Mastacembelidae),廣泛分布于非洲、東亞及南亞地區[1],包含了刺鰍屬(Mastacembelus)和中華刺鰍屬(Sinobdella)的共65種魚類[2-3]。分布于我國的刺鰍主要有5種,包括刺鰍屬的4種,即大刺鰍、腹紋刺鰍、三葉刺鰍、云斑刺鰍[4],以及中華刺鰍屬的獨種中華刺鰍。其中,腹紋刺鰍、三葉刺鰍、云斑刺鰍僅分布于我國云南省的部分地區[4],而大刺鰍和中華刺鰍則廣泛分布,大刺鰍主要分布于長江、珠江等流域,中華刺鰍主要分布于我國東部地區。刺鰍個體較小且天然產量不高,因此其資源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刺鰍認識的不斷提高,其良好的開發價值日益體現,在觀賞魚市場尤為凸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人為活動和江河環境污染導致水體污染加重,刺鰍野生資源遭到了嚴重破壞,資源量逐年下降,開展刺鰍種質資源保護及開發利用的研究勢在必行。
1分類學
刺鰍科(Mastacembelidae)在亞科級的分類一直存在爭議。Travers將其分為東洋區Mastacembelinae亞科和古熱帶區Afromastacembelinae亞科[5],但被其他分類學家否定。而刺鰍屬魚類的分類地位已經獲得一致意見,唯有中華刺鰍的分類地位存在爭論。Travers于1984年重新劃分了刺鰍科(Mastacembelidae),將中華刺鰍歸入鰻鰍科(Chaudhuriidae)[6]。但該分類引起了Kottelat等[7-8]、Britz[9]等魚類學家的強烈反對,他們一致認為中華刺鰍屬于刺鰍科。Kottelat等通過形態學特征分析,為中華刺鰍獨立建立了中華刺鰍屬(Sinobdella)[7]。而Britz通過對中華刺鰍和其他刺鰍屬魚類的骨骼形態分析,發現了2個獨特的骨骼特征:外翼骨與后篩骨之間獨特的半月板軟骨關節;coronomeckelian骨獨有的細長形狀和后向移動位置,從而認同了前者的分類[9]。目前,國際上包括Fishbase數據庫在內普遍接受S.sinensis這一學名和分類,而國內關于中華刺鰍的爭議主要集中于種名。國內學者大都認為中華刺鰍的正式名稱為“刺鰍”,學名為Mastacembelus aculeatus,屬于刺鰍科刺鰍屬。倪勇等認同其屬于刺鰍科刺鰍屬,但認為其種名應為“中華刺鰍”,學名應為Mastacembelus sinobdella[10]。
為區分中華刺鰍屬和刺鰍屬的魚類,國內學者開展了相關研究,試圖找到形態學鑒別方法。Yang等利用體斑紋、可量與可數性狀作為區別刺鰍屬魚類的依據[4]。趙子明等認[LM]為,刺鰍的體色與體斑紋在不同年齡、不同環境下是變化的,難以作為穩定的鑒別依據[11]。學者們通過比對大刺鰍與中華刺鰍的眼下刺及前鰓蓋骨,發現了明顯區別。中華刺鰍的眼下刺在眼前下方,不十分凸出,其最后端完全達到或超過眼球,但沒有超過其眼球的中心線;大刺鰍的眼下刺明顯凸出,其最后端沒有達到眼球。同時,中華刺鰍的前鰓蓋骨周邊光滑,而大刺鰍前鰓骨的后側下方有4個明顯的爪狀尖突(刺),其中1個深入至大刺鰍的肌肉內,另外3個尖突則暴露在外側。通過這些形態差異,文獻[11]認同了中華刺鰍單獨設立中華刺鰍屬(Sinobdella)的分類。Gao等克隆獲得了中華刺鰍的線粒體基因組全場,通過與大刺鰍等刺鰍屬魚類比對,也從分子遺傳學角度確定了中華刺鰍單獨設立中華刺鰍屬(Sinobdella)的分類[12]。
2形態學
大刺鰍體形側扁而長,尾部向后逐漸變薄。頭大吻突,吻端具管狀、柔軟的吻突。眼小,上側位。體被細小,橢圓形鱗片,側線明顯、斜直[13]。背鰭基長,前部由35枚左右游離短棘組成,臀鰭具棘2枚,且連尾鰭。胸鰭短圓,無腹鰭。體背側呈灰褐色或黑褐色,腹部呈灰黃色,頭背正中多有1條黑色縱帶,頭側由吻端經眼至鰓蓋上方也有1條黑色縱帶,向后常斷裂為1條縱行黑色斑點,沿背鰭基底伸達尾鰭基底。體側有多數塊狀網紋或縱波紋[14]。大刺鰍的體長與體質量曲線回歸方程為m=0.004 94L2.831 5(r=0.972 6),冪函數指數小于3,生長情況為負異速生長,體質量增長速度隨著體長的增加而減慢[13,15]。
中華刺鰍個體體型明顯小于大刺鰍。其體細長,側扁,背腹緣低平,尾部扁薄。頭小,略側扁。吻尖突,短于眼徑。眼小,上側位,眼下方有1根硬棘。口前位,口裂斜而低,無鰓耙。身被小圓鱗,無側線。體呈黃褐色或淺褐色,體側常具多條白色垂直紋與暗色紋相間組成的柵狀橫斑。背鰭ⅩⅩⅥ~ⅩⅩⅧ,55~63;臀鰭Ⅲ為57~64;胸鰭14。椎骨75~77。體長為體高的9.7~11.8倍,頭長為吻長的3.8~4.2倍[10]。中華刺鰍雌雄個體的形態整體差異十分顯著,雄性個體明顯大于雌性個體。中華刺鰍雌雄個體的體長、體質量曲線回歸方程分別為m=0.002 5L3.090 2(r=0.896)、m=0.002 2L3.153 3(r=0.844),冪函數指數大于3,生長情況為正異速生長,體質量隨著體長的增加呈加速增長[11]。
3生理生態學
大刺鰍棲息于有石塊的江河底層或有水草的岸邊,在亂石縫隙中活動[15]。大刺鰍為溫水性魚類,適溫范圍在7~33 ℃,最適水溫為20~29 ℃[14]。池塘人工養殖條件下,水體中溶解氧含量在3.5 mg/L以上時,大刺鰍可正常攝食和生長;溶解氧含量低于2.5 mg/L時,5~6 h內大刺鰍的缺氧死亡率達90%以上。大刺鰍具有借助輔助呼吸器官進行呼吸的功能,離水狀態下只要體表和鰓部保持一定濕潤,也能存活24~36 h[16]。大刺鰍一般白天潛伏在水底,夜間到淺水區捕食。食性以動物性為主,主要食物為水生昆蟲,喜愛食物為蜉蝣目,次要食物為魚蝦、魚卵,偶爾食用植物性的食物[13,15]。大刺鰍在食物選擇上較為廣泛,較貪食,有時極為兇猛,能將較大的食物一次性完整地吞入胃中,食物組成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15]。中華刺鰍的生活習性與大刺鰍類似,主要攝食蝦類、水生昆蟲幼蟲、小魚[10]。
染色體是遺傳物質的載體,染色體變異主要表現在染色體組型特征的變異。余先覺等于1989年對桂林地區中華刺鰍進行核型分析時發現,其具有明顯的X、Y染色體分化[17]。劉江東等對湖北省武漢市和荊州市的刺鰍進行核型分析,發現2個地區的刺鰍核型完全一致,并與桂林地區刺鰍核型基本相同,中華刺鰍的染色體數2n=48,染色體核型為16 m+4 sm+2 st+26 t[18-19]。XY染色體均為中部著絲粒染色體,Y染色體約比X染色體長10%。周榮家等通過PCR擴增了中華刺鰍Y染色體上的SRY盒基因,探討了該基因在魚類中的進化保守性[20]。陳戟等通過顯微切割和兼并引物PCR方法,從雌性中華刺鰍中期染色體分裂相中分離獲得X染色體并擴增其DNA,利用T載體和電轉化方法建立了中華刺鰍X染色體DNA質粒文庫[21]。王伯平從中華刺鰍X染色體文庫分離了SSR基因位點,并對性染色體端粒進行了分析,未發現末端端粒的缺失及中間端粒現象[22]。
[JP2]此外,伍律對中華刺鰍的胰臟和胰島進行了切片觀察[23]。初慶柱等對大刺鰍消化系統進行了組織學研究[24]。[JP]
4繁殖學
大刺鰍因其體型相對較大,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因此其繁殖學的相關研究開展較早,并已取得了人工繁殖的突破[14,16,18],而中華刺鰍的相關人工繁殖研究尚未見報道。
大刺鰍產黏性卵,其性腺卵母細胞的發育不同步,屬分批多次產卵類型,產卵期為4月底至1月初,產卵高峰期在7—9月,絕對懷卵量為1 952粒,相對懷卵量為32粒/g[13]。卵巢中卵母細胞發育可分為4個時相,各時相特點與家魚卵母細胞相似[15,25]。Ⅰ、Ⅱ時相較小,Ⅲ、Ⅳ時相較大,精巢為2顆細管狀,長度為5.5~9.5 cm。體長、體質量與平均懷卵強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25.6~30.3 cm體長段的大刺鰍平均懷卵強度最高,絕對懷卵量較高[25]。大刺鰍繁殖學基礎研究的開展為人工繁殖奠定了理論基礎。通過不同催產激素配方的摸索,大刺鰍的人工繁殖在多個省份均獲得了成功;之后,大刺鰍的親魚培育、人工授精、孵化、苗種培育等技術也取得了突破[14,16,26-28]。這些繁殖學關鍵技術的突破為大刺鰍養殖和資源保護提供了重要支撐,因此大刺鰍養殖開始在江西省[14]、福建省[29]、貴州省[30]等地逐步展開。
漁業資源調查表明,中華刺鰍為1齡性成熟[JP3],絕對生殖能力為600~1 100粒/尾,產卵期為6—7月[10]。中華刺鰍個體小、經濟價值低,目前其人工繁殖研究尚未見報道,但該品種在有些地區已作為觀賞魚類小規模進入市場,主要來源于野生捕撈。韓九皋對感染小瓜蟲病的觀賞中華刺鰍進行了觀察和防治[31]。[JP]
5發育學
大刺鰍受精卵的卵裂方式與一般的硬骨魚類相似,屬于盤狀卵裂,卵裂僅在胚盤上進行。胚胎發育可分為受精卵、胚盤隆起、卵裂、囊胚、原腸胚、神經胚、器官發生、出膜等8個階段,22個時期。在水溫為(25±1)℃條件下,大刺鰍受精卵歷時65.0 h孵化出膜,所需總積溫為(1 624.5±58.12)℃·h,發育速度明顯慢于普通無磷魚[32]。大刺鰍胚胎發育過程中始終維持著較大體積的卵黃囊和油球,仔魚期體長僅為 5 mm,具[JP3]有黏性的絲狀物使身體黏附于物體上或數尾魚苗黏在一起,靠擺動尾部進行輕微運動,孵化后5~7 d內仍依靠內源性營養供給維持其生長發育[26]。5~7 d后,卵黃囊完全消失,開始主動攝食,其口裂小,主要攝食輪蟲、水蚤、水蚯蚓等[16]。[JP]
6營養學
大刺鰍肌肉中的蛋白質含量高于草魚和鯽魚,與青魚、泥鰍、鰻鱺、黃鱔等魚類均值相近,而中華刺鰍的肌肉蛋白質含量高于上述6種典型經濟魚類[33-34]。2種刺鰍的肌肉蛋白含量均高于雞蛋和豬肉[34]。大刺鰍和中華刺鰍肌肉鮮樣中脂肪含量均低于6種典型經濟魚類的平均值[33]。中華刺鰍肌肉鮮樣中蛋白質與脂肪含量均高于大刺鰍。可見,2種刺鰍均屬于高蛋白和低脂肪食品,是優質經濟魚類。2種刺鰍肌肉中均含有18種氨基酸,其中包括8種人體必需氨基酸和10種非必需氨基酸,含量最高、最低的分別是谷氨酸、胱氨酸,必需氨基酸中含量最高、最低的分別是纈氨酸、色氨酸。2種刺鰍肌肉中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總量的比值以及必需氨基酸與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均符合FAO/WHO的理想模式。2種刺鰍肌肉中4種鮮味氨基酸(天冬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的含量分別為7.14%、8.76%,均超過了青魚、泥鰍、黃鱔、草魚、鯽魚,其肌肉鮮美度較高。此外,2種刺鰍肌肉中礦物元素含量豐富,氨基酸支/芳含量也較高,可用于治療肝臟疾病[33]。大刺鰍和中華刺鰍營養豐富,極具開發利用價值。朱定貴等分別測定了生殖季節野生大刺鰍雌雄魚性腺、肝胰臟、肌肉中脂肪酸組成與含量[35-37] ∶[KG-*3]大刺鰍雌雄魚各組織中飽和脂肪酸、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分別為C16:0、C18:1n-9;多不飽和脂肪酸在雌魚各組織和雄魚肝胰臟、肌肉中含量最高的均是DHA,在精巢中含量最高的是 C22:4n-6;雌魚卵巢、肝胰臟、肌肉中,含量最高的脂肪酸分別是C18:1n-9(32.65%)、DHA(18.54%)、C18:1n-9(3499%);雄魚精巢、肝胰臟、肌肉中含量最高的脂肪酸分別是C22:4n-6(33.52%)、DHA(45.68%)、C18:1n-9(2324%)。大刺鰍親魚培育可雌雄魚分池養殖,在雌魚飼料中同時添加 C18:1n-9、DHA、ARA可促進卵巢發育,提高卵子質量;而雄魚則投喂添加DHA、C18:1n-9、ARA、C22:4n-6的飼料,可提高精子質量[35-37]。
7遺傳多樣性
分子標記和測序技術是物種研究遺傳多樣性的重要工具。國內有關大刺鰍和中華刺鰍分子遺傳學的研究正逐步展開,已經運用多種分子標記研究了不同地理群體大刺鰍和中華刺鰍的遺傳結構。王方采集我國南部地區14條水系的大刺鰍個體,進行線粒體Cyt b基因的全序列分析,分析認為14條水系的大刺鰍分屬華南和云南兩大譜系,其種群相對穩定,沒有發生明顯的種群擴張[38]。陳婷婷利用線粒體COⅠ和D-loop基因序列對14條水系的大刺鰍進行了遺傳變異分析,結果顯示,大刺鰍群體表現出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和較高的進化潛力,也分屬于華南和云南兩大譜系,種群大小保持相對的穩定[39]。楊華強等分別采用線粒體D-loop基因[40]、Cyt b基因(待發表)和ISSR標記[41]分析了福建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海南省11個地理群體262尾大刺鰍的遺傳多樣性,3種方法的結果均表明,大刺鰍總群體遺傳多樣性較豐富,不同群體間遺傳分化較大,但群體間缺乏有效的基因交流,遺傳漂變是大刺鰍群體遺傳分化的主要因素。
中華刺鰍的遺傳多樣性研究相對較少。趙子明等對江蘇省5個湖泊144尾中華刺鰍的線粒體cyt b基因和16S rDNA序列進行了比對分析,結果表明,當前中華刺鰍的資源現狀不容樂觀,亟待加強保護,5個群體的中華刺鰍遺傳多樣性及進化潛力均較低,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很弱,群體間未出現遺傳分化,存在著較大的滅絕風險[42-43]。
分子遺傳學研究表明,目前大刺鰍和中華刺鰍的種質資源不容樂觀,而相關分子研究非常薄弱,需要用更多、更有效的分子標記開展全面的種質資源分析與評估。
8展望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是維持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主要載體。在全球背景下,1個物種的消失可能會危及其他物種的生存,造成對生物多樣性的連鎖反應,最終導致物種的滅絕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大刺鰍和中華刺鰍的生活環境已經受到人為干擾和破壞,導致其野生棲息地不斷縮小,野生資源量銳減,群體結構遭到破壞,遺傳多樣性下降。對這2種刺鰍的保護需要開展更系統、更全面的基礎生物學研究。目前大刺鰍的基礎研究相對較多,而中華刺鰍的研究剛起步,繁殖學基礎知識和人工繁殖、孵化、苗種培育等技術亟待突破。保護2種刺鰍資源需要開展一系列工作。首先,通過全面的調查和監測,掌握2種刺鰍種質資源的現狀,同時利用分子標記技術系統地對遺傳多樣性、群體遺傳結構、群體間遺傳距離、群體分化時間、群體間基因流動、群體起源等進行全面評估,這也有利于更好地指導種質資源監測和保護工作。其次,建立遺傳多樣性豐富的種質資源庫,有條件的地區建立保護區。建立人工種質資源庫或原種保護基地,并將野生遺傳資源異地活體保存,這是種質資源保護最為可行的有效方法。大刺鰍已被列為福建省保護動物,其他省份也可根據當地現狀制定相應的保護措施。
參考文獻:
[1]Roberts T R.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astacembelidae or spiny eels of Burma and Thailand,with description of two new species of Macrognathus[J]. Japanese Journal of Ichthyology,1986,33(2):95-109.
[2]Rainer F,Pauly D. Species of Mastacembelus in FishBase 2012[EB/OL]. [2016-04-20]. http://www.fishbase.org/identification/SpeciesList.php?genus=Mastacembelus.
[3]Rainer F,Pauly D. “Sinobdella sinensis” in FishBase 2014[EB/OL]. [2016-04-20]. http://www.fishbase.org/summary/Sinobdella-sinensis.html.
[4]Yang L P,Zhou W. A review of the genus Mastcembelus(Percifromes,Mastcembeloidae)in China with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and [JP3]one new record[J].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2011,36(2):325-331.[JP]
[5]Travers R A. A review of the Mastacembeloidei,a suborder of synbranchiform teleost fishes,Part Ⅰ:anatomical descriptions[J].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Natural History)Zoological Series,1984,46(1):1-133.
[6]Travers R A. A review of the Mastacembeloidei,a suborder of synbranchiform teleost fishes.Part Ⅱ:Phylogenetic analysis[J].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Natural History)Zoological Series,1984,47:83-150.
[7]Kottelat M,Lim K P. Diagnosis of two new genera and three new species of earthworm eels from the Malay Peninsula Borneo(Teleostei:Chaudhuriidae)[J]. Ichthyological Exploration of Freshwaters,1994(5):181-190.
[8]Kottelat M. Notes on the taxonomy and distribution of some Western Indonesian freshwater fishes,with diagnoses of a newgenus and six new species(Pisces:Cyprinidae,Belonidae,and Chaudhuriidae)[J]. Ichthyological Exploration of Freshwaters,1991(2):273-287.
[9]Britz R. Ontogeny of ethmoidal region and hyopalatine arch in Macrognathus pancalus(Percomorpha,Mastacembeloidei),with critical remarks on mastacembeloid inter-and intrarelationships[J].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1996,3181:1-18.
[10]倪勇,伍漢霖. 江蘇魚類志[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
[11]趙子明,王加美,袁圣,等. 中華刺鰍的形態學[J]. 江蘇農業科學,2016,44(6):321-324.
[12]Gao T H,Chen D Q.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spiny eel Sinobdella sinensis (Perciformes,Mastacembelidae)[J]. Mitochondrial DNA,2016,27(5):3230-3232.
[13]溫曉紅. 汀江大刺鰍資源的保護及利用[J]. 中國水產,2005,38(10):72-73.
[14]曾慶祥,方園,曾學平,等. 大刺鰍的生物學特性與人工繁養殖技術[J]. 中國水產,2016,50(3):70-73.
[15]黃永春. 汀江大刺鰍食性和繁殖生物學[J]. 水產學報,1999,23(增刊1):1-6.
[16]陳忠. 大刺鰍的生物學及其養殖技術概要[J]. 中國水產,2005,39(10):22-24.
[17]余先覺,周暾,李渝成,等. 中國淡水魚類染色體[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18][JP3]劉江東,黃琳,余其興,等. 刺鰍性染色體的細胞遺傳學確定證據[J]. 武漢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9,45(2):185-190.[JP]
[19]劉江東. 刺鰍性染色體的顯微分離和X涂繪文庫的研究[D]. 武漢:武漢大學,2003.
[20]周榮家,余其興,程漢華,等. PCR擴增黃鱔和刺鰍SRY盒基因[J]. 科學通報,1996,41(7):640-642.
[21]陳戟,趙剛,臧亞婷,等. 刺鰍X染色體DNA文庫的構建[J]. 水生生物學報,2009,33(4):571-576.
[22]王伯平. 刺鰍和擬緣([XCZ75.tif;%88%88])的微衛星DNA及性染色體研究[D]. 武漢:武漢大學,2013.
[23]伍律. 刺鰍的胰臟和胰島析[J]. 水生生物學集刊,1956(2):272-278.
[24]初慶柱,陳剛,張健東,等. 大刺鰍消化系統的組織學研究[J]. 淡水漁業,2009,39(2):14-18.
[25]劉霆,李建光,賀兵,等. 大刺鰍的性腺調查和懷卵量比較分析[J]. 淡水漁業,2005,35(5):28-30.
[26]李曉雙. 大刺鰍人工繁殖研究初報[J]. 中國水產,2007,41(5):44-46.
[27]張建銘,曾慶祥,劉斌,等. 大刺鰍人工繁殖技術初探[J]. 中國水產,2015,49(9):85-86.
[28]陳方平,李林春,查廣才,等. 大刺鰍催產效率與積溫的相關性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2015,43(19):116-117.
[29]賴誠明. 大刺鰍人工馴養初報[J]. 漁業致富指南,2007,20(16):52-53.
[30]馬文理. 大刺鰍池塘馴養技術試驗初探[J]. 農民致富之友,2012,25(24):86,135.
[31]韓九皋. 刺鰍感染小瓜蟲病及防治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2007,35(16):4826,4834.
[32]薛凌展. 大刺鰍胚胎發育觀察[J]. 淡水漁業,2014,44(2):101-104,108.
[33]伍遠安,梁志強,李傳武,等. 兩種刺鰍肌肉營養成分分析及評價[J]. 營養學報,2010,32(5):499-502.
[34]楊月欣,王光亞,潘興昌. 中國食物成分表2002[M]. 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2.
[35]朱定貴,陳濤. 大刺鰍生殖季節雌魚的脂肪酸組成研究[J]. 廣東農業科學,2011,38(16):108-110.
[36]朱定貴,陳濤. 大刺鰍生殖季節雄魚的脂肪酸組成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2011,39(30):18675-18677.
[37]朱定貴. 生殖季節野生大刺鰍雌雄魚脂肪酸組成研究[J]. 中國農學通報,2012,28(2):65-68.
[38]王方. 中國南部地區大刺鰍種群遺傳和親緣地理研究[D]. 廣州:華南師范大學,2012.
[39]陳婷婷. 基于CO[QX(Y15]Ⅰ[QX)]和D-loop基因對中國南部地區大刺鰍種群變異與親緣地理的研究[D]. 廣州:華南師范大學,2014.
[40]楊華強,李強,侯麗萍,等. 華南及臨近地區大刺鰍遺傳多樣性分析[C]. 2014年中國水產學會學術年會論文摘要集,2014.
[41]楊華強,李強,舒琥,等. 華南及臨近地區大刺鰍遺傳多樣性分析的ISSR分析[J]. 水生生物學報,2016,40(1):63-70.
[42]趙子明,陳小江,杜迎春,等. 五個湖泊中華刺鰍種群遺傳多樣性分析[J]. 水產科學,2015,34(12):789-794.
[43]趙子明,葉建生,劉美劍,等. 五個湖泊中華刺鰍種群線粒體細胞色素b遺傳多樣性分析[J]. 湖泊科學,2016,28(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