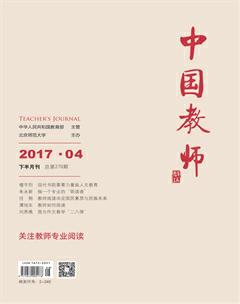句分長短,別樣風流
昌盛
詞,這一文學藝術(shù),興起于隋唐,發(fā)展于五代,在兩宋時期達到巔峰,其發(fā)展與當時的社會、音樂和文學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詞受音樂和近體詩律的雙重影響,故有“長短句”“詩余”“曲子詞”“曲詞”等名稱。
不同詞牌的詞,在篇幅、結(jié)構(gòu)、句型和用韻上皆不同,以清簡抑或繁復的語言、工整抑或多變的句式、拗怒抑或流婉的音節(jié),獲得強大的結(jié)構(gòu)張力和豐富的表現(xiàn)形式,和古風、律詩的美感特質(zhì),相異甚殊。詞更適宜于表達自由靈巧、細膩深微、復雜而個性化的情思,給了學生另一重創(chuàng)作空間。
“天生是詞人”
“現(xiàn)在的學生,天生是詞人。”在一次聊天時,王強老師如是說,又跟了一句:“根本寫不出古體或律體的感覺。”我當時不禁啞然,而后細想,確有這樣的現(xiàn)象:一些學生作的詩,句法或立意都乏善可陳,但換作填詞,卻總有幾句靈動可愛,這種現(xiàn)象暫且看作“易得佳句”。還有些學生并不通詩律,卻能憑著模仿作出詞來,暫且看作“無師自通”。這兩種現(xiàn)象成因不同,前者是因我們離詞很近,后者是因我們離詞很遠。
先說這“遠”,缺乏詞律常識的學生,以為詞的平仄和用韻很隨意,把填詞看作寫新詩一樣的自由創(chuàng)作,于是挑個詞牌,隨便定個韻,加點傳統(tǒng)的意象進去,就以為完成了。這就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再說這“近”。沒有什么比《虞美人》一氣呵成的九字句更能體現(xiàn)李煜的家國之愁,沒有什么比《如夢令》的格式更適合李清照對“知否”的強調(diào)。同樣,陸游那“錯、錯、錯”的嘆惋,也無法安置于絕句中。可見,這被喚作“長短句”的詞,正以豐富的句式,成為最貼近內(nèi)心的抒情載體。而今,亦然。
字數(shù)上,學生因靈感而吟得佳句,此句或為二三字,抑或四字、六字,此時句子的內(nèi)容、情感和字數(shù),彼此最為自然和諧。倘若強性拗成齊言體式的律詩,這自然與和諧就會被削弱;格律上,不同于近體詩,許多詞牌是押仄韻和平仄韻交押的,對仗方面的要求較低,這符合不少人的偏好;內(nèi)容上,詞可以比詩更加寬泛,貼近學生的生活。
古風和律詩多體現(xiàn)儒士文化精神,常以運典、諷喻、托物、借景的手法,表達民生多艱、羈旅鄉(xiāng)愁、懷才不遇等主題。中學生沒有去國懷鄉(xiāng)、躬耕田園的體驗,缺少許多作舊詩的原材料,但多少有些對光陰流逝的悵惘、小別親朋的憂傷,容易被自然風物所觸動。我們產(chǎn)生詩興的動機,有時并非一種情懷,而是具體的情感,甚至只是一點小的情緒。填詞,其實很適合記錄中學生那些平凡而細微的生命感受。
“遠”的誤會也好,“近”的默契也罷,總之學生與詞有緣。
學以成其道
詞,即樂曲的曲詞。隋唐時期,燕樂作為新的樂曲系統(tǒng)形成并蓬勃發(fā)展,其節(jié)奏、旋律多樣,時人為這燕樂所配的曲詞,在形式上不同于古風、律詩。譬如,樂曲《浪淘沙》是要重復一遍旋律的雙調(diào),反映在曲詞上就是形式相同的上下兩片。一首詞多少字、多少韻、如何押、平仄如何變化,由樂曲的長短、緩急、高低等決定。所以,詞是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
最早的詞譜,其實是音譜,后來很多音樂失傳,學者便收集前人的作品,歸納出每種詞牌的格律形態(tài),編訂為我們現(xiàn)在所使用的詞譜。講清詞的音樂性后,只需教學生認讀詞譜中平仄、押韻、換韻的標記,再要求其按譜填詞、依《詞林正韻》擇韻即可。
詞的修辭技法非常豐富,對仗與領(lǐng)字需要重點講解。詞的對仗形式多樣,如鼎足對(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扇面對(水風輕、頻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等。對仗時常不避重字,甚至刻意用重字,如“人”字對(一霎兒晴、一霎兒雨、一霎兒風)、“工”字對(桃花紅、李花白、菜花黃)、“丫”字對(汴水流、泗水流)。運用好對仗技法,可使詞作更顯連綿多姿、流麗生動。
詞的領(lǐng)字,譬如“更能消、幾番風雨”“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念橋邊紅藥”,具有起振全篇的爆發(fā)力、涵括多句的包容力,更在音韻節(jié)奏上有搖筋轉(zhuǎn)骨之美。填長調(diào)時,須格外關(guān)注領(lǐng)字的聲、情與力。
詞作的篇幅會對內(nèi)容和情感的表達,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篇幅增加,內(nèi)容也須跟著豐富,典故的運用、繁筆的鋪排,也就成為客觀需要。同時,詞作的情感,也應復雜曲折些。反過來,字數(shù)越少,越要凝集筆力,以突出事物特點。所以,小令往往語言精練,抒情直徹。不同詞體的美學特征,也就各異:小令貴清簡靈巧,中調(diào)講究和緩勻齊,長調(diào)以深沉跌宕為尚。
詞的每一片要保證獨立、完整,且與上下片不失關(guān)聯(lián)。所以過片時,意脈上要似斷仍續(xù),呈水窮云起之美。填詞時,也要關(guān)注起結(jié)的手法,使情、景、事、理高度融合,追求含蓄深婉、回味無窮。
由是可見,填詞不能照搬作詩的思路與經(jīng)驗。但作詩、填詞都要保持興趣與閱讀量,以古為師,法眾取上。
我的課叫作“詞作賞填”。“賞”什么?我將隋唐至近代的傳世名篇做成讀本發(fā)給學生,再把學生的“賞”細分為三步:一為通覽,把握詞作的整體藝術(shù)風貌;二為精研,閱讀自己最鐘愛的詞人的整本詞集,以快速形成填詞的語感與風格;三為泛讀,跳出偏好,欣賞不同題材、體裁和風格的詞作,開闊眼界,豐富技法,最終沉淀為自己的寫作特色。當然,“賞”還包括對同伴習作的研討。我常挑出較為典型的學生作品,作為正面或反面教材,在課上與學生共同分析。
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
填詞的過程可分兩類:極具天分的人,胸有成篇,參照詞律一氣呵成;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則非如此。人們往往因某些感發(fā)生成一兩佳句,這是本詞天成的部分,不妨聚焦于此,千錘萬煉,再根據(jù)字數(shù)、格律和韻腳,確定詞牌,最后豐實全篇。這是“胸有成意—后有成句—繼而成闕—最后成篇”的創(chuàng)作路徑。
修改詞作比填詞更難,也更提升功力。處理詞作的方法有三:熱處理(趁熱打鐵,解決格律、情理、邏輯上的不諧之處)、溫處理(繼而與人分享,獲得客觀反饋)、冷處理(暫且擱置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瑕疵,待閱讀量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增加后再做反觀,以開茅塞)。
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不足,會導致作品原本追求的美感反入雷池。譬如:追求內(nèi)容和角度的“新”,反成材料和表達的“生”;追求語言和手法的“奇”,反使作品讀起來“怪”;追求情感表達的“真”,反因鋪墊不足或情景未融而顯得“直”;追求語言曉暢“平”易,反因內(nèi)容單調(diào)而顯得“白”;追求色彩之“麗”,反成遣詞之“俗”;追求意象之“濃”,反成堆砌之“密”;追求意境之“淡”,反成意象空乏的“疏”。不妨記住這些關(guān)鍵詞,用以自評。
別樣的課堂
詞是樂曲的歌詞,這是中學師生皆知的常識。但如果學生只會填詞卻不會唱,那么詞在聲韻和句式方面的魅力,就都被架空了。
我的課堂倡導音樂的回歸。我會用箏來彈唱宋詞,也會為詞作重新度曲,帶著學生體驗詞樂相融的美感。同時,我會把倚聲填詞和唱詞的基本規(guī)則講給學生,于是所收到的作業(yè),不僅有狹義上的詞作,還有學生自己創(chuàng)作及演唱的詞樂,甚至為流行樂曲重新填寫的歌詞。音樂的加入,不是創(chuàng)新,而是正道的回歸,豐富了詞作的美感,更能給學生以更深刻的創(chuàng)作體驗。
比起作詩,填詞更像是一門鼓勵多角度描敘生活細節(jié)、關(guān)注“微思考”“小情緒”的藝術(shù)。作詩沒有“大志向”,則缺少風骨,但填詞往往要尊重人的“小情緒”,判斷詞作品質(zhì)的未必是情感的境界大小,還可以是真摯動人的程度。所以,一首詞只要不是無病呻吟,而是言之有物,哪怕是在寫生活的細節(jié),也能打動人心,成為好詞。
北京一場雨后,“雙虹”驚艷全城,我戲作《十六字令》詠之:
十六字令 虹
虹。
青黃表里白為宗。
晴光斷,
空色兩相同。
學生也紛紛填起詞來:
荷葉杯 虹
張亦晨
雨打珠簾輕凈, 虹影,滿春庭。
畫樓如洗闥如染,云淡,彩光凝。
荷葉杯 虹
許鈺晨
一晌破空初見,迎面,色三重。
二心風雨雨將短,天晚,暮光濃。
十六字令 虹
韓庚達
虹。
彩夢流光幾色重。
東風起,
旖旎卻成空。
當元曲、新詩等后繼而起,當詞所依托的音樂發(fā)生缺位,當如今的語言環(huán)境使填詞愈發(fā)艱難,當自己的嘔心之作難覓知音……外部環(huán)境變了,我們或許再努力也到達不了宋人的高峰,那么我們還能不能填詞、要不要填詞?我想,這是學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它的答案會催生當代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感和使命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使命,學生若能成為古典底蘊、世界眼光、現(xiàn)代精神共同熔鑄的詞人,便成為了古典詩詞之道的肉身。今人以填詞來陶養(yǎng)性靈的過程,其實也是詞自身演進的過程。既然詞得到了傳承和演進,那它將是永不老去的文學生命。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教師,主講填詞部分)
責任編輯:孫建輝
sunjh@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