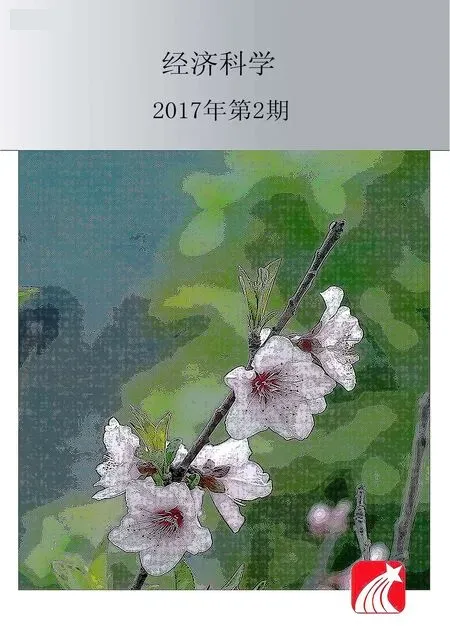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非線性特征*
——基于PSTR模型的實證研究
孫海波 焦翠紅 林秀梅
(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 吉林長春 130012)
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非線性特征*
——基于PSTR模型的實證研究
孫海波 焦翠紅 林秀梅
(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 吉林長春 130012)
本文構建面板平滑轉換模型,運用我國2003—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不僅支持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U”型關系的存在,還表明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經濟發展水平的門限效應。當前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省份已進入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影響階段,而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尚未跨越經濟發展水平的臨界值,人力資本集聚并不利于這些省份產業結構改善。進一步,為克服由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雙向因果關系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構建聯立方程模型重新進行檢驗,發現所得結果與面板平滑轉換模型結果相一致,表明本文結論具有很好的穩健性。
人力資本集聚 產業結構升級 非線性特征 PSTR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發生深刻變革,主要表現為農業增加值比重逐漸下降,工業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不斷攀升。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仍面臨嚴峻挑戰,集中體現為產業發展質量低下、發展方式粗放,以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2014年,全國層面來看,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2.7%,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8.1%,雖然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過70%;分地區層面來看,東部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8.81%,中西部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0.27%。可見,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差異明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人力資本集聚因素。如今,中國經濟發展迅猛,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人力資本集聚現象越來越明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人力資本水平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王小魯等,2004)。為此,有必要針對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關系進行深入研究,這不僅可以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理論依據,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伴隨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有關人力資本集聚的研究逐漸展開并取得豐碩成果。Fujita和Thisse(2003)依托新經濟地理學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闡釋了人力資本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Alessandra和Philip(2009)指出,人力資本集聚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Rauch(1993)通過對美國大城市調查數據分析,發現人力資本聚集對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具有明顯促進作用。Glaeser和Resseger(2010)的研究也證實這一點,認為地區勞動生產率與人力資本集聚呈正相關關系。張海峰(2016)考察了人力資本集聚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力資本集聚有利于區域創新績效的提升。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討論了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Joshua和Edward(2012)研究認為,人力資本集聚與來自私人部門的創新溢出對產業發展具有積極影響。焦勇(2015)利用2003—2012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認為人力資本集聚可以推動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許慶明等(2015)將中國長三角地區人口集聚程度和產業結構狀況與日本、韓國進行對比,發現提升長三角地區人口集聚程度能夠加快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陶長琪和周璇(2016)研究表明,省域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
總體來看,現有研究都強調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線性影響,事實上,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并非簡單地表現為線性的正向或者負向作用,兩者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特征,然而當前文獻對此并未涉及。于是,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已有文獻做出有益的補充:第一,不同于已有研究中所采用的線性回歸技術,本文利用面板平滑遷移(PSTR)模型對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非線性特征進行識別,PSTR模型不僅能夠較為細致地刻畫模型回歸系數在截面上的異質性,而且模型回歸系數還可以實現在不同區制間平滑轉換,能夠很好地捕捉變量之間的非線性特征。第二,考慮到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可能帶來內生性問題,本文設定有效的聯立方程模型以克服內生性問題帶來的影響,增強研究結論的可信度。第三,鑒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進一步探討了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區域差異,以期更加深入地把握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取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人力資本集聚不僅可以降低知識傳播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進而改善地區產業結構(Glaeser,1999)。人力資本集聚程度高的地區,高學歷人口密度大,方便知識共享產生新思想,充分滿足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同時,Vollrath(2009)研究發現,人力資本錯配嚴重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于人力資本離散區而言,人才流失嚴重,無法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對高水平人力資本的需求,也就導致人力資本離散區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產業結構調整乏力,成為制約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因素之一(王金營,2013)。以上分析表明,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可能同時存在正效應和負效應的雙重影響。為清晰展示二者關系,我們利用我國2003—2013年分地區人力資本集聚程度與產業結構水平數據繪制出散點圖(圖1)。據此,我們提出假說1:
假說1: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呈U型關系。

圖1 人力資本集聚程度與產業結構水平的散點圖
隨著經濟發展,大量高層次人力資本向城市集聚,尤其是一些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李海崢等,2013)。陳得文和苗建軍(2012)采用空間過濾模型消除人力資本空間相關性影響后,發現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人力資本集聚效應最明顯。Curran和Blackburn(1994)也指出,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將導致人力資本流失。從中國現實經濟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例如,2014年,北京、天津和上海人均GDP已超過9.5萬元(當年價),而甘肅、貴州和云南仍不足3萬元,如此大的地區差異必然會對人力資本流動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人力資本集聚效應的發揮。Barro等(1992)的研究強調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相互匹配的重要性,只有二者匹配協調才能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積極的影響。若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缺少生產所需的先進機器、必要設備等重要的物質資本,即使有大量人力資本集聚于此,也難以實現經濟大步前進,那么合理的產業結構也就無從談起(魏下海和張建武,1999)。可以看出,人力資本集聚效應的發揮會受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約束,在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人力資本集聚表現出明顯的比較優勢。而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人力資本擁有量基礎薄弱導致產業技術水平難以短期內提升。因此,我們提出假說2:
假說2: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經濟發展水平門限效應。
三、研究方法
對于檢驗變量之間非線性關系是否依賴于某一個變量(門限變量),最原始的方法是人為主觀地確定門限值,然后根據門限值將樣本分為兩組或者多組,最后對每組樣本進行參數估計。可是這種做法不僅在門限值選取上具有很大的隨機性,而且也沒有對門限值進行參數估計和顯著性檢驗,存在著嚴重缺陷,得到的估計結果也不具有穩健性。Hansen(1999)借助嚴格的統計推斷方法對門限值進行假設檢驗與參數估計,提出面板門限回歸(PTR)模型,很好地克服了上述方法存在的缺陷。單門限模型形式可簡潔地表示為:

其中,I(·)代表指示性函數,當括號內條件表達式成立,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如果存在多個門限值,可在上式基礎上進行擴展。然而,大多經濟環境下兩種區制之間的轉換是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Hansen(1999)提出的門限回歸模型,在門限值兩側轉換是跳躍式的,無法實現平滑轉換。González等(2005)通過放松面板門限回歸模型中的一些限制條件,并引入一個連續變化的轉換函數,提出PSTR模型,從而實現模型在高、低兩種區制之間平滑變換,避免PTR模型中的突變現象,使面板門限回歸模型更加一般化。
(一)PSTR模型介紹
本文主要介紹兩區制PSTR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i=1,2…,N代表樣本個數,t=1,2…,T代表時間;yit與xit分別表示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向量;αi表示個體效應;εit代表零均值同方差的隨機干擾項;β0和β1表示解釋變量系數;g(qit;γ,c)是以可觀測變量qit為轉換變量的連續有界函數。
已有研究多將g(qit;γ,c)設定為Logistic函數,具體表達式如下:

其中,c=(c1,c2,…,cm)表示位置參數,且c1≤c2≤…≤cm;m代表位置參數的維度;γ>0表示平滑參數,其值的大小直接影響到g(qit;γ,c)平滑轉換速度。González等(2005)以及Colletaz和Hurlin(2006)的研究表明一般m取1或2足以滿足解決問題的需要。為了更加清晰地觀察轉換函數的變換過程,我們分別模擬平滑參數γ取0.1、0.5、1和5四種不同值時,g(qit;γ,c)的圖像。其中,位置參數只進行簡便取值,m=1所對應的c=0,m=2所對應的c1=-1,c2=1,具體模擬結果如圖2和圖3所示。

圖2 m=1;c=0

圖3 m=2;c1=-1,c2=1
從模擬結果中可以看出,當γ取值較小時,g(qit;γ,c)可以實現平滑轉換;當γ取值過大時,g(qit;γ,c)轉換速度較快,在轉換點附近圖像變得更加陡峭。據Logistic函數的性質可知g(qit;γ,c)的取值范圍在0到1之間,在轉換函數的兩個端點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β1和β1+β2。接下來,我們分析m不同取值時,PSTR模型的詳細情況:
1、m=1,表明位置參數只有一個維度。
2、m=2,表明位置參數有兩個維度。
(二)PSTR模型的線性與非線性殘余檢驗
線性檢驗是對原假設H0:γ=0的檢驗。為有效彌補相關參數未識別對模型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將g(qit;γ,c)在γ=0處利用一階泰勒展開進行處理,構造輔助回歸方程。針對檢驗原假設是否成立,González等構造了相關統計量進行檢驗,具體如下:

其中,SSR0與SSR1分別表示原假設下殘差平方和與備擇假設下殘差平方和。2006年Colletaz和Hurlin又提出pseudo-LTR統計量,豐富了模型檢驗方法,具體形式為:

如果拒絕線性原假設,則說明模型存在非線性轉換機制,即r≥1。進而,需要繼續檢驗非線性部分的個數,直至接受原假設,獲得最終的r值。
四、變量說明與模型構建
(一)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水平
產業結構升級不僅意味整體產業效率的提升,生產要素逐漸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也暗含產業內部技術結構的升級,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從而實現經濟效率不斷提升。伴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服務化趨勢日益突顯,服務業將成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走向(羅富政和羅能生,2016)。為此,本文參考閆文娟等(2012)的做法,采用第三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水平。
2、核心釋變量:人力資本集聚
本文參考陳得文和苗建軍(2012)的測算方法,采用大專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數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并借助區位熵來考察我國不同地區的人力資本集聚程度。

式中,HAi表示i地區人力資本集聚程度;HCi表示i地區人力資本水平;THC表示全國人力資本總水平;Pi表示i地區人口數;P表示全國總人口數。HAi數值越大,說明該地區的人力資本集聚程度越高。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對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產生一定影響,導致人力資本分布格局發生改變,為了清晰地展示這種變化,本文分別給出2003—2008和2009—2013兩個時間段內人力資本集聚程度核密度分布圖(圖4和圖5)。

圖4 2003—2008年HA核密度分布圖

圖5 2009—2013年HA核密度分布圖
圖4可以看出,2003年地區人力資本集聚程度核密度分布圖峰幅窄、峰值高,并且呈現出不對稱的雙峰特征。其原因可能是受到1999年我國普通高校本專科院校擴招政策的影響,2003年本專科畢業人數增多,對地區人力資本集聚產生一定沖擊,從而出現雙峰特征。到2005年以后,峰值有所回落,且寬峰特征顯著。此外,核密度分布圖呈現出明顯的拖尾現象。說明這一時期內,地區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差異明顯,有極化的發展趨勢。圖5顯示,2009年到2013年,單峰特征明顯、峰值逐漸回升并且峰寬收窄。其原因可能是,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東部地區就業壓力加大,而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潛力相對凸顯,導致部分勞動力從東部地區回流到中西部地區,使得人力資本分布不均衡問題有所緩解。
3、轉換變量: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各地區人均GDP衡量,并利用各地區人均GDP指數進行平減,換算成2003年為基期的人均GDP。
4、其他控制變量:基礎設施,參考汪偉等(2015)的方法,用各地區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來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各地區城鎮人口數比年末總人口數衡量;對外開放程度,用各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比值表示,其中進出口貿易總額利用各年人民幣匯率(年平均價)進行調整;投資率,參照魏下海和張建武(2010)的做法,用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來表示。政府財政支出,沿用陳得文和苗建軍(2012)的方法,用政府財政支出與GDP之比來測度。出生率,采用一年內一地區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數的比率表示。
以上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由于西藏部分數據缺失,故不將其納入樣本范圍,本文選取2003—2013年30個省市(區)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并對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
(二)模型構建
為捕捉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非線性影響,在上文分析基礎上,我們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STRit代表產業結構水平,HAit代表人力資本集聚程度,X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qit代表轉換變量。隨著轉換函數g(qit;γ,c)在0到1之間變化,模型(8)實現了從低區制到高區制的平滑轉換。進一步,可以推導出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

式(9)可以看出,當β21<0時,(β11+β21)<eit<β11,表明伴隨模型從低區制向高區制轉變,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降低;當β21>0時,β11<eit<(β11+β21),意味著模型從低區制向高區制轉變,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增加。可見,eit的實際值是β11與加權變換后β21的加總。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模型檢驗
避免出現虛假回歸,我們對所有變量進行LLC檢驗,結果顯示全部變量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為此,可以直接利用這些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在對PSTR模型進行參數估計之前,需要計算LM、LMF和LRT統計量對模型進行線性與非線性殘余檢驗。本文PSTR模型的相關檢驗與估計結果均通過Matlab2010b軟件實現。表1給出以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轉換變量時,不同位置參數維度下的PSTR模型線性與非線性殘余檢驗結果。

表1 線性與非線性殘余檢驗結果
從表1的結果可以看出,在m=1與m=2兩種情況下,LM、LMF和LRT統計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H0:r=0。表明本文所選用的面板數據具有明顯的異質性,也就是說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驗證了本文計量模型設定的合理性。進一步,對PSTR模型非線性殘余檢驗,結果顯示,m=1與m=2時都不能拒絕原假設H0:r=1。說明PSTR模型只含有一個非線性轉換函數,即r=1。在接受模型只含有一個轉換函數后,需要確定位置參數的維度。我們采用AIC和BIC準則來確定最佳m取值。當m=1時,兩個轉換變量所對應的AIC值和BIC值均小于m=2時的值。據此,可以得出模型最佳轉換函數個數和位置參數維度組合為r=1,m=1。表2給出PSTR模型具體的參數估計結果。

表2 PSTR模型估計結果
表2結果顯示,位置參數的估計值為10.399,對應的人均GDP為3.283萬元(2003年價格),在位置參數兩側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當人均GDP低于3.283萬元,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為-0.065,并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表現出負效應;當人均GDP達到門限值時,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變為0.089(-0.065+0.309×0.5);當人均GDP高于3.283萬元,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效應逐漸顯現,影響系數最終穩定在0.244(-0.065+0.309)。具體而言,經濟發達地區收入水平相對較高,工作環境和基礎設施等條件優越,誘使人力資本向這些地區集聚,有助于經濟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焦勇,2015)。而落后地區人才流失嚴重,人力資本配置不合理,無法滿足產業升級對專業化勞動力的需求,嚴重阻礙產業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李天健和侯景新,2015)。在雙重因素的作用下,人力資本集聚勢必會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非線性影響。此外,結合表2中平滑參數估計結果與圖6的轉換函數圖形可以看出,轉換函數漸進式變化,說明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實現了在不同區制間平滑轉換。圖7給出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系數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散點圖。從中可以看出,伴隨轉換變量的增大,eit由負值逐漸轉變為正值。當eit<0,說明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抑制作用,但隨經濟不斷發展這種抑制作用趨弱;當eit>0,說明人力資本聚集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并且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增強。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產業結構水平隨著人力資本集聚程度加大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走勢,表現出明顯的“U”型特征,并且這種“U”型反轉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圖6 轉換函數圖

圖7 eit與轉換變量散點圖
從模型控制變量估計結果來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門限值以內時,基礎設施估計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當經濟發展水平越過門限值后,基礎設施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基礎設施建設的促進效應逐漸消失,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結構改善將沒有任何幫助。城市化水平與對外開放程度的估計結果相同,線性部分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而非線性部分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只有在經濟發達的情況下,城市化建設與對外開放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才能突顯。當模型處于低區制時,投資率、政府財政支出和出生率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模型進入高區制后,抑制作用轉變為促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物質資本投資和政府財政支出的促進作用具有時滯性,初期的大量物質資本投資與政府支出并不會產生明顯效果,隨時間推移逐漸表現出促進作用。出生率表現顯著為負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紅利時期過高的出生率對經濟發展造成一定壓力,但近年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老齡化現象嚴重,而新生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老齡化,起到改善勞動力年齡結構的作用,所以出生率與產業結構升級又表現出正相關。
(二)穩健性檢驗
以上本文利用PSTR模型驗證了我國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具有非線性特征。不過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人力資本集聚有利于地區創新能力的提升,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同時,產業層次水平較高的地區在吸引人力資本方面又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種雙向因果關系容易引發內生性問題,從而影響估計結果的準確性。為此,我們構建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集聚的聯立方程模型以解決內生性問題。
1、產業結構方程
在產業結構方程中,被解釋變量仍是產業結構水平,核心解釋變量為人力資本集聚程度,控制變量為基礎設施、城市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投資率、政府財政支出、出生率,各變量的度量與前文相同。為檢驗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本文引入四個二元虛擬變量D1、D2、D3、D4,這四個虛擬變量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來設定的。具體而言,將經濟發展水平按照由低到高排序的四分位數為臨界點,當經濟發展水平處于最小值到上四分位數的范圍時,D1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D2、D3、D4依此類推。據此,HA×D1表示低經濟發展水平的處理組,HA×D2和HA×D3分別對應中低和中高經濟發展水平的處理組,HA×D4表示高經濟發展水平的處理組,根據HA×D1、HA×D2、HA×D3和HA×D4的估計系數來判斷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
2、人力資本集聚方程
在人力資本集聚方程中,主要從以下幾四個方面選取影響人力資本集聚的變量。第一、經濟活力程度,本文使用產業結構水平衡量經濟活力程度,并將其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如果一個地區擁有較高級的產業結構,那么該地區的經濟更具活力,自然會吸引大量人力資本;第二、社會發展水平,一方面,收入水平無疑是影響人力資本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各地區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來源中的工薪收入衡量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從工作穩定性的角度考慮,城市就業形勢也會影響到人們是否在該城市工作,用各地區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來反映;第三、環境因素,如今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人們在選擇工作和居住城市時也開始考慮環境問題,為此,我們將環境因素作為一個控制變量引入到模型中,本文以工業廢氣排放總量來衡量地區環境狀況;第四,科教資源,通過科教投入也可以反映出一個地區對人才的重視程度,分別以R&D經費內部支出占GDP比重和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教育統計年鑒》。
結合產業結構方程和人力資本集聚方程,得到一個聯立方程模型。此外,我們還控制了年份效應和地區效應,具體形式為:

式(10)中,Yr代表年份效應,Provn代表地區效應,X和Y分別表示除核心解釋變量之外的其他控制變量,ε1和ε2表示隨機干擾項,其他變量含義同前文。
選擇合適的估計方法對聯立方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由于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相互影響,所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或者廣義最小二乘法(GLS)對聯立方程中的每個方程進行估計并不是最有效的。而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通過將似不相關回歸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相結合,能夠同時處理系統中各方程的內生性問題和誤差項之間的相關性問題,得到的估計結果更為有效。據此,本文選用3SLS對聯立方程(10)進行估計,具體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為了進行對比,表3中給出未控制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產業結構方程還是人力資本集聚方程,在控制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之后R2均增大,說明模型的解釋能力有所提高。因此,本文重點關注控制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的估計結果。從表3中1b的結果可以看出,人力資本集聚*D1項的估計系數為-0.145,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當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時,人力資本集聚未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反而表現為抑制作用;人力資本集聚*D2項與人力資本集聚*D3項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06和0.072,二者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是因為經濟發展處于中等水平時,人力資本流入和流出相對頻繁,導致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總體作用效果并不明顯;人力資本集聚*D4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人力資本會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綜上可知,伴隨經濟發展水平由低到高,人力資本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由負向轉為正向,與PSTR模型估計結果相一致。
(三)區域差異分析
根據PSTR模型估計得到的門限值,我們按照2006年、2010年和2013年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門限值的大小關系,將樣本劃分為低區間(低于門限值)和高區間(大于等于門限值)兩個部分,具體劃分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2006年,僅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個省份位于高區間,其余省份全部位于低區間;2010年,遼寧、江蘇、福建、山東和廣東這些沿海省份進入高區間;到2013年,吉林與黑龍江兩個省份也進入高區間。由此可見,除海南省之外,東部地區其他省份均已越過經濟發展水平門限值,分布在“U”型右側的上行區,人資資本集聚可以加速這些省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仍受經濟發展水平約束,集中在“U”型左側的下行區,致使人力資本集聚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無法發揮。
六、結論
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轉換模型,以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限變量,檢驗了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在此基礎上,為消除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雙向因果關系的影響,我們構建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聯立方程模型重新檢驗。最后,考慮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又進行區域差異分析。綜合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結論:(1)人力資本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表現出明顯的“U”特征,并且二者之間存在連續平滑轉換機制。(2)聯立方程模型估計結果顯示,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時,人力資本集聚并不利于本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當地區經濟發展進入高水平階段后,人力資本集聚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表現出明顯地推動作用。與面板平滑轉換模型結果一致,保證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3)從地區差異分析來看,目前人力資本集聚對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中西部大部分省份仍處于“U”型左側的下行區,受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人力資本集聚并不利于這些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基于實證研究結論,我們認為通過人力資本集聚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行之有效途徑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充分釋放人力資本集聚紅利,助推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同時,東部地區繼續發揮沿海城市和經濟特區的先導作用,帶動其他地區產業結構轉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后,嚴重阻礙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為此,中西部地區要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合理完善現有生產力布局,確定重點發展產業和戰略產業,通過產業轉移對接,引進與自身資源稟賦關聯度大、產業鏈長的投資項目,盡快跨越經濟發展水平門檻。此外,還要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尤其在人才引進方面,要完善人才激勵和服務保障體系,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為人才引進提供基本保障。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要繼續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引導人才向中西部地區流動。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區域差異之大,人力資本分布不均衡。因此,要著力解決人力資本空間分布不平等的問題。一方面,協調好省際間教育資源投入,尤其是加大中西部的一些偏遠地區基礎教育投入;另一方面,要確保各地區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促使人力資本分布結構合理化。
1.陳得文、苗建軍:《人力資本集聚、空間溢出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空間過濾模型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
2.焦勇:《生產要素地理集聚會影響產業結構變遷嗎》[J],《統計研究》2015年第8期。
3.李海崢、賈娜、張曉蓓、BarbaraF:《中國人力資本的區域分布及發展動態》[J],《經濟研究》2013第7期。
4.羅富政、羅能生:《稅收負擔如何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基于稅負層次和規模的討論》[J],《產業經濟研究》2016年第1期。
5.李天健、侯景新:《中國人力資本的空間集聚與分布差異》[J],《世界經濟文匯》2015年第3期。
6.陶長琪、周璇:《要素集聚下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非線性和溢出效應研究》[J],《當代財經》2016年第1期。
7.王金營:《區域人力資本積聚和開發機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8.汪偉、劉玉飛、彭冬冬:《人口老齡化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11期。
9.魏下海、張建武:《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門檻效應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0年第5期。
10.王小魯、樊綱:《中國地區差距的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J],《經濟研究》2004年第1期。
11.許慶明、胡晨光、劉道學:《城市群人口集聚梯度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國長三角地區與日本、韓國的比較》[J],《中國人口科學》2015年第1期。
12.閆文娟、郭樹龍、史亞東:《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效應:線性還是非線性?》[J],《經濟科學》2012年第6期。
13.張海峰:《人力資本集聚與區域創新績效——基于浙江的實證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
14.A lessandra,F.,and Philip,M.,2009,“Universities,Agglomerations and Graduate Human Capital Mobility.”[J],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vol.100,pp 210-223.
15.Barro,R.J.,and Sala-i-Martin,X.,1992,“Public Finance in mMdels of Econom ic Grow 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59,pp645-661.
16.Colletaz,G.,and Hurlin,C.,2006,“Threshold Effects of the Public Capital Productivity:An International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Approach.”[R],LEO Working PaperNo.1.
17.Curran,J.,and Blackburn,R.,1994,“Small Firms and Local Economic Networks.”Paul Chapman.
18.Fujita,M.,and Thisse,J.F.,2003,“Dose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 th?and Who Lose From It.”[J],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vol.54,pp121-145.
19.Glaeser,E.L.,and Resseger,M.G.,2010,“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Skill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50,pp221-244.
20.Glaeser,E.L.,1999,“Learning in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46,pp254-277.
21.González,A.,Ter?svirta,T.,and Dijk,D.,2005,“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R],Working Paper,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2.Hansen,B.E.,1999,“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N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93,pp345-368.
23.Joshua,D.,and Edward,F.,2012,“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 ies:An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in Thre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gionalScienceandUrban Economics,vol.42,pp1-14.
24.Rauch,J.E.,1993,“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Evidence from the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34,pp380-400.
25.Vollrath,D.,2009,“How Important are Dual Economy Effects for Aggregate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8,pp325-334.
(H)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編號:15ZDA01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編號:71373101)、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研究計劃(編號:2016050)、新結構經濟學專項研究基金的階段性成果。作者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