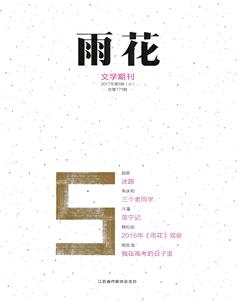青年,如何完成現時代的文學使命?
參加者:
何 平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劉大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
金 理 復旦大學中文系
何同彬 《鐘山》雜志社
韓松剛 江蘇省作家協會
沈杏培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時間:
2017年3月21日16點—18點
地點:
南京師范大學仙林校區敬文圖書館西報告廳
整理:
李 涵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何 平:我們可以自由一點,就像一次開放的文學討論課,說的是向迅和龐羽,但可以延伸到我們時代的青年寫作。我已經不算是青年批評家了,今天是江蘇省作家協會和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基地共同舉辦的“江蘇文學新秀雙月談”第一場,我在這兒是串場和陪襯。首先我們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劉大先談談。
劉大先:何老師說他不是青年,那我們就先來談談“青年”。很多人對“青年”存在著一些偏見,一般會認為青年就是指“80后”“90后”,而一說到青年文學就會聯想到韓寒、郭敬明,但其實并不是這么回事。我們都知道代際劃分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概念。我們談論青年文學的時候就不能把它狹隘化。
其實,向迅的出生地,我在2008-2011年去做過田野調查,與人類學比較接近的調查,對象是少數民族和漢族雜居的地區文化,這些地方的風景非常好。但我發現向迅的作品中卻很少涉及這些,那他的作品寫的是什么呢?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是基于鄉村記憶和個人成長經驗構造的個人家族史。他所有文學作品的背后實際上都在寫他自己,沒有那種“民族風情”,更側重于內心的展現。事實上,那種內心的東西特別不好寫,同樣也不好評。
畢竟散文不同于小說,詩文無定法。散文在中國整個文學脈絡當中定位是非常高的,除了詩歌就是散文,只不過現在經過了西方文學理論、現代散文觀念演變歷程的“沖刷”后將其簡單化了。而對于向迅的散文,你沒法給他找到一個固定的闡釋規律。他只是非常真實地在袒露個人的經驗以及這種經驗所生發出的感受和思考。雖然這個思考不一定是成熟的,但是他敏銳地抓住了在他家鄉生活中積淀出的普遍而真實的命題——經濟迅速發展,鄉村共同體迅速瓦解。這個瓦解不僅僅在生活方式、經濟生產方式、謀生手段,也在于經濟結構。向迅就是對于力圖抓住我們時代根本性命題有著非常強烈欲求的作家。
此時我想轉到另外一個話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50后60后所設立的話語體系已經逐漸成型并且成為一種話語壟斷。而80后90后新一代的作家中,有沒有這種潛能,能夠突破以前的話語體系?在向迅、龐羽這里,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跡象。
讀龐羽的小說,我能夠感受到一種超出她生理年齡的成熟感。她有一種野心,試圖通過用不同的手段創作出自己的語言。小說中的眾多構成要素很多都不是她個人經驗的直接產物,而是她想象出來的。這實際上是文學寫作的一個動力,也是文學寫作的能力所在,即是說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是作家親身經歷的,但是通過作家的想象力能夠給予它一個賦形。
何 平:剛才劉大先開了一個好頭,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即何為“青年”?“青年”在我們的時代如何寫作?我們不能根據年齡就籠統來說——向迅、龐羽和下面在座的是青年,我們不能按照簡單的生理年齡標準來衡量所謂的青年,大先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賦形”。他講到向迅的家族史怎么來的,作品呈現出的又是怎樣的,也包括龐羽對于她所面對的世界是如何處理的,她不是僅僅去寫自己所熟悉的能體驗到的那個世界,而是通過想象力拓展了書寫空間。所以說劉大先肯定年輕人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在給本科生上課的時候談到“文學是不是生活所必需的”這樣一個命題。在這種情況下,兩位青年作家還是選擇了文學來表達他們的認知和體驗。向迅是把他自己放在整個家族中間,必然要面對家族與生俱來的甜蜜與不幸,變化以及那樣一種災難與懷念,以此拼命地打撈家族記憶,打撈不再繁華的集市和街道。而龐羽,她刻畫了許多小人物的失敗史,這樣一種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如果龐羽不寫,她小說當中呈現的小人物在我們今天這樣一種時代里就會是沉默者。下面我們有請復旦大學中文系金理談談他的看法。
金 理:對龐羽的創作,我有一個簡單的觀感。第一,龐羽的語言非常好,基礎非常牢固。她應該有比較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會在小說中融入一些古典詩詞,而且不著痕跡。這在同齡作家里是出類拔萃的。其次,在她筆下有非常多的人物登場。我跟我們學校的同學交流,發現他們有這樣一個印象——青年文學都是比較同質化的文學。龐羽作品中有很多的人物,但她也一直在觀察在探索,這是她不一樣的地方。
在今天這樣一個場合我們可以更加真誠地討論文學,所以接下來我想談談龐羽寫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龐羽的小說有一個特征——很務實。她是高度理性化和高度現實主義的作家。而龐羽有非常強烈的征服性和擴張性,她要求小說去偵測生活真相的方方面面,去穿透人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有時候藝術既要密不透風,但也要有一些“留白”。所以對于龐羽的小說,我期待能有一些留白之處。就像《福祿壽》,作家在她筆下的人物面前,權威性以及控制欲太搶眼了。小說的精神是復雜的,每個小說都告訴讀者,世界遠比你想象得要復雜得多。我非常希望這些人物身上有沒有被作家言語、被目前小說所呈現的那種隱秘性。在這個角落中,人物可以去安放他化解生活當中糾纏如麻的瑣事的能力,人物可以去散發他面對生活當中絕望時的智慧和勇氣。這樣一種角落和留白在龐羽小說當中要少一些。那么理性和控制欲有時候是不是也會帶給讀者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呢?
何 平:金理所說的也是我想到的。而且他談論問題的舒緩沉靜是特別適合談文學的節奏,特別讓人沉迷。我理想中的談文學就是應該在這樣的語言節奏和氛圍下,讓你不知不覺沉醉其中。
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擁有書寫的權力,但如何控制住自己、不要讓自己在書寫過程中濫用權力是很重要的。而如今的批評家,面對作家寫作出現的問題應果斷澄清,這是一個批評家以一種協商和對話的方式與作家進行的交流。同彬在青年批評家里面,也是以犀利著稱,請他來談談。
何同彬:我對當下青年人的寫作方式、語言、發展形態都自己一定的態度。先說說龐羽。龐羽她還太年輕,因此她的作品仍然能看得出她處于青春寫作向成熟寫作的過渡階段。她的每一次嘗試幾乎都能透出她的稟賦來,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即她這個年齡和程度把握不了的書寫節奏,包括抒情的節奏。當然這對于一個90后的青年作家來講是很難避免的。從她整個作品的美學風貌來看,她是一個有很強個人性、女性氣質的作家,通過經營某種空間以及細描心理現象生發出一些孤獨感和消極情緒。我從來不會否認女性寫作者有更強烈的女性身份特征,因為相對于男性,女性有著不可替代的經驗,包括童年記憶、成長經驗、人事人情,這些都透露出作為一個女性所特有的那種敏銳。但問題在于,我們已經知道更早的作家像張悅然、張怡微等,基本上把女性寫作者能夠寫到的形態都涉及到了,所以對于龐羽來說,她未來的創作挑戰還是很大的:你如何把自己特有的東西呈現出來?
剛才我們說到龐羽小說的小敘事,到了向迅這里,是一個人間的小敘事,里面都有很強的個人性。所以就跟龐羽所面臨的挑戰一樣,即向迅又如何在一個龐大的“鄉愁”書寫傳統中突出自己的獨特性?他現在還沒有逃離目前的寫作方式,而要實現這種獨特性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我期待他在未來的寫作中能夠有所突破。
除此之外,現在我們的青年都活得太“正確”了,青年作家也是這樣,在這樣一個文學已經邊緣化的時代中,如果還是按照原有的軌道去寫,你怎樣完成你對于這個時代的使命?
何 平:何同彬對青年寫作提出了很高的期待,他的要求特別高,就是要做文學史上的、文學傳統中的有突破的作家。接著請韓松剛來談談。
韓松剛:剛才幾位老師主要從內容方面談了兩位青年作家的創作,下面我主要從形式方面談一點自己對于向迅散文寫作的看法。
五四時期的散文重思想和精神,更加強調散文的意義和趣味,并從這個層面上發展出了一重一輕兩個維度:以魯迅為代表的“重”的向度和以周作人為代表的“輕”的向度,重,重量、沉重;輕,輕靈、輕松。向迅的散文創作基本上是沿著“重”的路子走下去的。他的散文《誰還能衣錦還鄉》《消逝的原野》《失敗者的畫像》《大地悲歌》《最后的村莊》等等,無不流露出作者對于家鄉的沉重思考和深沉憂慮,而《鄉村安魂曲》《卡斯布羅集市》等長篇散文,更是在個人情感、現實世界的基礎上增添了歷史的籌碼,由此深具個人感、現實感和歷史感等多重意味。
散文的抒情應該是有節制的。不克制的抒情產生的是放縱的快感,但難以形成深沉的思想魅力,而克制的抒情,卻往往能夠傳達出巨大的情感力量。向迅散文集《斯卡布羅集市》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其長篇散文的寫作中,這種對于敘事和抒情的掌控表現得十分突出。他在散文集《誰還能衣錦還鄉》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的縱橫捭闔,到這里開始慢慢地收斂,這是向迅挑戰有難度的寫作的結果,也是他“遲到的覺醒”。向迅的這種平衡主要得益于小說,尤其是小說的敘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德語課》、赫塔·米勒的《低地》、多麗絲·萊辛的《幸存者回憶錄》等等,都對向迅的散文寫作產生過震動和影響。向迅也在嘗試著把敘事和議論有機地融入到散文的現實呈現和個人抒情中,盡管我還不能說向迅的散文是可以當小說來讀的,但是很明顯,向迅的散文有著一種“小說化”的趨勢,和一種屬于他自己的敘事腔調。在《鄉村安魂曲》和《卡斯布羅集市》這兩部長篇散文中,向迅表現出了一種以小見大的氣象,他之前對于細節處理的弱化在這里得到了強化,他所表現的世界不再僅僅是個人的、家族,抑或社會的現實種種,而是有了一種闊達的生命氣象和哲學思考,他正在突破大部分散文所聚焦的哀傷氣息和挽歌情節,試圖達至一種更為深沉的悲劇層面和藝術境界。我覺得這是當下散文寫作十分缺乏的一種書寫氣度和氣勢。
賈平凹說:“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像火,一般人不敢到跟前去,散文倒像是水,多溫柔呀,誰都想去游一下,但可能就把你淹死了。”我不知道向迅會不會游泳,但他肯定是沒被淹死,也希望他以后可以游得更好,寫出更精彩的作品。
何 平:在今天散文是一個比較活躍的文體。像向迅這樣一種家族史式的寫作方式在新世紀也是特別流行的一類散文。家族史用散文這種文體來處理,如果沒有豐沛的材料話就變成了無病呻吟。像龐羽,她是寫小說的,小說可以更飛揚跋扈一點。下面我們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沈杏培老師談談他怎么看龐羽的小說。
沈杏培:龐羽,包括很多90后的作家,他們的起點、寫作的內容往往是從自己個人經驗比如說童年、成長、校園青春主題生發。但是90后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的青春寫作周期非常短,很快就從“寫青春”的主題跳到其他主題上去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反抗或者說是逃離前輩寫作框架的需要。其次,她的作品多是關于生存困境的敘事。核心即人的孤獨和生命的殘忍。像《福祿壽》,這部作品把我們整個一生都看透了。一個教授老年喪妻,下身癱瘓,坐在輪椅上。他的兒子在美國請元嫂幫他,結果元嫂的老公去偷他的獎,她的女兒誘惑教授,想覬覦他的家產。教授發現這一家的陰謀后把元嫂開除。小說突出的是那種老無所依和孤獨的處境。她這種寫作還是有根基的。當下社會是一個改革深化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龐羽的小說,可能會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證詞。
我再簡單說一下我的幾點建議。第一點,龐羽的創作手法可以多元一點。比如說留白。留白不僅是中國傳統的一種手法,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略薩也提到這一點。他認為福克納的小說充滿意味深長的沉默,并將這一手法稱為“隱藏的材料”。而龐羽小說中的每一個結局都會處理得很“實”。第二點,龐羽可以盡量遠離或者跟文壇保持相對距離,在相對孤寂中完成自己。當代文壇是一個大染缸,不要太看重這些所謂批評家的意見,很多說法對你沒有什么作用,只會傷害你的積極性,包括我講的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沒有什么用的。
何 平:杏培老師提到的“青年作家如何與批評家進行對話”的問題值得討論,但因為時間關系,我們還是回到主題上來。如今很少有機會批評家能夠與作家進行面對面的直接的對話,而我們今天的研討會就設置了這樣一個環節。下面我們就給兩個作家一個機會,讓他們談談,在聽完了剛才幾位青年批評家對他們作品的看法之后,他們又有什么樣的感受。
龐 羽:非常感謝有機會能夠在這個春天的下午跟大家坐在一起談文學。先從我小時候說起吧,我父母告訴我,我第一次學會走路是從床上突然爬下來,跌跌撞撞沖出去,這個速度對于我當時而言是非常快的。同樣的,我覺得一個作家在剛開始創作的時候亦是帶有這種很快的速度。我是2013年真正開始小說創作,至今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而到現在,我仍然覺得作家走向成熟的一個方式就是必須要學會優雅地走路。
寫作的伊始是從讀書開始。某天我在父親書櫥里發現了一本書,這本書是用白皮包著的,這上面寫了兩個字——“活著”。我花費了整個星期六下午通過翻閱新華字典看完了這本書。后來我接觸了《變形記》,再后來我遇到了美國作家奧康納,我覺得他們都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之后我還看了《釋迦牟尼故事集》,非常感謝這些書在我生命當中的出場順序,它們對于我的寫作都有著或顯或隱的影響。我在2009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之后到2013年都沒有發表過,這段時間我非常痛苦同時也非常充實。在南大我選修了化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那時候有非常強烈的學習愿望,想把它們全部“拖”回來、據為己有。有些時候我們做一些事并不是為了雕塑自己,而是為了連接,后來我就寫出了《真草千字文》,這算是我小說的開始。作為小說家,要學會成為一座橋梁,人們從黑暗中經過這座橋,也許對面也是黑暗,但是卻向光明更近了一步,我們需要背負文學到達堤岸。我喜歡利落的語言。從小時候看書開始,我就養成了必須記筆記的習慣,見到好句子就會揣進口袋里。
作為90后作家我才剛剛起步。剛才劉老師說,青年文學家不能狹隘,要向大的方向看齊;金老師說小說要有留白,要張弛有度;何老師提到我們要沖破知識的界限;韓老師指出任何文體都有界限;沈老師說要運用各種創作手法……我受益匪淺,我現在全部據為己有,好好消化,不辜負各位老師的期待。寫作就像是越過高墻,這需要很強的創作力。而我現在試圖各條路都走一遍,失敗了也不要緊,因為還年輕、還有體力去撞南墻,走錯了不是浪費時間,而是鍛煉了角力與方向感。我非常希望能憑借自己的力量越過生活的高墻,畢竟對于寫作來講,每一道光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向 迅:我重點談一下突破創作瓶頸的問題。兩三年前,我感覺到自己步入了一個創作瓶頸期。寫作過程中時常陷入沼澤、舉步維艱,同時也時常感到焦慮、沮喪。每每這時,我就會通過讀書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新的苦惱也隨之而來。我的內心會涌現如是的想法:既然已經有那么多經典作品,自身再如何努力也無法超越,那為什么還要超越呢?雖然如此,但還是能夠激起創作沖動。
其次我再談一下我對于創作這件事情的感受。中國正走向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期,整個民族都處在迷茫、困惑、成熟、掙扎、奮斗、巨大的輪回中,形容為史詩般的時代,一點都不過分。我們沒有看到作家反映這巨大變革時代的努力,之前我對這個觀點很贊同,但是后來我在一個研討會上聽到一個人的發言,改變了我的一些看法。他提到,我們就應該在時代敘事的基礎上,尋找一個更大的可能性,這給了我十分豐富的啟迪。作為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變革下的寫作者,確實會遇到很多困惑,尤其是在文學的影響和地位日漸上升的前提下。但是我覺得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生活如何變化、形勢如何多樣化,我們評判一部文學時,總有一條是不變的,那就是能否打動人心、引起共鳴。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如何讓作品依然能夠看到大時代的車輪,如何在車輪滾動中看到尚未離去的煙塵,如何成為一個有個性的作者,如何對碎片化生活進行整體的表達?這應該是我們值得思考的事情,謝謝大家。??
何 平:時間不早了。感謝在座的青年作家和批評家,感謝各位同學,我們一起擁有的這個“文學”的午后一定會成為大家的美好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