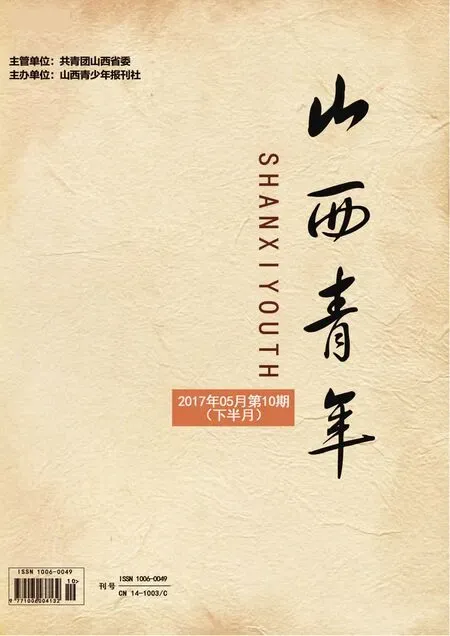論“同情感”與貧窮的存在*
周文君
江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
?
論“同情感”與貧窮的存在*
周文君*
江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
透過斯密《道德情操論》[1]中的“同情感”解讀并理解貧窮的現存狀態,進而發現“同情感”中的貧窮所引發的社會傾向性行為。這種具有傾向性的社會行為經過“同情感”的加工,以及人類想象力的發揮和日積月累的實踐,向往富足的生活成為人類的普適愿望,而已實現者成為貧窮者的模仿對象。這些社會行為也逐漸被內化為人們道德判斷的標準,進而影響對感情合宜程度的“同情感”。
“同情感”;貧窮;貧窮狀態;社會行為;道德選擇
正如人們對“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這一命題的討論,盡管人們抗拒貧窮的存在,但貧窮依舊存在,無法完全消除,因為在大多數時候貧窮是一種相對狀態。因此,每個社會都無法完全拒絕貧窮的存在。
一、“同情感”中的貧窮狀態
斯密的同情感是中性的,是指一個人或幾個人對另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處境能夠表示理解,并懷有同樣的情感,即雙方能夠在情感上同感共鳴。因此,這里的同情感可指各種情感上的互通。在斯密看來,行為的合宜與否,與個人選擇行為的原因和所傾向的結果分不開(斯密,15)。那么,當一個人的貧窮是由于社會轉型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原因或者其它非可控因素導致的,尤其是群體性的貧困,此時,引發合宜性的同情感的對象或是原因是合適的、得體的;但當一個人的貧窮狀態是自我選擇的結果,而自身本是有能力改變的,卻選擇流浪、乞討,此時,由這種情景產生的貧窮狀態的性質是相反的,行為是不合宜的,由此產生的同情感與前者是相反的。
談及處境的順逆對個人行為合宜與否的影響,斯密認為一般地,對悲傷的同情感比對快樂的同情感更為強烈,但人們更容易完全“同情”喜悅,對悲傷的同情感往往不如當事人自身的感受更加深切(斯密,50-58)。而自己的感受會通過感受陌生人、朋友等人的情感來調節自我感受,就如同庫利的“鏡中我”。因此,當感受到他者對處于貧窮狀態的自我存在懷疑、忽視甚至蔑視,以及感受到他者對處境優渥者的羨慕、尊敬和禮遇,人們往往傾向于展現自身美好快樂的一面,并試圖隱藏自己窮困潦倒的一面。
從斯密“同情感”的角度看待貧窮狀態:(1)貧窮的存在是被世人拒絕的。道義上,世人應該對貧窮者的存在表示憐憫和同情,從應然性出發不應該歧視。但實際上貧窮的存在為各個民族、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世界所急迫之問題,貧窮是一種問題狀態,應該被解決。(2)貧窮的存在是恥辱的、愧疚的,它是一種行為選擇,而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中,新教倫理的世俗化使得新教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某種具有時代意義和發展意義的契合,主張為上帝而努力進取、創造財富、勤儉節約,來證明自己是被上帝接受的。但新教精神要求“禁欲”,要求世人能夠保持節儉的生活方式,即人們可以選擇“貧窮的生活方式”。因此,貧窮是一種過程,一種行為選擇,而不是結果。(3)貧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狀態表現。這并不代表對消除世界貧困毫無信心,此處的“貧困”是一種相對性的表達,正如窮人與富人這一對相反的詞語,有富貴,就有貧窮。
二、“同情感”中的貧窮與社會行為
因貧窮而產生的同情感在以風格迥異的方式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尤其在能夠滿足基本的溫飽需求后,個體因貧窮產生的不滿感不是源自身體上的不適,而是源自精神上的不適。而源自精神上的不適很多時候會因為人類自身想象功能的發揮得到體現和反應(斯密,32-36),此外,源自想象的情感及其同情感比源自身體的情感及其同情感更強烈。因此,由想象貧窮帶來的各種變化將會使貧困者的感受像放大鏡一樣被放大。
“同情感”通過想象力的發揮,將原本的喜悅和悲傷程度得到擴大。事實上,一方面,無論貧窮富貴者,他們所用的生活必需品是固定的,但是由財富所帶來的精神滿足感在貧窮者的想象力下得到放大,并且富貴者自身也考慮到這樣的感覺。因此,人類向往富足,擺脫貧窮。這樣的心理導向引導著人類進步和成長,無疑是具有積極傾向性。另一方面,人類更加容易附和和“同情”富足者,并將其處境想象成是最為完美的幸福狀態,由此,其生活選擇也會向富者看齊,時尚被富貴者引導,富者的生活方式和時尚選擇也成為貧窮者的關注點。
此外,斯密認為人們會希望通過他人的情感與我們的是否相合來評價他人的情感合宜與否,同時認為“一個對他自己的不幸沒有什么感覺的人,對他人的不幸,必定總是更沒有什么感覺,因此更不會想要減輕他人的不幸”(斯密,310),這與傳統地利他主義者的觀點恰恰相反,但更符合人性的特征。試想,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不幸福無所察覺,反而先關注他者或眾者的幸福與否,此為邏輯不通。如無法或沒有能力覺察自身的各種變化,又如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能夠為他者考慮。
三、“同情感”中的貧窮與道德選擇
基于“同情感”對貧窮狀態的影響和“同情感”中的貧窮所體現出來的行為表現,貧窮可以成為個體在通往富足過程中的一個動態變化,但不能成為一種永久不變的靜止狀態,保持貧窮的靜止狀態等于承認自己愿意屈于貧窮,而這被人們認為是甘于墮落,為人們所不恥。當人們努力追求更富足的生活,那么,富足者的生活狀態將會成為相對貧窮者的模仿對象,進而影響我們的美丑觀,這種“能力”也逐漸演變為一種權力選擇。同時,這種權力是福柯所闡述的“微觀權力”,是一種被內化了的價值觀和社會習慣。以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出發,這種固化的社會習慣和時尚觀并不是后現代主義所追求的,后現代主義認為社會處于一種重構的狀態,社會需要新的建構以適應社會的諸多變化。
斯密認為真正的博愛是神之工作,盡管力量薄弱的個人無法做到施惠于眾人,但個人有能力為他自己、家人、朋友和國家的幸福而努力。但過度關注自我,過于歧視貧窮和強求富貴,或者陷于財富的欲望怪圈中,個體也會失去人性美的光輝,扭曲自我價值的標準,進而成為一臺“自我的機器”(見圖一)。

圖一
[1]亞當·斯密[英].道德情操論[M].謝宗林,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610295016)。
G
A
1006-0049-(2017)10-0053-01
**作者簡介:周文君(1996-),女,漢族,河南正陽人,江南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專業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