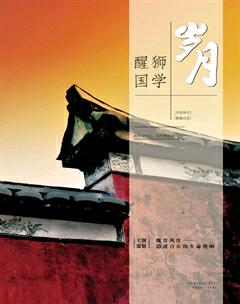生命的完滿
大化于胸,與物為春,天地間還是一個有情的宇宙。在中國人看來,宇宙不是一個冷漠的時空存在,不是一個無情的物理世界,它是生命的鼓動,是情趣的流蕩,是嚴整的秩序,是圓滿的和諧。宇宙存在對于中國人總是具有一種親切感、家園感,這就是中國人的宇宙情懷,也就是莊子的美學襟懷。在莊子這里,人生最高境界是個審美境界。因此,李澤厚指出:“從所謂宇宙觀、認識論去說明理解莊子,不如從美學上才能真正把握莊子哲學的整體實質。”
莊子從人間狀態的考察建立自己的美學。說起來,人世間就是一個名利場,陷在這個名利場中,大家活的都很累。莊子為此又講了一個寓言。說是一個人和自己的影子較勁,他拼命地奔跑,想甩掉自己的影子,但是不管他跑的多快,也不管他跑到哪里,他的影子總是跟著他,怎么也甩不掉。到了最后,他就累死了。莊子啟發他說,和影子較什么勁呢?你只消到那棵大樹下的陰涼地兒休息休息,影子不就沒了嗎?
我們在名利場上的很多較勁,其實都是和虛幻的影子較勁,就像《金剛經》所說:“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回頭一看,不過是過眼云煙。我們不應忘記,紅塵滾滾中,還有一個別樣的世界,那就是莊子指點的大樹下面的綠蔭,那是一個清涼的世界,美的世界。
桃花亂落如紅雨
美的王國,有自己的一套法律,有自己的一套游戲規則。
人們面對任何一個對象,都可能從三個角度來看,都可能形成三種態度。我們拿桃花來做例子。春風蕩漾中,桃花盛開,絢爛如火。一個人走過來看到盛開的桃花,他腦袋里就浮現出這樣一些念頭:這桃花是草本呢,還是木本?當他腦袋里出現這些念頭的時候,他對桃花采取的就是科學態度,植物學的態度,概念的、分析的。另一個人走過來看到桃花,他想不到桃花是草本還是木本,他想的是,這桃花今年的市場行情怎么樣,當這個人腦袋里出現這些念頭時,他對桃花采取的就是商業態度,也就是功利態度。第三個人過來了,他本來就是春游踏青,尋花覓柳。猛然間,如火的桃花綻放在眼前,他的眼前一亮,心中一顫,桃花的形象打動了他,桃花的香氣滋潤了他。他的全副身心都感到震顫,他的整個靈魂都和桃花融為一體。這個人可能是唐朝詩人劉禹錫,他看到桃花,腦袋里就出現一首詞,他寫的: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科學態度是一種理性的分析,實用態度是一種利害的盤算。審美態度既跳出了理性的分析,又跳出了利害的盤算,它就將自己的全部情感都投射到桃花的形象中,它就用自己的整個靈魂來擁抱這桃花,“桃花亂落如紅雨”,剎那間獲得一種心靈的了悟、情感的陶醉。這種了悟和陶醉,就像喝酒喝的微醉微醺,美學家把它叫作審美體驗。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種審美體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只要你能跳出喧囂不堪的現實世界,哪怕是偷得浮生半日閑,你都會領略到審美的快樂。
就在這審美體驗中,我們的人生獲得了最深刻的啟悟,最踏實的安頓,最愜意的享受,這樣我們就進入了審美境界。
那么,這個審美境界對于人生,意義何在呢?我們中國人把它看成人生的最高境界。審美的境界為什么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德國思想家弗洛姆談到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時說:“他終日所想的只是這類問題:怎樣才能爬上去?怎樣才能掙更多的錢?至于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人,他是從來想不到的。”
金錢也好,地位也好,說到底都是生存的手段。人整天全都陷到里面,就是把手段當成了目的,忘記了弗洛姆說的“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人?”
因此,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在人來人往的雅典大街上東尋西找,有人問他:“你在找什么?”他竟回答說:“我在找人。”
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找人,這個哲學故事告訴我們,盡管滿大街熙熙攘攘都是人,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已經“成為一個人”?
那么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人?換一個問法,就是人怎樣活著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才能夠實現生命的豐富和尊嚴?鄧麗君唱的《小城故事》用七個字就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人生境界真善美。真的世界引導我們求知,善的世界引導我們向善,美的世界,才是安頓我們生命的世界。莊子為我們指點的,就是一個美的世界。
經聲佛號,喚回世上名利客;晨鐘暮鼓,驚醒人間夢里人。
莊子的智慧只能點到為止但我還是想用莊子解夢來結束莊子智慧的討論。莊子在《齊物論》中說,一個蠢人正做著夢,但不知道身在夢中,在夢中又做起夢來了。醒來才知道是做了夢中夢。但另一個聰明人知道,蠢人的所謂醒來,其實也還是在做夢,而聰明人一個勁地說蠢人做夢、做夢、做夢,哪里知道他自己其實也是在說夢話。話說莊子這一夢,就夢到了禪宗。佛家說,佛本來不做夢,但為了普渡眾生,不得不進到眾生的夢中。眾生在未成佛前,都是在做夢,但卻像莊子說的那個夢里人一樣不自覺。
對于佛來說,夢就像鏡花水月,是根本不存在的虛空世界;但對眾生來說,做夢卻不知是夢,還執著地以為那是真實的世界。因此很多寺廟上都刻著這樣的對聯:“莊子的解夢和佛家的解夢何其相似?莊子說道在屎溺,宇宙的大道竟然在屎尿里,這話也總是讓人想起禪家的機鋒。因此有人說莊禪一家,甚至有人說莊子是中國第一位大和尚。《莊子》書中虛擬了一篇孔子和學生顏回的對話:
顏回曰:“回益矣。”
(譯:顏回說:“我進步了。”)
仲尼問:“何謂也?”
(譯:孔子問:“怎樣進步了呢?”)
曰:“回忘禮樂矣。”
(譯:顏回答:“我忘掉禮樂了。”)
曰:“可矣,猶未也。”
(譯:孔子說:“很好,但是還不夠。”)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譯:過了幾天,顏回又見孔子,說“我進步了。”)
曰:“何謂也?”
(譯:孔子問:“怎么進步了呢?”)
曰:“回忘仁義矣。”
(譯:顏回答:“我忘掉仁義了。”)
曰:“可矣,猶未也。”
(譯:孔子說:“很好,但是還不夠。”)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譯:過了幾天,顏回又見孔子,說“我進步了。”)
曰:“何謂也?”
(譯:孔子問:“怎么進步了呢?”)
曰:“回坐忘矣。”
(譯:顏回答:“我坐忘了。”)
仲尼踧然曰:“何謂坐忘?”
(譯:孔子驚奇地問:“什么叫坐忘?”)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
(譯:顏回答:“遺忘了自己的肢體,拋開了自己的聰明,離棄了本體忘掉了智識。和大道融通為一,這就是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
(譯:孔子說:“和萬物同一就沒有偏私了,參與萬物的變化就沒有偏執了,你果真進入了賢人的境界啊!我愿意追隨在你的身后。”)
這篇對話中,莊子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坐忘”,就是忘掉一切文化智識,甚至連自己的存在都要忘掉,這樣就進入與萬物為一的境界。這個境界,正是佛家追求的境界。佛家講真諦俗諦,認萬物為“有”是俗諦,認萬物為“無”,是真諦,也是要在否定中接近真如。佛家這個否定,也就是莊子“坐忘”達到的境界。適如馮友蘭所說:“一切都否定了,包括否定這個‘否定一切,就可以達到莊子哲學中相同的境界,就是忘了一切,連這個‘忘了一切也忘了。這種狀態,莊子稱之為‘坐忘,佛家稱之為‘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