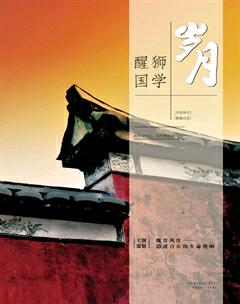物莫能兩大
公士或
不少人感嘆:秦國好運,連出幾代明君;魏公子倒霉,碰上了魏安釐王這樣的昏君。殊不知,真正的癥結在于,信陵君選擇的救國之道——賢公子輔政的運作模式,違背了中央集權制的基本規律。換言之,這條路的盡頭本來就不通向富國強兵,只是看起來很光鮮而已。
賢公子輔政模式的關鍵在于,招攬天下士人,然后在諸侯中贏得聲譽,再借此資本執掌國政并結交盟國。
這與春秋卿大夫的貴族政治有幾分相似。兩者都有封邑與龐大的私家勢力。但不同的是,春秋卿大夫生活在諸侯分封制政體中,而賢公子面對的是(不同版本的)中央集權制政體。盡管賢公子輔政有很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但本質上只是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變招,而非分封制貴族政治的延續。這使得賢公子最終依然受到王權的強力控制。
光從實用的角度說,賢公子對內利于團結社會各界力量,對外與列國交涉也更為暢通。尤其是那種朝廷不便直接出面的事情,賢公子的數千門客可謂一把利器。此外,賢公子辦事主要靠私人門客,也不太依賴國家經費。朝廷省錢省力,財政負擔相對較小。
當然,這是以賢公子忠君愛國為前提的。
賢公子輔政的首創者是孟嘗君。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是齊國丞相。孟嘗君為了讓家族地位穩固,于是廣招門客。養門客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把門客養到上千規模時,由量變引發質變,進化為國內外影響力巨大的賢公子。例如,齊湣王猜忌孟嘗君時,他的門客馮驩先游說秦王帶厚禮聘請孟嘗君為相,后又勸諫齊湣王不要被秦國挖墻腳。經過一番巧妙運作,齊湣王不但恢復了孟嘗君的丞相職位,還增加了千戶食邑。
此事充分反映了賢公子門客的活動能力,也暴露出一個隱患——假如馮驩只做第一步的話,孟嘗君和他的三千門客就會加入秦國。事實證明,這個不安因素對齊國的衰弱影響巨大。
秦五大夫呂禮逃亡到齊國,一度被齊湣王任命為相。齊湣王做這個決定是因為要與秦國結盟。與呂禮不合的蘇代,說動孟嘗君破壞這個計劃。于是呂禮與孟嘗君交惡。
為了排擠呂禮,孟嘗君竟然寫信建議秦相魏冉攻打齊國。他的邏輯是:呂禮促成秦齊聯盟后,魏冉的地位就下降了(其實蘇代也是用這個思路說服孟嘗君的),想保住權勢,就說服秦王攻齊,破壞呂禮的計劃。孟嘗君曾率領齊魏韓三國聯軍攻秦,迫使秦國割地求和。這次他卻為了一己之力引秦攻齊。結果,魏冉真的攻齊,呂禮離開齊國,孟嘗君的權勢穩固了,但齊國利益受損。
再后來,孟嘗君與齊湣王翻臉。他跑到魏國做了丞相,并參與了樂毅的合縱攻齊行動。齊國被五國聯軍打殘,從此一蹶不振。齊襄王復國后,孟嘗君憑借自己的薛邑封地保持中立,不屬于任何諸侯。
這,便是賢公子輔政演變的最壞結果。
信陵君不同于孟嘗君。他是真愛國者。雖然做過竊取虎符擅自殺將等逾矩之事,但歸根結底也是為了魏國抗秦大業著想。所以,他始終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挽救魏國,包括擴張私家勢力。
魏安釐王一度很倚重魏無忌這個弟弟。禮賢下士的信陵君,搜羅到許多能人異士,緩解了長期以來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也讓其他諸侯對魏國開始刮目相看。比起朽爛低效的官僚隊伍,信陵君的三千門客更像是魏國的頂梁柱。然而也正是這點,讓魏安釐王心存忌憚,不敢放手用他。
無論信陵君為相為將,三千門客都是一股令人生畏的編外力量。孟嘗君任齊相時,齊國還有不少文武能臣可以制衡他。而在爛到根子里的魏國,文武百官完全不能與賢公子爭鋒。魏國將逐漸形成二元政治格局,君王與賢公子各掌一半國政……
中央集權制最忌諱政出多門,追求最高權力的穩定。照這個節奏發展下去,賢公子勢力足以架空君王。魏公子當然沒有這種野心,可他在客觀上始終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當魏安釐王聽到“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的詆毀時,陷入了極度恐慌。他開始也沒信,但架不住眾口鑠金。畢竟,比起信陵君,魏安釐王的存在感太弱了。而且魏國源于晉卿,熟悉這種下克上的套路。這又加深了他的疑慮。
因此,魏安釐王解除了信陵君的上將軍兵權,讓他人代將。信陵君自暴自棄,被酒色掏空了身體而卒。魏安釐王也在同年離世。魏國最后的救命稻草沒了,衰亡速度加快。到頭來,大家都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