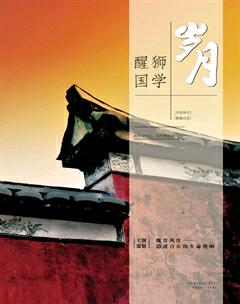風流本天然 無待自超絕
魏晉人士的風流現在幾乎已經成為歷史上已經確證的定調。正史、野史和史傳筆記中對古代人物和事件的記載常常有著較大的反差,學術史上那些堂堂正正、正襟危坐的歷史面目,在野史和史傳筆記中也會露出蹩腳、酸腐的嘴臉來,這樣的例子太多,可是唯獨魏晉士人的記載上,正史野史達到了一反常態的一致。
看來我們似乎可以這樣定論,風流,正是魏晉士人的正常生活樣態。
魏晉士人的風流似乎是他們的天性
隨遇而安、不拘禮法、興會神到、蕭散不羈,有時甚至還有些瘋癲。比較有代表性的,似乎還得舉王子猷的例子: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
“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八個字幾乎可以作為魏晉風流的一個代名詞。一個夜中失眠的忽然起意,就可以不顧大雪,急不可耐地去尋訪忘身山水的名士,王子猷的腳步迫切、一念必行。行狀至此,就可以稱為風流。一個臨時的念頭,最后成為一夜雪中急迫的腳印(當然行程多數是在乘船)。想到,而后不顧一切地馬上行動,沒有計劃、沒有安排,甚至沒有攜帶糧食飲水,一路上只有腹中先前飲下的酒提供著縷縷熱度,當然還有幾個不明所以而唯唯諾諾的跟班兒。這種灑脫是現代人無法模仿的,一念欲往,便馬上行動,沒有遲疑、沒有預算、沒有顧慮。如果故事僅到此,那么魏晉風流其實可見一斑。但是王子猷還是帶來了更出人意料的舉動,興會神到的一夜雪行,終于到了名士戴奎的家門前,卻搖身而返,仿佛從來就沒有想要造訪戴安道這回事兒。于是便有了那瀟灑不羈的八個字。
王子猷出身名門,世代貴爵,其父王羲之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我們今天似乎想不出為什么一個出身豪門的貴族子弟受了許多年的禮法教育,還會如此放蕩不羈。一個不愁吃穿的貴公子因為雪夜中忽然醒轉而輾轉反側,短暫的彷徨之后便非要即刻去拜訪一個山水間的前輩。他的生命中有許多事情可以消遣、可以自娛,可以招來朋友賓客一起游玩、歌舞、醉酒,當然在王子猷的時代,名門子弟還有許多德育、文化方面的課業,總之突發奇想的夜奔和一個貴族子弟本無聯系,卻又被一個貴族子弟實踐成了千古流傳的一件快事。
王子猷本身快活嗎?一夜尋訪,到達目的地后,轉身而歸,他似乎除了行路疲憊,什么也沒有獲得,怎么會快樂?——這是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對王子猷來說,他所要做的,已經達成,目的不是造訪戴奎其人,而是實踐了這一造訪的過程,興致得到極大的張揚和發揮,從而實現了精神滿足,更不消說還有一夜雪景,除了這個絕塵不羈的公子哥,當晚還能有幾人能有機會欣賞?王子猷的“興”并非是理性實用的現實滿足,而是生命格局中美的實踐的滿足,是在用來填飽肚子的欲望之外的更高一層的實踐。因為高于現實日用的格局,自然表現出來就是放蕩不羈,精神的通達,常常從突破慣常的得失權衡開始。
當然,魏晉士人令人瞠目的行跡還有許多。如嵇康鍛造。一個舉世矚目的學者,生得俊朗不凡,卻常常不洗澡;朝廷派人請他做官,他要費勁心思去躲避、拒絕;29歲便受封關內侯的鐘會,幾乎是人人追附的對象,鐘會對嵇康也敬佩不已,然而嵇康回應他的只有叮叮當當的打鐵之音;嵇康不打鐵的時候就和六個名聲大噪的賢士喝喝酒、唱唱歌,之后回去繼續打鐵——這是他心目中比做官要高尚得多的工作。嵇康和阮籍可謂魏晉名士中真性情的狂士,嵇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狂士,阮籍只能算半個。用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也說到類似的話:“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后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嵇康把狂放不羈貫徹得滴水不漏,自然缺乏變通和妥協,于是殺身之禍來矣。而阮籍則遁入“發言玄遠”的折中地帶,得以盡年。然而有意思的是,是嵇康——而不是阮籍——寫了一部當時非常有名的論文《養生論》,從哲學意義探討養生的理念、方法等等方面。雖然嵇康早逝,但是他的養生論從莊子意義上的精神實踐出發,突出精神養生的意義。可見嵇康對于生命的認知,并不僅在長度,而更在厚度。他的一句話可以印證此說: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到這,實際上涉及了一個問題:魏晉士人何以做到這樣的風流和人格獨立?
魏晉歷史有一個區別于其他時期歷史的有趣之處,在中國以君王為核心的著史觀念中,以筆者對《晉書》的閱讀所及,幾乎沒有很少涉及晉代帝王,而大多大書特書王謝。晉代的帝王多為士族門閥擁立,實際權力十分有限,于是歷史上就出現了晉惠帝這樣的極品皇帝。雖然晉惠帝并非歷史武斷傳播的那樣低能,但是能在正史中流傳出一位癡呆惡名的帝王,卻是其他朝代幾乎沒有的。晉代門閥權勢很大,是以百姓不知帝王而知王謝二家。這是其他朝代鮮見的。所以魏晉士人(尤其晉代)的全部熱情幾乎都用在門閥士族的身上。而世家大族自己手握兵權、司法、經濟、仕進等等大權,自然對皇帝無所求,于是儒家禮法的經濟基礎在此發生斷裂,而又因為封建禮法自身又無法克服的迂腐和繁縟,真正有才學的名士自然會用力于禮法之外。于是放誕、任達成了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曾在那個短暫的特殊時期擺脫了帝王政治的禁錮,在政治權力和經濟自給上相對自由,那么他們的風流正是天然的,絕無一絲偽裝,也無需偽裝。是以詩仙李太白追慕謝公和謝宣城,因為他們的放達不羈和李白的天性合拍,然而合拍僅是合拍,李太白終究還是想建立功業,那一聲仰天大笑,嘲笑的不僅僅是被困在土地上的蓬蒿人,最終也成為了他的自嘲。

魏晉士人的獨立與風流,也源于魏晉是一個談玄的哲學年代。
幾乎很少有人會不承認西方理性的深刻,也幾乎很少有人把東方與深刻聯系在一起。從古希臘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開始,西方的理性一直在不斷地向真理縱向地追尋。他們演繹出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龐大的哲學版圖,他們在這些版圖里成為一個又一個“哲學王”,甚至他們的名字本身也成為哲學的代名詞。
而東方的理性色彩相比之下則黯然無光,先秦道家零星地探討過本源問題之后,雖然其后還有董仲舒、王充、葛洪等人斷斷續續地“接著說”,然而非但氣象不侔,連用心也跟著壞了起來。甚至在董儒獨尊之后,幾乎所有讀書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在“天人”關系上,而不久又實實在在地忘記“天”和“人”的本來面目,轉而努力于“關系”,即致力于論證儒家倫理哲學的合法性。雖然在魏晉時期,玄學刮起了一陣看似理性的風潮,可是細看,仍然糾纏了太多漢儒的思維定式,而終至于岑寂。
可是,這岑寂,正是東方哲學覺醒的開始。
如果說西方的哲學是理性深刻的話,那么東方的哲學暫時可稱之為“感性的深刻”。這需要走出東方哲學的言語困境,因為言語正是東方哲學的最大假想敵。我們不得不重新看看魏晉時期“言意之辨”的內容,即語言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問題。“圣人立象已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而這些論斷的先導問題是一個正相反的結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我們需要注意這里的“盡”字,它是一個極其苛刻的字眼兒,它要求以它為媒介構成的雙方要以某種形式極度吻合而且同步,并且永遠在時間和空間上保持這種吻合與同步。那么無可爭議,語言的形質很難滿足這個苛刻的要求,然而除了語言又沒有其他的介質能有效地詮釋意義,這個難題陷入了困境。
魏晉玄學的儒者們最終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用以詮釋和展衍的工具正是詮釋和展衍的障礙。于是,他們只剩下酒和默默的竹林。
這時候,其實正是問題得以解決的時候,因為,語言除了文字和聲音,仍有另一種形式——無言。在阮籍窮途時,他曾訪問過孫登,孫登給他的答復是長久的沉默,阮籍無方,只好默默離去,正走在回去的山路上,孫登長嘯了一聲,竹林的葉子仿佛受到感召,隨風搖曳,阮籍大驚,一種瞬間直達頂峰的明亮感瞬間崩開,迅速填滿了他的宇宙。
如果這不算是無言之言,那么它何以完成了盡意的使命?
我們常常在意那些有著具體形質的東西,把自己牢牢囚禁在經驗世界的有限之中,漸漸失去了超越性的思維方式,這即是說,我們所失去的,是一個接近于西方真理的那樣的世界。西方的深刻是由理性的自我批判積累而成的,東方的深刻卻完全需要另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并不陌生,它既是西方的深刻最先濾去而又最終達成的東西,又是領悟東方的深刻的唯一途徑和內在尺度,它就是美。
美一定和天然的自由感和真實感緊密相連,追求美,也是魏晉風流之所以可愛可敬的地方。所以一千多年來流傳至今的魏晉風流,必定建立在魏晉士人對獨立人格的認同和堅守之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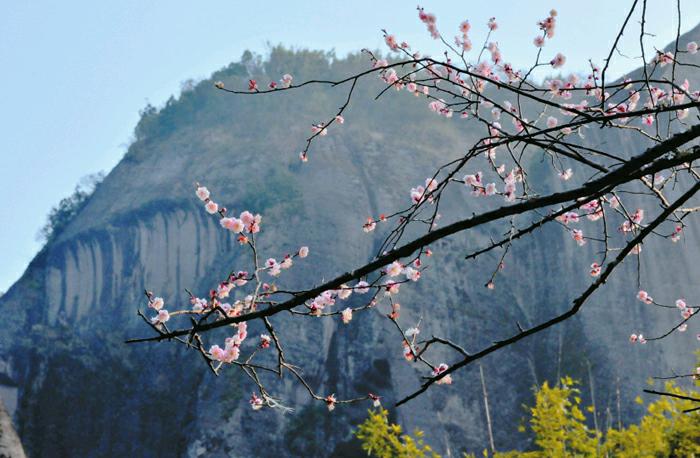
張康,市作協會員,古典文學博士在讀,出版詩歌散文集《北·回歸》,發表詩歌、散文、文學評論等數十篇,現為《北方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