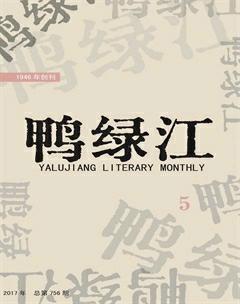烏蘭以西
李萬華
1
如果從高處去看,會看到大地上的色彩與色彩之間,存有鮮明界線。一種色彩如何結束,另一種色彩如何開始布局,似乎都有安排。然而站在大地之上,色彩之間這些清晰界限何以接替呈現,會時常忽略。有時正沉浸在一種色調當中,認為世界將會始終如此,無以改變,驀然抬頭,發現眼前景況已經變幻。有時,甚至連這種顯而易見的變化都看不到。人走進這種變化之中已經多時,腦際徘徊的,依舊是先前風光,仿佛大腦也在遵循慣性運動。烏蘭以西,接近德令哈時,草原如何被荒漠接替,便是如此。
或許是路邊花朵讓人注意到這種改變。此前路邊還開著半臥狗娃花,這些喜歡干旱和陽光的菊科植物,有著細長葉子和淡藍色花瓣,有蓬大而金黃的花蕊。我曾在河湟谷地一些極度缺乏水分的山坡看見另一種阿爾泰狗娃花綻放,在那些塵土足夠覆蓋鞋面的地方,它們大叢生長,植株高到一尺以上,葉子稀疏,覆有塵土,但是小小花朵清爽秀麗,惹人欲去采摘,又不忍采摘。在烏蘭以西的公路旁邊,我見到這種菊科植物,植株已經矮小到只有五寸左右,花叢變小,有時只是單獨一兩株,勉強開出單薄花朵。我曾下車,以微距方式拍下這些花瓣,只為簡單存念。等到發覺路旁狗娃花被一種紅色匍匐植物取代時,才發現遠處草原,已被荒漠替換。這種悄無聲息的變化,仿佛因為歉疚和慚愧,而不敢放聲喧嘩。可是,大地上發生如此鷹化為鳩的變化,居然無人察覺,一時又讓人覺得無比悵然,這不該是大地慣常的做法。狗娃花倏忽遁去,草原植物被一些色澤不夠明確的荒漠植物取代,仿佛瞬間換了一個星球。
這些荒漠植物為了減少水分蒸發,已將葉片變得窄小細長,有些葉片,甚至已經成為針形。無法越過高速路上的護欄,只能從遠處去猜想它們,它們或許正是常見的那些荒漠植物:柴達木豬毛菜,駝絨藜,唐古特白刺,沙拐棗,梭梭……有人說,它們屬于人工栽植,為了固沙防沙。是否果真如此,不得而知,但這種說法先入為主,當我仔細去看,它們果然如同剛剛布局的棋子,一叢一叢,在廣漠的大地上分布均勻,從無擁擠或者大范圍遺忘的情況出現。它們的色彩,也和大地一樣,淺褐,或者枯黃。我猜測可能是時節的緣故,也有可能,是因為裸露的地面太多。我對這些地方,并不熟悉,也不曾多次往返,得以窺見人們勞動的場景。若只依靠想象,斷然想不出人們是怎樣以栽種植物的方式去度量如此廣袤的土地,只能偶爾現出一些勞作的身影,然而那身影,又只是米勒畫作中那些永遠躬身面對土地的人。
以為水從此便在這里消失,再不肯光顧,哪怕只是以雨的形式,以露的形式,以雪花的形式和冰的形式,以及,以蒸汽的形式,可是,在靠近遠山的地方,湖水又突然出現。水為何總會和山一起出現,偶一發問,答案即顯,因為山無處不在。這塊高原原本是水的高原,后來才又變成山的高原。乳白的,淺藍和深藍的水,一汪,或者一線,仿佛一聲微茫的呼喚,穿越荒漠上的熱氣和耀白光線而來,讓人扭轉脖頸,暗自欣喜。待到凝神,它卻又不管不顧,抽身離去,仿佛與剛才無關。扒著車窗戶,看那些現出又遠離的水,依稀明白世間諸種出現,只為離去,存在只是一個微細過程,匆忙,而且慌亂。
2
很多時候,我會想起那些山,那些滿是褶皺的山。起初見它,曾有視覺和概念上的強烈沖擊。我慣常見到的山,已經有定勢存在,它們如何出奇,似乎都逃不脫山的概念,然而在走向德令哈的路上,這些概念一一被摧毀。車子向前,路兩邊迅速閃過的,那些山體的色澤,無法一下看穿,只能憑眼力判斷,是深黛、暗褐還是淺紫,似乎都是,又都不是。起先以為是暗褐,但是太陽光線一轉,暗褐亮麗起來,成了淺紫,若說那就是淺紫了,溝壑部分的色彩卻又黑起來,仿佛是深黛,又帶點蒼黑。如此迷亂,無法做出肯定,只得改變關注點。脫離色彩,眼前所顯,全是褶皺。那么多的褶皺從山脊披離下來,密集,并且顯得酣暢,仿佛干草搭在墻頭,剛剛被雨水澆透,又仿佛,有大手,將那些山坡折疊起來,壓出印痕,然后像一柄扇子那樣撒開。后來,我將那些褶皺想象成外星人臉上的皺紋。然而若說它們是山的皺紋,歷經漫長歲月,漸漸形成,又不盡然。因為那些山峰,并不顯得蒼老,它們聳立在近處,仿佛有人正在將它們揪起,像揪起一堆帶著褶皺的深色絲絨布。
要知道,對一件事物的描寫,若用盡各種比喻和想象,并力求新穎奇特,那只能說明,描摹者并無多少能力,能直接對這一事物做出恰如其分的描寫,他只好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依靠和借用一些不確定,來模糊這一事物的形態和特征。這一種表達方式,看上去似有講究,顯得典雅柔婉,但實際上,表達不過似是而非,大致若是。
那些山似乎與任何生命無關,盡管我看見那些褶皺中,隱藏一些深色植物,但那些植物或許已經干枯。那些山只與時間有關,那并不僅僅是過去的時間,還包括未到的時間。但是我們明白,時間不過是一種概念,它只與物質的變化有關。兜來轉去,那些山,實際只與它自己有關。它如何出現,怎樣運轉,何種變化,無人看得清楚,便是前人后人輪流去看,也不過是盲人摸象,只有局部。它的存在始終孤單。盡管如此,我還是會記下它們的名稱,宗務隆山和牦牛山,它們依舊是祁連山這龐大山脈中段的南北兩個分支。
我同時會想起那些駱駝。那不是羊群那樣以群出現的駱駝,而只是幾只。便是幾只,也非隨處可見。大荒原上,總是行走很久之后,才出現那么幾只,在那些同樣看不清色澤的草棵之中。它們在那里,除去低頭啃食那些荒漠植物,再無事可干,有時也會抬頭一望,望向山野和荒原。那引頸一望的姿勢,顯出曠古憂傷。但在更多時候,它們顯得閑淡放任,不關心任何事情。我從一旁望去,倒是種種擔憂。夜晚歸向何處,碰到襲擊者如何逃脫,是否被人飼養,如果不用來載重和騎乘,它們的生理結構是否會改變……
我還會想起那一群黑色的大鳥。那只是偶爾見到的一群,一路之上,也只是見到一次。它們大約從荒漠起飛,飛到高處,忘卻方向,只好來回往復。它們并不旋轉,排除掉烏鴉的可能,它們扇動翅膀的樣子,如同海鷗。它們的背景是那些帶著褶皺的山脈,底色單一,從遠處看去,它們如同一些縹緲無際的念頭。
有人說,人心只是一堆念頭的來來去去。但那只是被習氣熏染之后的情形,我們的初心,如同平靜之后的浩瀚大海,偶有一些念頭,也不過是那平面之上的些微漣漪。
3
陽光不僅有斑斕色彩和多種形狀,而且擁有氣質。荒漠上的陽光,直率果敢,膽汁質那樣,形狀也是固定不變,大片攤開在地面上,單一到讓人惋惜。進入德令哈市,陽光瞬間沉靜起來,帶些寂寥。其實,太陽還是那舊日的一輪,天空也未曾變更,若說事物有何鮮明的不同,也不盡然,但某種變化還是顯而易見。
高速公路向右一拐,路旁有大棵白楊樹栽植。這些挺拔樹木神情嚴峻,似乎始終都在提高警惕,想來也是一種喜歡自律的樹木,不懂嘻哈世間,不懂逍遙風塵。若說白楊果真如此寡淡乏味,又有例外。如果白楊長得足夠高大,夏季葉片手掌一般撐開,一陣風過便是一片銀光之外,樹葉會在風中發出蕭蕭之聲,那時若如靜坐窗前簾后,很有江南夜雨唐宋邊塞的蕭瑟之意,有時,甚至會有“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的悲涼。與白楊一同挺立的,還有路燈。若在以前,路燈桿子通常低矮,間距較大,夜晚到來,燈光一縷昏黃幽暗,人在街頭走過,很有聊齋的鬼魅味道,有時讓人懷舊。但現在,這樣的路燈再難見到。
德令哈的陽光,并非為這些驀然出現的白楊樹和路燈而改變,我從它們身旁經過,發覺陽光在那里依然顯示著簡單直率的一面。之外,便是那些大型建筑,是否是它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同樣從它們身旁經過,那些以灰色和象牙白為主調的高大建筑,顯然精心設計,在竭力體現個性風格的同時,注重端然大方和凝重莊嚴,這種強調,明顯突出與四周環境的和諧與默契。礦業部門,會議中心,體育中心,學校,研究院,名曰“藍天白云”的大酒店,以及各種賓館和住宅樓,它們端坐在這塊名曰德令哈的大地上,長時間沉默。因為是新建城市,有些建筑尚未有人進駐,大門緊閉,綠化帶植物長勢旺盛,一些野草,依墻披離。
后來,我終于明白,讓陽光顯得沉靜和寂寥的,并非那些植物和硬性設施,并非陽光它自身,而是人。
坐在步行街前面的小廣場上休息,正是傍晚時分,太陽已經西斜,白日太陽的烘烤早已消減。如果在其他地方,日暮前的時刻,步行街一定嘈雜,人們忙著采購,忙著回家做飯,買者賣者,都會高聲大氣,飯館也會顧客盈門,車輛擁塞。但在此處,一派蕭疏。我坐在沙棗樹下的椅子上,看人們來去,然而在二十幾分鐘的時間內,只有寥寥數人路過此處。他們多是回家的中學生,穿著校服,塞著耳機,也有老人結伴,躬身而行,年輕的夫妻,專注于話題。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于這種冷清,風過時,沙棗樹發出大的聲響,零星葉子旋轉而下。
在體育中心,我看到人工布置的花壇上有“激情柴達木,魅力德令哈”幾個大字,可能是某項活動剛剛結束。亦有零時搭建的大型帳篷,里面擺滿書籍,原來正在開展讀書月活動。走進帳篷,兜轉于各個書攤之間,試圖淘得一兩本,然而此處依舊如同其他書店那樣,擺放的書只以學生的各種輔導資料為主,也有營養保健、烹飪和一些暢銷書,文學書籍以青少年版世界名著為主。終于找到一本圖文本《山海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卷數不全,只有下冊,算是諸多書籍中的另類,決定買下。
夜晚很快到來,這應該是德令哈無數清寂夜晚中普通的一個。正是中秋,在如此空曠廣漠的地域上賞月,該是難得的機會。然而云層一直密布在東部天空,絲毫沒有退去的跡象。眼前的大街,只是清闊,街邊樹木在路燈暈染下,是龐大漆黑的一團,樹影斑駁,風過時,影子在地面跳蕩,仿佛一群來自春天的小獸,偶有騎自行車的年輕人當街而過,車輪帶起的,是一縷無可名狀的草木清香,片刻沉寂后,依稀有樂聲自遠處傳來。
4
懷頭他拉,這個名字念起來有種音韻學上的美感,抑揚頓挫。原是蒙古語,意思是西南的莊稼地。想必很久以前,此處也曾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然而,那會是多久之前呢,在懷頭他拉幾幅巖畫前,我發現已經無法用慣常的方式去理解時間。巖石之上,是一些拙樸的刻畫和描摹,來自動植物,以及人類。腰線細長、正在疾馳如飛的狼或雪豹,犄角銳利、身型健壯的野牛和馬鹿,溫順的羊正在低頭啃食青草,三馬架套、志在必得的獵手,飛矢劃出精美弧線,相依相偎的陰陽魚,騎馬之人,神情專注的男子和女子,后來出現在佛陀胸部的“卍”字,某種沐浴在陽光下的強勁植物,狩獵,放牧,追逐,休憩,舞蹈……千年前的種種存在,被觀察,被記憶,并在堅硬的巖石上,由另一種石器仔細磨劃。那些場景,構圖精簡,寥寥數筆,但是活潑,泛出神采。
巖石之前,時間自今而昔。想那定是天空明澈、陽光溫煦的一些時日,高大山脈在遠處連綿,山頂積雪發散幽微藍光,風從山頂披拂而下,漫過原野,翻動草木,掀起陣陣涼意。大地蒼茫寥廓,豐茂植物正在生長,草色之中,藍色湖泊如同珠寶鑲嵌。另有一些河流,正在緩慢流淌,靜謐水面銀光泠泠似有聲響。一場狩獵在遠處進行,靜伏,呼喊,奔騰突圍,健壯男子裸露肌膚,陽光已給他們鍍上某種金屬光澤。近處,女子、孩童和老人守著生活營地,炊煙熄滅,然后升起。母系時代早已過去,女人從某些繁重勞作中解脫出來,開始紡織烹飪。石紡輪,牛羊毛,植物纖維,燒制的粗陶器皿,采擷和種植一些果蔬,編穿珠貝,沿著河谷找尋彩色石子,這些細微,足夠忙碌一個整天。老人并不太老,仍舊躬身勞作,孩童赤足,嬉鬧之中種種模仿學習……時間緩慢,如同從大麻上剝下纖維,每一件事情都認真對待,話語可以和笑聲一起傳到遠處,夜晚到來,天空被篝火映紅。
如此想象,如此關注這些穿越時間卻依舊爛漫的畫面,我似乎也是其中之一:沒有過度文明熏染,沒有無以名狀的偏執和奢望,一些習氣尚未形成,太多煩惱亦未生起,沒有過去之心,也不在乎未來之時,注重當下剎那,明白錯失便是永久。勞作,愛,安眠,死亡……時間到底是何事物,我伸出手,可以觸摸亦被他們觸摸的巖面,可以感受他們曾經的愉悅和驚奇,以及強大持久的想象力,但我們的心,為何早已如此不同。
何為逝去,再不相逢,何為永存,亙古常新,一念而東,一念而西,剎那變幻,總成萬年。這樣的迷局,早該破解,然而沉陷太深,任誰都逃脫不掉。考古資料說,這些巖畫創作時間是北朝后期到唐朝時代,那正是任意隨心,卻又簡單純真的年代。
可魯可湖畔,我同樣被時間迷幻:我所面對的湖水,并非千年之后,而是千年之前。當是千年之前的中秋節氣,秋氣并未凜冽,但是秋風早已瑟瑟,云在天空,已經散成絮狀。雪也已經降臨,罩著遠處山頭,仿佛楊絮層層堆積。湖畔蘆葦已經黃去。這些蘆葦,曾經青蔥年少,曾經蘆花似雪,現在,它們成為另一種色澤,仿佛換了一套思想體系,與昔日舊有徹底決裂。巴音河自東南而來,緩緩注入湖中,仿佛一條游魚,湖水又從西南流出,進入另一湖泊(托素湖)。風偶爾凄緊,但是湖水依舊平靜,依舊清明,天光云影,倒影其中,另一層蘆葦,正在向湖底生長。我似乎一直坐在湖畔,風不曾吹亂黑發,湖水也不曾打濕雙腳。曾經有人捏著木叉來湖中捕魚,他們赤腳,俯身湖面,靜無聲息。也曾有其他女人,來到湖畔,用陶罐汲水。她們結伴而來,似乎并不急著汲水回去,她們將陶罐放置一邊,臨水梳妝。也有孩子,跑來嬉戲,蓄養的牛羊,曾來湖畔飲水,黑頸鶴和斑頭雁曾在天空低翔。只是這一時,他們都已歸去。鳥歸巢穴,牛羊回到草場,孩子或許已經熟睡……湖畔靜謐,再無其他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