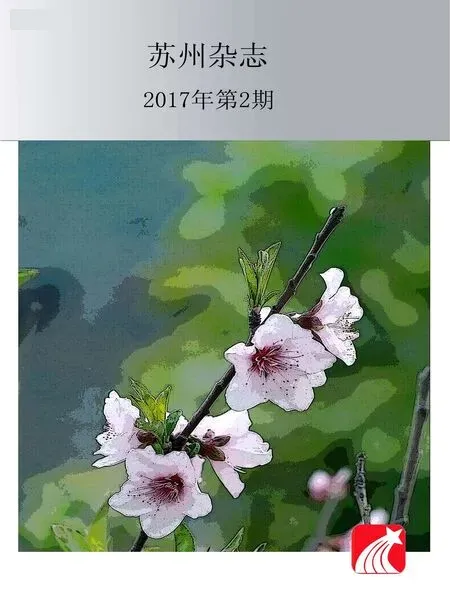崔護老師
潘振元
崔護老師
潘振元

一
崔老師原名崔光祖,祖籍博陵,曾用筆名“笑風”。1924年1月生于太倉。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第七、八屆蘇州市政協(xié)常委,高級工藝美術師,中華詩詞學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江蘇分會會員、中國工藝美術學會高級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江蘇分會常務理事、江蘇省考古學會會員、蘇州書法家協(xié)會副理事長、蘇州書畫研究會副會長、寒山藝術會社副社長、鶴園書畫院副院長、蘇州文聯藝術指導委員會委員、蘇州國畫院畫師、蘇州園林局藝術顧問、平江書畫院顧問等。崔老師于2008年12月4日因胰腺癌醫(yī)治無效逝世,享年84歲。
二
崔老師的一生,經歷過太多的曲折、磨難和屈辱,但也是他不斷自強、自立,自我奮斗的一生。在他生病住院其間,對我詳細回憶了他的過去,聽了讓人心酸。
他的祖父名叫崔逸峰,家有十幾畝田地,主要是種田,為了生計也做過道士。太平天國戰(zhàn)亂時從湖州逃到太倉,開了個肉鋪謀生。其父崔昌麟,繼承父業(yè),也以種田讀書為主。不幸的是在崔老師七歲時,得病謝世。由于崔老師當時尚幼,無奈之下與其母一起寄居外公家。外公家姓黃,是當地的一支大族,耕讀世家。單是宅中的一個木犀園,占地就有十多畝,其中有一棵大樹占了幾間屋。祖上做過官,到了他外公黃云甫這一代,家道還殷實,以堪輿為業(yè),也有不少官府親戚。當時崔老師的姑夫即在上海做道工局局長,修過海塘。其母黃秀英,是黃家最小也是最得寵的女兒,受過很好的教育。崔老師失怙后,全由其母承擔啟蒙教育,親自傳授《三字經》《千字文》,從讀識一千二百個方塊字開始,進行了系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崔老師后來讀太倉師范時,正值淪陷時期,實施奴化政策,學校改教日語,所以崔老師的傳統(tǒng)文化根底主要靠他的母親。
崔老師從小熱衷于寫字、繪畫。每天拿了一條長凳,坐在門口練字,學的是趙孟頫,寫就了一手好字。鄉(xiāng)親要寫字,包括婚喪喜慶送對聯,廟里的匾額聯語等都叫他寫,在鄰里寫出了名。后來,有人提醒他趙字寫大了,字不容易立直,于是在前清秀才的姑父指導下,改學趙佶的瘦金體。
崔老師的繪畫,主要得力于其表兄張星域,張星域當時在蘇州滄浪美專擔任教師,教西洋畫。此人學問好,畫也畫得好,因親戚關系經常有接觸,接受他的傳授指導,受其影響很大。同時,崔老師在當地有一群朋友,都出于太倉的名門望族,如毛三江、陸莘農等,尤其與畢秋帆的后裔交往很密切,經常一起玩,一起切磋,不僅使他在藝術上,包括在文學詩詞各方面都有得益。同時也促成了17歲那年與陸福臻、畢樊年在太倉民眾教育館舉辦了“三人書畫聯展”,在社會產生很大反響。
太倉師范畢業(yè)后,為了謀生,到太倉博古堂拜鄭也函為師,學中醫(yī)外科,但一年不到,老師病逝。于是就跟老師的大兒子鄭咸澤到昆山、太倉繼續(xù)學醫(yī),幫寫脈案、開方子,這樣又學了一年多。到20歲左右時,正巧有個朋友是上海人,跟了他去上海闖蕩,報考了上海武陵書局。當時幾次考的內容雖是繪畫,但因書法寫得好,被錄取做了編輯,包括文稿審核。同時一起考入武陵書局的還有華三川、梅云等。解放后,因蘇州房屋便宜,書局買的房子空關著,書局將編輯部遷到蘇州,崔老師是第一批到蘇州,書局叫他負責并代管書局在蘇州的另外兩個小企業(yè)。就這樣崔老師到蘇州定居。在編輯部遷蘇期間,崔老師創(chuàng)作了《大地重光》、《翠崗紅旗》(合作)、《小毛森王越》等連環(huán)畫,接觸了蘇州一些書畫家,其中有個叫金魁年,住在喬司空巷,此人是金拱北的弟弟,經他介紹崔老師參加了新國畫研究會。該會有百多人,分七八個組,因此熟識了朱博原、朱犀園、朱竹云、柳君然、陳娟隱等一大批書畫家。嗣后又擔任了蘇州市政協(xié)金石書法研究會秘書長,更廣泛結識了周瘦鵑、陳小青、顧頡剛、顧公碩等一批遺老耆宿。然而,好景不長,碰到“三反五反”打老虎,因書局的老板在上海,崔老師就變成資方的代理人無故被揪斗。隨即上海武陵書局撤銷。當人生處在最困難的時候,顧公碩與恒孚老板程叔履在經濟上都伸出援手。程叔履以幫他寫文稿、處理房地產方面的契約為由,讓崔老師住在他家。1954年蘇州土特產公司下屬的檀香扇廠招人,招考繪畫,分甲乙丙丁四等,崔老師以甲等被錄用(乙等可補習后再考,丙等以下不錄用)。然而,到檀香扇廠受到了更大的迫害,廠內原有一幫人,看到崔老師設計的產品好,畫得好,能力強,參加全國手工業(yè)展覽又獲全國獎,在政協(xié)金石書法研究會方面又經常見報,可能出于妒忌,或是政治上的需要,借1957年整風鳴放之機,對崔老師出于好心講的“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日本生產的檀香扇,已在國際上成為我們的競爭勁敵”,竟然把這句話顛倒黑白說成是助敵人威風的右派反動言論,不僅開除,還押送到派出所,這使崔老師再次跌入人生的深淵。可誰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最絕望、最困難、最屈辱的時候,也就是崔老師回到家的第三天,就被滄浪民間工藝美術廠的好心人請去擔任設計工作,第二年評上先進生產者。雖然極具諷刺性和戲劇性,卻可以看出當時環(huán)境的險惡與人性的善惡。1959年該廠并入民間工藝廠,1962年成立吳門畫苑,后又并入民間工藝廠。崔老師的第三次噩夢是文化大革命,他解放前曾用過一個筆名“笑風”,在文革中被人拿出來批判,說:“毛主席講‘東風壓倒西風’,你起筆名‘笑風’,分明不懷好意!”于是把他作為典型的反動知識分子揪出來,大字報、掛牌、戴高帽子,批斗,受到極度的迫害與摧殘。所幸的是:三次大的人生災難,沒有把崔老師生存的意志摧垮,沒能動搖他獻身藝術的信念。因此,當改革開放到來,調入工藝美術研究所,擔任設計室主任后,迎來了他藝術創(chuàng)作的春天。

三
事物有其兩面性,磨難對人生也是一種錘煉,往往更是一種激勵。文革中雖然燒掉了匯聚半生心血的兩本《碧鳳吟稿》和全部書畫作品。但浩劫一過,他堅持把所有的寄托、希望和精力,投入到書畫與詩文的創(chuàng)作中,成果豐碩。先后完成《湖山風月樓紀游詩草》《丹青吟》《硯邊談硯》《唐伯虎年表》《蘇州百詠》《崔護詩詞集》《畹華集》《太倉雜事詩》《稗珠集》《歷代七夕詩詞鈔》《崔護詩書畫集》等。人稱其“詩書畫印四絕”,錢仲聯贊曰:“以畫鳴,其題畫詩及書法并佳妙。”
崔老師的畫,他堅持自己的想法,畫自己的畫,走清逸一路的畫風。體現性靈之妙,瀟灑之韻,清逸之情,自得之趣。對于他的追求和成就,能讀懂和認識的人還不多。他用小斧劈皴的山水畫,風貌獨具;他的墨竹,人稱“崔竹”;他為全國民進畫過的墨牡丹,在一次全國民主黨派會上,驚譽北京;他的人物畫,吳帶新風,柔中帶剛,清麗灑脫,別具一格。繪畫中顯示出鮮明的個性、強烈的時代感和深厚的功力。他早在50年代作品就入選全國第二屆國畫展并獲銀獎,連續(xù)參加了江蘇省第一、二、三屆書畫展覽,全國各民主黨派美術聯展,全國青年畫展,獲得全國文聯頒發(fā)的一等獎。80年代頻繁的文化交流,使崔老師在兩岸三地和日本聲名鵲起,名重江、浙、滬。1985年國慶前夕,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邀請榮幸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觀看了鄧小平的閱兵儀式。1986年以藝術家身份應邀參加“蘇州市友好訪問及文化交流團”訪問了日本。

他的瘦金體書法,雖然也吸收了吳湖帆的一些特點,但有他個人的風格,剛柔相濟,尤其柔中見骨,使轉靈動,瀟灑飄逸,帶有很強的抒情性,令人喜愛。他創(chuàng)作了不少篆刻作品,尤其在50年代合作刻的《黨》字印譜、《蘇州風光》印譜、《百花齊放》印譜、《雨花臺烈士姓名》印譜等。雖作品大都已經散失,但他有兩方印,被收入日本編印的《中國現代印人集》。他先后為蘇州及海外新加坡等地書寫了二十多塊碑刻和無數的匾額與牌坊楹聯,他精湛的書法獲得了社會廣泛贊譽,作品被競相收藏。
崔老師創(chuàng)作的大量詩詞,突出在才氣與性情上。他以詩人的才情氣質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的作品,這在當今畫家中是無出其右的。且精于古風,最善長歌。一曲“船娘曲”,數十家詩刊轉載,風靡了全國。他三百六十多首蘭花詩詞,震驚了詩詞界與蘭花界。有“一代寫蘭宗師”之譽。
崔老師學識淵博,他常說,一個人一世中能留下一點文字,是人生的大福分。崔老師為此治學不息,耕耘不止,在美學、博古、鑒賞、工藝、文史、園藝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曾復制瑞光塔出土的珍珠舍利寶幢,幾與真品無異;另外,跟昆曲傳字輩鄭傳鑒唱小生,跟王傳淞也學過。他在《牡丹亭》中唱小生,在《鄭州放糧》折子戲中扮老師,《林沖夜奔》的折子戲他能一唱到底,幾次在拙政園、獅子林里公開唱過,聲情并茂,博得好評;他的文章,行云流水,博古通今,識見精辟,不襲陳言,積三四十萬言,燦若云錦,美如珠玉。
崔老師德高望重,大家把他比喻為“人中龍鳳”,見到他的人都說“相見恨晚”。他的謙和、真誠、正直,淡于名利,不求榮達,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美德,為人所稱美。他熱愛我們這個社會,他的作品中飽含激情,始終盡情地歌頌,淋漓地贊美。他關心家鄉(xiāng),熱心收集太倉史料,他熱愛蘇州,寫了一百多首《蘇州好》,成為蘇州歷史上少有的頌辭鴻篇。他在臨終前幾天,還在不停地叨念:要是給他一點時日,他還可以做不少別人不愿做或不肯做的事情,特別講到還未做完的那些事時,老淚盈眶,看了讓人心碎。他優(yōu)秀的品質、高尚的人格和治學探藝老而彌勤的精神,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和學習的榜樣。
殘月冷風,寒云低空,崔老師雖已離開了我們,但他的人品美德,將永遠地銘刻在我們的心間;他的藝術精神,將已深深地播種在蘇州這片沃土上。崔老師的一生,是獻身于藝術的一生,是為蘇州書畫事業(yè)作出了貢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