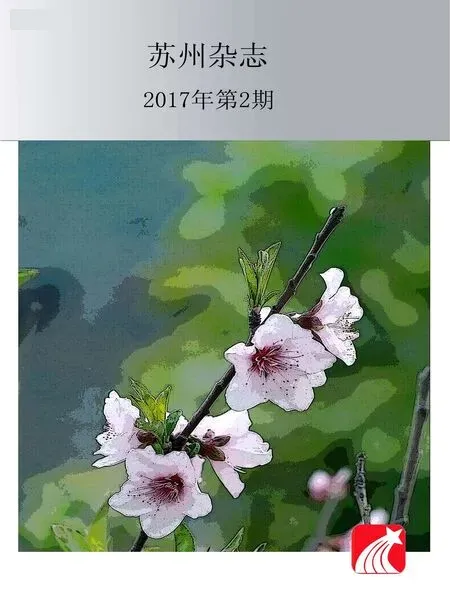《吳下名園記》點校記
王刃
《吳下名園記》點校記
王刃

《吳中文獻小叢書》由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于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939年至1943年)陸續編纂刊行,共三十二種三十冊,舉凡與吳地相關的山水游記、人物年譜、詩詞創作、金石書畫、日記信札、筆記小品等,品類繁多,可謂包羅萬象。或為未經刊印之遺稿,或為流傳已罕之孤本,很多文稿幸賴當時學者苦心搜羅得以保存。小叢書刊行旨趣說到,“地方文獻,全文化之所由積也。文化為物,群倫攸共,故凡尊惜文化,應自地方文獻始。”放到今天,這套蘇州地方文獻叢書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殊為可惜的是,由于出版于淪陷戰亂年代,編審校對頗為匆忙草率,此小叢書錯訛脫漏之處甚多,而且年代久遠,七十余年來多數再未刊印,現在已難窺全豹。因此,參考其他文獻、版本,重新比勘點校,并改為現行標點符號,以簡體中文印行,也許并非毫無意義。
《吳下名園記》為小叢書的最后一種,編號三十,“掇拾前人記述吳中園林之作,匯為一編。”此書選文頗為精當,姑蘇四大名園拙政園、獅子林、滄浪亭、留園自然必不可少,同時也兼顧可園、半園、鶴園等現今游客寥寥之所在。既有蘇舜欽、文徵明、歸有光、俞樾等大師名篇,亦輯錄歐陽玄、彭啟豐、金天羽諸賢達逸文,一冊在手,“不惟足資來游者之向導,而吾吳中名園興廢之跡亦得由是而稽焉。”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以及筑園者大多有著共同的精神向往,即閑適、隱逸。這也許是蘇州人骨子里的精神內核罷。顧頡剛先生描繪蘇州人的追求是:“飲酒、品茗、堆假山、鑿魚池、清唱曲子、揮灑畫畫,沖淡了士紳們的胸襟,他們要求的只是一輩子能夠消受雅興清福,名利的念頭輕微得很,所以他們絕不貪千里迢迢為官作宦,也不愿設肆作賈,或出門經商,只是一味眷戀著溫柔清幽的家園。”所謂“閑”者,用蘇州話來講,約略就是胸無大志,平平淡淡地過過“小日腳”,十分“寫意”。稼句先生在《懷土小集》題記里說,“這個寫意是吳下方言,說不大清楚,大約就是舒坦、愉快、隨意、省心的意思。我感到寫意的事很多,比如早春探梅,檐下聽雨,樓臺賞雪,去滄浪亭喝清茶,去黃天源吃點心,最讓我覺得寫意的,那還是隨意讀點閑書,如今書印得多,買的送的借的,往往堆積如小丘,真有點來不及讀,那就按著自己的喜好,翻翻這本,翻翻那本,這就來得寫意了。”早有人發現蘇州人中少有在外闖蕩者,蘇州人心心念念的是“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清氣覺來幾席,凡塵頓遠襟懷”,所以留戀故園,所以不屑于遠行,閑適隱逸的人文精神應當是一個重要原因。蘇軾《記承天寺夜游》說道,“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張岱《湖心亭看雪》也言,“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仔細玩味,蘇東坡清于骨,張宗子清于態,雖格有仙凡之別,但終究得一閑字,欣賞蘇州園林,似乎也應從“閑、隱”二字入眼,乃得真趣。
俞樾《半園記》記載,史杰邀請俞曲園參觀他修建的半園,俞樾觀覽后嘆為觀止,認為此園“高高下下,備登臨之勝;風亭月榭,極檉柏之華。視吳下諸名園,無多讓焉”。俞樾問史杰,既然此園如此佳妙,為何要叫半園?史杰回答,因為此園僅僅只有一半,邊上還有一大塊空地,人家勸我買下,以求其全。我卻認為如果事事要求全,那么達不到目的必然不爽,這種傻事我才不干。“吾謂事必求全,無適而非苦境,吾不為也。”俞樾聽后心悅誠服,認為史方伯“合知足,知不足兩義,進乎道矣”。并不覬覦旁邊空地,有半園足矣,是“知足”,知足可以有閑心,可以長樂,可以戒“貪、嗔”。知道自己的園子并不完美,只能稱為半園,是“知不足”,知不足可以杜絕狂妄無知,可以戒“癡”。由此可見,《吳下名園記》并非止于描繪園林的歷史、方位、建筑、景色,類似的通達議論俯拾皆是,值得一讀。
本書點校時以小叢書版為底本,盡量保持小叢書版文字的原貌,并參校其他版本和實地碑刻。小叢書有明顯錯誤的,徑行修改,不出校語,可改可不改之處,一任其舊。
書讀得多了,往往會將一部分興趣轉移到地方故土上來,縷述風俗,考訂古跡,閑暇時輯錄點校一些古書,也是來得格寫意。本人生性慵懶,輯錄點校當然也是“磨洋工”,時斷時續將近三個月,終于完稿。由于學識淺薄,錯誤自然不少,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