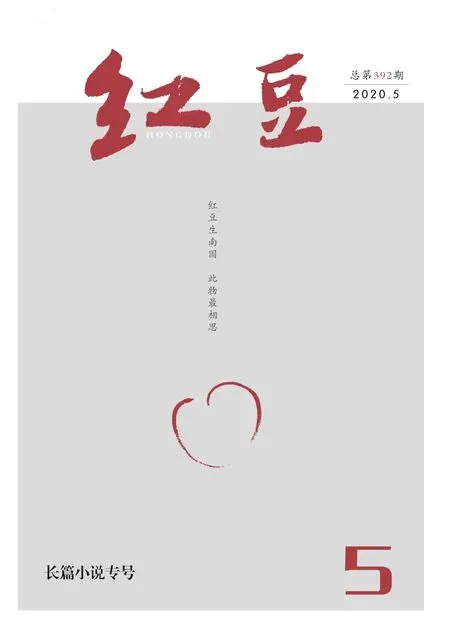班公柳
樓衛東就在這所全縣最高學府,縣完全小學任教,全校有五六十個學生,四五位老師,由于老師學生基本住校,還有幾位管理人員。課程設有藏語文、算術、音樂、體育等。本來設有漢語文課的,只有校長扎西會一些漢語,不太忙的時候上幾節課,課本堆放在教室一角,學生有時候自己翻一翻,有時候來了工作組,會漢語的干部客串教上幾節,縣上會漢語的干部和駐地軍人,偶爾也來講一講故事,照本宣科,領讀幾篇課文。
樓衛東的到來,喜得扎西校長一會兒跑到他房間,一會兒跑到操場,一會兒又折回來。
開始樓衛東還問聲好,扎西用磕磕巴巴的漢語回答他,你好,你好。
扎西來回跑了幾趟以后,樓衛東只咧咧嘴,算是問候。比扎西校長跑得更勤的是學生,一堆一串地來,推來搡去,嘻嘻哈哈,見他抬頭看他們,哄地一聲散了,跑得不遠不近。過一會兒,前呼后擁再次出現。還來過幾位留長辮子穿藏袍的男女,皮膚黝黑得如同鍋底,從亂糟糟的頭發和臟兮兮的服裝來看,顯然不是學校老師。
打量一陣,發現學校沒有院墻,教室和師生宿舍與牧民土坯房子混雜在一起。
他特意穿上綠軍裝,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平時舍不得穿這套衣服,只在重要場合才穿,比如首都某位學生領袖來學校演講,比如學校為他開歡送會,比如在西安與青年學生見面,他才獎賞自己一樣,鄭重其事地穿一回。以前穿過父親淘汰下來的軍衣軍褲,離開家讀大學的時候,母親把這套軍裝整整齊齊放進藤條箱子,將巴松遞給他,拍著他的肩膀說,音樂能陶冶情操。他興奮得真想拉一下母親的手。
從小到大,很少主動拉拽父母的手,父母對他們幾兄妹很少摟抱親昵,他也沒有看見父母之間親密的言行,母親稱呼父親永遠是柳政委。即使父親的職位變動過幾次,母親依然這樣稱呼,柳政委吃飯啦;柳政委二小子學校開家長會,我去啦。父親叫母親總是小鬼,小鬼我要下連隊一周時間;小鬼下次大會發言簡短一些。
當啷,當啷,一陣悶響,樓衛東才意識到要上課了,順著聲音望去,扎西校長正笑呵呵地望著他,一邊望,一邊敲擊兩只巨大而彎曲的東西,敲完以后放進吊在半空中的皮囊里,皮囊在風中搖擺不定。
他才恍然大悟,上課鈴聲是牦牛犄角敲出來的。
幾步走到講臺前,掃視了一下學生。所有學生全都坐著,瞪大眼睛望著他,有的微笑,有的驚訝,有的恐懼,有的茫然。
他把課本往講臺上一放,大聲說:上課。
安靜,超乎尋常的安靜,連風聲都聽不見。學生依舊坐著,奇怪地望著他。
忽然,教室門外傳來一個聲音,只叫了一聲,所有學生都齊刷刷地站起來,齊聲喊了一句什么,有的還向他鞠躬點頭。幾秒鐘以后,所有學生又整齊地坐下。
一偏頭,看見扎西校長離去的背影,方才明白,原來學生聽不懂他的漢語。
稍稍平靜一會兒,就講了起來,忘了學生只會藏語,忍不住提問,沒有人回答他,有人交頭接耳,有人嬉笑不止。趁他轉身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一個男生離開座位,走到教室后面,對著教室一角撒尿。他是聽到唰唰聲,才回頭,確信自己沒有看錯,站在原地不動,大腦一片空白,牦牛犄角再次相互撞響,他還在發呆。
過了幾天,一個男生背著一個嬰兒來上課,前后左右的學生一會兒摸摸嬰兒的小腳,一會兒摸摸小臉,鬧得嬰兒哭泣不止,他只好讓那個學生出去。男生剛出教室,一個女人背著鼓鼓囊囊的羊皮袋子走到男生跟前,既不放下袋子,也不抱過嬰兒,揭開藏袍就給孩子喂奶。男生歪著脖子、斜著肩膀,努力把嬰兒往女人跟前湊。女人喂完奶轉身離開,衣角在風中一路飄拂。
男生目送女人走遠,在原地轉圈,雙手大幅度擺動,嬰兒哼唧幾聲就不哭了。樓衛東走出教室,向男生招手,男生背著嬰兒,重新坐回原位。
后來他注意到,這個男生不背嬰兒的時候,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還喜歡佝僂著腰。
還有一次,一個女生沒有請假就不上課了。扎西校長騎馬出去了一天,帶回一個陌生的男孩,并告訴他這是女生的弟弟,姐姐回家放牧,弟弟頂替上學。
樓衛東一時反應不過來,就問:女生還來上課嗎?
扎西晃晃腦袋,攤開雙手,吐吐舌頭。
樓衛東逐漸發現,藏北的白天特別漫長,夜晚同樣漫長。常常的,想起消失在冰河的巴松。
幾年以前,剛把巴松帶到北京去的時候還不會吹奏,只知道像一捆柴的精美樂器叫大管,一位老師告訴他這是西洋樂器,在西方被稱為巴松,演奏巴松的大師很受推崇,巴松演奏家與鋼琴大師地位相同。他喜歡這個奇怪的名字,好在有熟練的二胡口琴技法,摸索一段時間,竟然能像模像樣地吹起來。巴松的音質既不同于薩克斯,也不同于大小提琴,具體有什么區別,自己也細分不清,只是覺得好,美好。
現在,那份好,只留存在記憶里。
他到縣城周邊轉過幾次,希望找到制作巴松的材料,結果發現這里不僅沒有樹木翠竹,甚至連一株高過小腿肚子的牧草都沒有,哪能找到楓木?在這里想要制作一支巴松,如同癡人說夢。
慶幸的是,還有二胡和口琴,便一曲接一曲拉著二胡,《二泉映月》《聽松》《空山鳥語》。口琴吹奏《小夜曲》《鳳陽花鼓》《漁舟唱晚》。老師學生全都擠到他周圍,笑容燦爛,眼眸明亮,有好幾次,他都想告訴老師和學生,你們笑得真好看呀,比大學校園里的芍藥牡丹都好看呢。你們的笑容千變萬化,蹦著跳著都在笑,芍藥牡丹只是一張面容、一種姿勢。
一想到他們聽不懂他的話,興奮度銳減,沮喪之情陡增,對牛彈琴的感覺油然而生。
他發現,許多人沒有見過二胡和口琴。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邊聽邊咧嘴大笑,欣喜無比。沒過幾天時間,整個縣城都沸騰了,年輕人,年老者,藏族人,漢族人,全往學校擁。
一天清晨,陽光剛剛灑滿原野,學校來了幾個人。他不知道來者何意,照常上課。扎西把他從教室拽出來,藏語夾雜著漢語,還雙手比畫,向來人指一下,再指指他的膝蓋,一只手不停向外擴展。
終于明白來人是想聽他拉二胡,他指指教室,意思是還要給學生上課哩。
扎西揮一揮手,指揮另一位老師進了教室。
他搖搖頭,苦笑一陣,取了二胡,坐在木凳上,左手緊一緊內弦軸,右手剛握弓桿,大概用力過猛,起音高銳,嚇得一個人往另一個人身后躲。躲避的同時,脖子抻得更長,腦袋抬得更高,眼珠子轉得更靈活。
一天傍晚,一位眉骨高挺的小伙子抑制不住激動,合著他的二胡曲調跳了起來。接著是兩個人,三個人,后來是所有人,房間容納不下,就到操場,大家手拉手,圍成一輪太陽,一輪十五的月亮,把他圍在中間,繞著他轉圈,歡笑,唱歌,跳舞。在他身邊點起牦牛糞火堆,熊熊篝火燃燒起來,火苗跳躍,親和纏綿,打著卷兒,做著伴兒,合唱一般,獵獵歡笑。
變戲法一樣,篝火上架起了一口大鐵鍋。鍋里放進從縣城外的河里鑿下的冰塊,冰塊化成水的漫漫過程中,有人緊緊抓住羊子的四只蹄子,將羊毛繩子勒進羊子嘴里。羊子還沒來得及呻吟,一滴血不流,就無聲無息地死去。一個漢子用尖刀輕巧地剝去羊皮,羊皮與羊肉之間有一層薄薄的白,絲絲縷縷,柔和溫潤。漢子一邊開膛一邊念念有詞,旁邊有人雙手合十跟著念誦。一陣好聞的氣息隨羊子的胸腔熱氣彌漫開來,內臟隨即被掏出,有人清洗羊腸子,有人將羊油和青稞粉放進羊肚子,與胸腔里的羊血混合拌勻,再灌進清洗后的羊腸子。鐵鍋里的水沸騰時,血腸與羊肉一同入鍋,過了一會兒,水面漂起一層褐色泡沫。
樓衛東發現自己的飲食習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自從來到藏北,就沒有見到大米白面,取而代之的是糌粑和風干的牦牛肉羊肉。青稞炒熟以后磨出的面粉就是糌粑,他已經非常熟悉。經常吃羊肉,還是第一次看見殺羊,灌血腸的過程也是第一次領略。
人越聚越多,火越燒越旺,好幾次有人拉拽他的手,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扎西對他說,鍋莊,鍋莊。他才把口琴裝進衣服口袋,一只手伸向扎西,一只手隨便伸出去,立即被人拉住了。
手與手相牽,繞著大鍋邊唱邊跳,所有人都在唱歌,所有人都在跳舞,所有人都興奮異常。第一次理解了鍋莊的含義,原來是圍著篝火鍋臺起舞的歌舞,藏族人的用詞也很形象生動哦。
忽然想起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藏族歌舞,盡管只是在廣播收音機里聽過,熱情歡暢高亢的歌聲曾經長久地感動過他。記得才旦卓瑪演唱的是《毛主席,祝你萬壽無疆》。此時,置身于藏族人中間,遠離首都北京,更能理解演唱者的情真意切、激情飛揚,對毛主席的祝福和愛戴。才旦卓瑪是藏族人,唱的卻是藏漢兩種歌詞,他也可以教身邊人唱這首歌曲,雖然不大明確藏語字句意思,祝福贊美自然有的,想一想,就放聲唱了起來。
毛主席的光輝
嘎拉亞西諾諾
照到了雪山上
依拉強巴諾諾
他唱著,有意放慢節奏,果然有人跟著哼唱,但唱兩個字就咕嚕開了,音調跑得遙遠。
他笑著,繼續教唱,還是沒有人能完整地唱出一句。心想這里大概離北京太遠,不大了解毛主席,對這首歌太陌生。還是教一首與當地風土人情有關的歌吧,想了想倒不好意思起來,滿懷熱情來到西藏,竟然連一首藏族歌曲都不會。還是教那首在唐古拉山下即興創作的歌曲吧,只有四句,簡簡單單,歌詞內容又是他們熟悉的,學起來應該不難。
這一次,他沒有獨自先唱,而是一字一句,聲情并茂,像合唱團的指揮,雙臂用力,打著手勢,節奏分明地揮舞。反復幾次,還是沒有人學會,只是更多的笑臉望著他,仿佛在欣賞他的獨角戲。
正當他有點灰心的時候,有人雙手遞給他一條冒著熱氣的羊前腿,并從腰上拔出腰刀給他。他接過羊腿,看其他人,大家只拿著小塊羊肉或一截血腸,唯獨自己捧著一條完整的羊腿。想都沒有想,趕緊遞給身邊一位辮梢花白的男人,搖擺著雙手,沒有接那藏刀。男人又把羊腿轉給身邊的老年婦女,婦女的發辮如同兩條干枯潔白的羊毛繩子,長長地垂在腰際。
忽然,男人捧起他的雙手,放到自己臉頰上。樓衛東有些緊張,不知道要發生什么,慌亂地看著扎西校長,扎西正刀口朝自己,專心地割一塊羊肉,嘴里嚼得正香。
只能任由男人擺布。雙手剛觸摸到男人的臉龐,第一感覺是粗糙,接著就有了溫軟的感覺,心里頓時熱乎起來。這種感覺曾經有過的,只在模糊的記憶里,母親的臉龐夢幻般一掠而過,攜著江風的呼嘯和乳汁的馨香。
僅僅一剎那,就被冷風驅散了。自從來到這里,風就沒有停歇過,藏北的風真有毅力,無休無止,無處不在。
冬天來得可真早啊。心慌了一下,垂下雙手,向老人點點頭。
有人走到他面前,雙手合十,羞澀地微笑,彎腰施禮,吐著舌頭。有人把自己的額頭抵到他額頭上,他不知所措,又不好躲閃。直到扎西校長摟著他的肩膀,額頭抵到他額頭上,并用漢語說,你,我,兄弟,兄弟。
他才明白,這是藏族人表達友好的方式。
看著扎西黢黑的臉龐,那封言辭激憤的檄文上躥下跳,奔涌而來。
文采飛揚的檄文書信出自親兄弟之手,雖然可能會老死不相往來,還是佩服他的才華,那才是兄弟呢。如果真要算兄弟,郭漢山算一個。
感覺有些疲憊,想回房間休息,剛要轉身離去,一個男孩一溜煙跑到他面前,學著他剛才的樣子,唱了起來:一個美麗圣潔的地方……
后面是一串哼哼唧唧,嘻嘻哈哈。僅僅只這一句,樓衛東就激動不已。
還是有成績的嘛,有人學會了一句漢語,這是一個良好開端。男孩拽住他的衣襟嬉笑,仰起脖子向他說著什么,他聽不懂,只是覺得面熟,應該是一名學生吧。
男孩見他沒有反應,把手伸進他衣服口袋,他感覺到了,啪一下,打著了小手。男孩后退幾步,瞪大眼睛看他,眼里滿是不解。
篝火還在燃燒,羊肉還沒有吃盡,青稞酒繼續暢飲,一位中年男人搖搖晃晃一陣,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樓衛東快跑幾步,想要扶起他,被扎西校長攔住了,指手畫腳一番,他大致明白了意思。這個人犯病了,不能動他,安靜平躺一會兒,自己就會爬起來。
夜空飄起了雪花,歌舞漸漸停歇,火苗跳一跳就熄滅了。有人用一張牦牛皮抬走了那個人,雪花落在牦牛皮上,落在男人身上,也落在樓衛東身上。他沒有拍打雪花,任由自己穿風渡雪,喘息連連。
夜朦朧,雪朦朧,偶爾能看見自己哈出的熱氣,熱氣很快飄逸到雪花中,與雪花邂逅相融。
原本要好好睡一覺的,翻來覆去睡不著,只好靠在床頭,裹著羊毛被子,就著酥油燈,給郭漢山寫信。好像有好多話要說,開了幾次頭都作廢了,只好寫了幾句報平安的話,折好信,又糾結到哪里郵寄,想起聽誰說過,開山季節地區和縣城之間有郵車來往,半個月跑一趟,才昏昏睡去。
迷蒙之中夢見自己在喝酒,喝了一口就醉了,醉了以后向一座雪山跑去,跑到山下雪山不見了,出現了一條河流。河水清澈平緩,流速悠然舒緩,河畔長著荷花、茉莉花、菖蒲、蘆葦、香榧樹、榕樹、棕櫚樹。小鴨戲水處,浮著一支油亮的巴松,暗黃的管體,淡黃的哨片,模樣甚是好看。
巴松,巴松。他大叫起來。
驚醒以后,坐直身子,冷風颯颯,打了一陣寒戰,重新鉆進被窩,睜著眼睛等天明。
樓衛東驚奇地發現,自從來到西藏,長夢方醒一般,攜風挾雪,對許多以前不曾注意和上心的人和事,記得異常清晰,花草樹木,飛鳥走蟲,春風秋雨,白鷺蒿草,都能分辨清楚。回味長久以后,對那位白頭發漢族人更加佩服,他好像說過,到西藏以后會留戀內地的綠色,關注以前漠視的事物。
一天正午,陽光明媚,但不溫暖,終于來了一位漢族人。他雙手抱著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皮水桶,桶里有一株小樹,從幾片彎曲的金黃色葉子看,應該是柳樹。來人放下水桶,摘掉帽子和墨鏡,才認出是一位副縣長,姓王。
樓衛東趕緊招呼,他卻不坐,站在門口說:急著要到內地出差,順便回上海探親,不出意外的話,明年開山以后才回來。這樹大概四歲,三年前路過班公湖,在湖邊挖來的班公柳,這次走的時間久,請樓老師幫著照看一下,記住澆水保暖就行。
末了,撓一撓油光發亮的齊肩黑發,又說:知道縣里來了一位高材生,早要來看望,這不,趁著大雪尚沒有封山,修路剛回來,忙得幾個月沒有理發洗澡,生了一身虱子,先回去收拾收拾,得趕在大雪封山以前走出羌塘無人區。
王副縣長重新戴上墨鏡氈帽,樓衛東發現他額頭上有一圈褐色紋路,紋路以上白一些,紋路以下暗黑一些,眼睛像熊貓眼,鏡片以外的皮膚顏色更黑更紅,想必是常年戴帽子墨鏡留下的印跡。
都走到操場了,王副縣長回頭說:這里紫外線太強,會傷皮膚,搞不好還會患白內障,出門千萬記住戴墨鏡帽子。下次路過拉薩給你帶一頂帽子回來,咱這的人帽子同衣服一樣重要。
樓衛東暗自興奮,總算認識了一位說漢話的人,盡管口音既不像上海話,也不像普通話,更不是藏語,還是感到無比親近。
摸著班公柳的葉子,低頭去嗅,有一絲清香,這是春天的味道、花木的氣息,好長時間不曾聞到了呢。部隊大院和大學校園的垂柳,春風時節,柳芽如一只只鵝黃色的小燕子,起風時,翩然翻飛,飄飄欲仙。春雨過后,柳絮如銀,綿密細軟,一會兒飄向海棠,一會兒游到池塘,似煙非煙,似霧非霧,綾羅浮萍一般。秋天的垂柳溫婉華貴,淡淡的韻味,溫和的氣息,不刺眼不張揚,小金魚小信鴿一樣,搖曳婀娜,鋪灑一地,踩在上面,舒緩如緞。記憶中柳枝的顏色,同樣也是春天的風采,掐捏一番,一定能溢出春天的汁液,想起來就歡喜陶醉。
以前怎么就沒有這種感覺呢?
上次在獅泉河鎮,也見過柳樹,鐵銹紅的枝干,應該是紅柳吧。枝干直指天空,沒有彎曲的氣象,與內地的白楊、松樹毫無二致,掙扎著,努力向天空生長,只是沒有白楊、松樹的高度,更沒有隨風飄搖的枝條、曼妙嫵媚的柳絲。紅柳枝椏繁多,蓬蓬松松一堆,辨不出誰是主干,誰是枝杈。王副縣長的這株班公柳枝干為灰白色,拇指般粗細,主干上分出兩根更細的枝條,枝條則是黃褐色,葉的邊緣有小小的鋸齒,彎彎地掛在枝頭,悠然,閑適。
樓衛東把水桶輕輕抱起,放到床頭跟前,比了一下高矮,樹梢剛剛齊腰,枝條同紅柳一樣,也是一副向天歌的架勢,不卑不亢,精神抖擻。
數一數,九片葉子。不放心,伸出右手食指,指點一遍,不多不少,九片。
四歲,班公柳四歲了,王副縣長怎么把樹比喻成人呢?只有人才說幾歲幾十歲的呀。
腳步抬得很高,在房間轉了一圈,又來數,還是九片。
九九長久,九州四海,十拿九穩,鶴鳴九皋,呵呵,真好啊。藏北大地,還是有高過小腿肚子的植物嘛,而且是一株柳樹,太驚艷了,簡直像是天外來客。
幾步就跨到門外,地上沒有積雪,只有細小的礫石,環顧一番,沒有看見一滴水。來這么長時間,還沒有到河里背過一次水,鑿開一次冰,甚至沒有跟著拖拉機拉過一次水,這些事全由廚房師傅承擔。性急中,抓起臉盆到了河邊,發現河面只結了薄薄一層冰,也許夜晚冰結得厚一些,上次大鍋煮羊肉的冰就有一指厚。
河邊,一位看起來眼熟的女人正要背起木桶起身,見他走近,放下背桶,伸出手來。他不知其意,一臉平靜,女人收回雙手,在圍裙一樣的橫格布上摸了摸。
河面不寬也不窄,與河岸幾乎一個平面,河水想必不會太深吧。他想沿河邊走一走,找塊大一點的石頭坐一坐,如果夢境能夠復原,說不定能等來自己的巴松。
正在他想象的時候,身后傳來嗨嗨的聲音。
應聲看去,女人向自己身邊指一指,又向他指一指。他朝她點點頭,說一聲,謝謝。
女人笑一笑,背起水桶走了。他在河邊走了許久,也沒有找到一塊能坐的石頭,臉被吹得生疼,腿腳越來越麻木,只能彎腰前行。瞇起眼睛,竭力望去,依然是一望無際的礫石灘,一片一片積雪凌亂散開,只有低頭細看,才能分辨出礫石縫隙間淺淺的荒草和晶瑩的冰雪,小草就像麥芒,尖細,有力,不卑不亢。
回眸間,縣城是那樣渺小,除了灰突突的土坯房別無他物,與廣闊的原野相比,如同掌心的一顆痦子,桑葉上的一粒蠶卵,太陽上的一顆黑子,靜靜地臥在荒漠中,顯得可有可無,微不足道。一轉身,手里的搪瓷臉盆“咣當”掉在地上,彎腰去拾,沒有拾起來,雙手舉到嘴邊,哈出幾縷熱氣,搓一搓手,再搓一搓臉。
河面封凍嚴實,連一條裂縫都沒有,哪里才能取水呢?
驀地,想起女人指過的地方,緩步而去,只是臉盆大小的坑洼,坑洼也結了冰,好在冰層脆薄,像是剛剛生出的新冰,舉起臉盆去敲,咔嚓一陣,冰裂水出,咕咕上冒,冷氣四溢。盛了水,端起臉盆往回走,走出幾百米,感到手有些痛,想歇一歇,緩緩彎腰,臉盆放到地上了,手卻粘在臉盆沿上動不了。心生惶恐,不知道將要發生什么,身體怪異地扭曲著,臉都快挨著水面了,蹲也不是,坐也不是,站立也吃力。
嘯——嘯——
好熟悉的聲音。
艱難地仰起脖子,真的是雄鷹,同唐古拉山的雄鷹一模一樣,碩大,敏捷,翅膀展開足有半張竹席大小。雄鷹由遠及近,頭頂暗了下來,撲棱棱,嘩啦啦。再抬頭,塵土迷了眼睛,想要去揉,手還粘在臉盆上,同時感到被用力拉拽,向上拎起。
他驚得彈跳起來,彈起更多塵土,臉盆“咣當”落地,在礫石上轉圈,清水潑出,飛起水珠連連。轉眼間,雄鷹飛去,飛得搖搖欲墜,怪模怪樣。
傻傻地望著雄鷹飛去的方向,不由得想起老白,如果他在身旁,會教給他高原生存技能,不至于被雄鷹吃掉或抓到天上。
看看雙手,手掌好好的,只是有些紅,揉搓一陣,麻木減弱。臉盆旁有一根拇指般粗細的羽毛,顏色呈褐色,其間夾雜著黑色細紋,羽毛上粘著些微冰渣。捏了捏乳白色羽骨,有些堅硬。臉盆倒扣在礫石上,水跡所到處,逐漸轉化成冰晶,細細微微,輕輕薄薄。
他樂了起來,雄鷹沒有吃掉他,叼走他,反倒被冰水粘掉了一根羽毛,怪不得飛翔的時候歪歪斜斜,隨時都有掉下來的危險。
這一次,只端回小半盆水,走一走,歇一歇,搓搓手,哈口氣,回到房間,水面竟然沒有結冰。小心翼翼地給班公柳澆了幾捧水,剩余部分,過幾天再澆。
第二天起床,盆里一滴水都沒有,就像從來不曾盛過水一樣。東張西望一番,也沒找出原因,或許哪個學生趁他不注意洗臉了呢。
自從房間多了一株班公柳,進進出出的老師學生更多了,大家站在小樹前,喜笑顏開,跳來跳去,他對大家說,只許看,不準摸。有人大概聽懂了,恭恭敬敬地圍觀。一個男孩伸手拽下一片柳葉,急得他只能吼叫,不好意思驅趕。男孩做著鬼臉,跑了出去。目光追逐中,發現那男孩不是別人,正是掏他口琴的小家伙,也是第一個學會漢語歌詞的小家伙。男孩后面,立即跟了一串孩子,時不時發出呼叫聲,歐珠,久美,歐珠久美。
樓衛東總算記住了男孩的名字,歐珠久美。
既然學生喜歡樹木,就上一節植物普及課,每個班輪流上,恰好有一篇課文,便領學生朗誦,他領誦一句,學生跟著念一句。
——我們村里種了許多果樹。現在是春天,滿樹都是花,桃花,蘋果花,海棠花,我們村是花園。到了秋天,樹上結滿果子,我們村就成了果園……
剛領誦了兩遍,歐珠久美忽地站起來,問道:格根啦,花,什么是花,桃花是什么?
問完以后,歐珠久美依舊站著,哄堂大笑過后,更多的聲音接踵而至:格根啦,果樹是什么?秋天是什么?……
樓衛東愣住了,背靠黑板,站了許久。
他覺得累,前所未有的累。無奈,原來這般可怕,如此無堅不摧,直擊心房。嬉笑聲瞬間退去,消失得有些怪異,四周一片寂靜,連喘息咳嗽的聲音都不曾出現。
透過小小的窗戶望去,黃豆般大小的冰雹從天而降,窸窣飄搖,撲朔迷離。
猛地,想起班公柳,風一般旋出教室,還沒進到房間,就看見扎西校長正立在柳樹旁,一手掀起藏袍,一手提著褲子,尿腥味異常濃烈。
看見樓衛東進來,便哈哈大笑,并說:施肥,施肥。
愕然過后,樓衛東說了聲謝謝。再看那枝條,一片葉子都沒有了,鐵桶里沒有落葉,地上也不見葉片,張了張嘴,最終沒有罵出聲。
定了定神,心想,河里結冰了,天上下冰雹了,該是落葉的時候了,花開一季,草木一秋,是自然規律,即便是遙遠的江南水鄉,這個季節,梓樹楠樹也會落葉,候鳥也會飛往嶺南更溫暖的地方。
扎西離開以后,樓衛東四處搜尋了好一陣,才在窗戶縫隙間發現了一片柳葉,撫弄了許久,夾在筆記本里。心想再次見到柳樹發芽,起碼得到明年春天,或者開山以后,那個時候王副縣長就回來了,還會帶頂帽子給他呢。
想一想,就輕松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