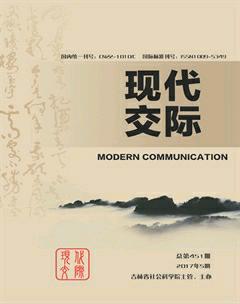從《紫色》中譯本看翻譯中的性別身份
劉學(xué)思
摘要: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擁有多重身份和角色,而無論他是讀者、作者還是創(chuàng)造者、研究者,始終離不開他的性別身份,這里不僅僅指生理性別,也包括社會性別。本文通過對美國黑人女作家艾麗斯·沃克《紫色》的兩個譯本,來分析性別身份在翻譯中的作用和影響。
關(guān)鍵詞:性別身份 《紫色》 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5-0090-02
隨著20世紀(jì)9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學(xué)者們著力于對語言層面背后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一些因素進(jìn)行研究,翻譯研究也從語言文字層面提升到了文化、歷史、哲學(xué)、政治等層面。根茨勒(Edwin Gentzler)認(rèn)為,翻譯與身份的研究是翻譯研究的新方向(2008)。國內(nèi)學(xué)者也對“身份”研究引起重視,王東風(fēng)認(rèn)為“身份問題是當(dāng)今翻譯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語言身份、文化身份、階級身份、社會身份、性別身份、年齡身份、民族身份、殖民地身份、霸權(quán)身份,只要涉及跨語跨文化交際,這些身份就會以不同的方式現(xiàn)身于翻譯之中”。
一、翻譯中的性別身份
“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最初是一個醫(yī)學(xué)名稱,用于向大眾解釋性別重置手術(shù)的本質(zhì)。社會學(xué)理論中性別學(xué)研究認(rèn)為人的社會性別身份具有流動性,性別身份可以與生理性別相符,也可能不符,有時還會出現(xiàn)“雙性同體”(androgyny),即人是擁有雙性意識,或者說用雙性視角來看問題。譯者的性別身份可以說是譯者身份在性別層面的體現(xiàn)。
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擁有多重身份。“譯者的身份應(yīng)是多重的,他既是讀者、作者,同時又是創(chuàng)造者、研究者。”(田德蓓,2000:20)在翻譯的不同階段,要做到性別中立都不容易。作為讀者,譯者從自身性別出發(fā),同時帶著原作者的性別去欣賞理解原作。作為作者,尤其是在翻譯女性主義作品時,譯者需要拋開自我的性別身份,以原作者的性別身份將原作內(nèi)容和形式以目的語表現(xiàn)出來。作為創(chuàng)造者,譯者不是簡單地將兩種文字進(jìn)行轉(zhuǎn)換,其中還包含了自己的再創(chuàng)造,而在創(chuàng)造過程中,譯者要拋開與原作者的性別差異,盡可能地與原作者融為一體,尤其是翻譯性別色彩較濃的作品時,要注意自己的性別身份。作為研究者,譯者不僅要研究原作語言,同時也要研究其創(chuàng)造背景、社會文化以及原作者的性別身份。總的來說,無論在翻譯的哪個階段、哪個方面,性別身份都會發(fā)揮不同的作用,從而對翻譯帶來不同的影響。譯者的性別身份可以說是譯者身份在性別層面的體現(xiàn),也可以說是譯者各種身份中的一部分。
二、女性主義作品《紫色》與中文兩譯本
《紫色》是美國黑人女作家艾麗斯·沃克于1982年創(chuàng)作的書信體小說,描寫中下層黑人女性的覺醒之旅。而20世紀(jì)80年代在經(jīng)歷了兩次女性主義浪潮之后,多元文化凸現(xiàn),這時的女性主義批評肯定了男女差異,側(cè)重“身份批評”,把種族、性別和文化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正是《紫色》的創(chuàng)作背景。女性主義特色無疑是這部作品的亮點(diǎn)和特色,并為其贏得了美國文學(xué)最重要的獎項(xiàng)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全國書評家協(xié)會獎。
無獨(dú)有偶,《紫色》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中文譯本分別是由女性譯者陶潔和男性譯者楊仁敬所譯。兩位不同性別的譯者在對女性作家的女性主義作品又有哪些不同的解讀和翻譯呢?
例1:He beat me today cause he say I winked at a boy in church.I may have got something in my eye but I didn't wink.I don't even look at men.
陶譯:他今天揍了我,因?yàn)樗f我在教堂里對一個男孩拋媚眼。當(dāng)時我的眼睛也許進(jìn)了東西,但我沒有拋媚眼。我從來不去瞧那些男人。
楊譯:他今天打我,因?yàn)樗f我在教堂跟一個男人眉來眼去。我也許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可我并沒眉來眼去的。我連男人都不敢看一眼。
本例中兩位譯者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處理。首先beat一詞,女性譯者陶潔選擇了“揍”這個詞,而男性譯者楊仁敬用的是“打”,顯然“揍”比“打”更猛烈,更能反映he(此處指繼父)對女性主人公“我”施暴,以及主人公所遭受的苦難和折磨。所以從beat一詞的翻譯可以看出,女性譯者陶潔似乎對女性主人公的經(jīng)歷更能感同身受,在理解和翻譯時,更能準(zhǔn)備地把握性別身份。另外一句I don't even look at men.陶潔翻成“我從來不去瞧那些男人”,體現(xiàn)了女性的桀驁不馴,而楊仁敬翻成“我連男人都不敢看一眼”,則體現(xiàn)的是女性的膽小怕事。從上下文來看,此時的女主人公并未覺醒,只是默默地接受現(xiàn)狀,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帝求助,男尊女卑的思想還是深深烙印在她心里,所以楊譯雖然在某種程度中貶低了女性的地位,但是生動地還原了女主人公此時的心情。
例2:It took him the whole spring,from March to June,to make up his mind to take me.
陶譯:他拖了整整一個春天的時間,從三月一直拖到六月,最后才下決心要我。
楊譯:從三月到六月,他花了整個春天,才下決心娶我。
原文中him指女主人公茜麗的丈夫某某先生,他最初想要娶茜麗漂亮的妹妹耐蒂。陶譯“拖了整整一個春天”“從三月一直拖到六月”,連續(xù)兩個“拖”字加強(qiáng)了原作中拖延的意味,再現(xiàn)了原文中某某先生不愿意娶茜麗,而茜麗又為了保護(hù)妹妹耐蒂,以至她希望某某先生能夠盡快娶她的心理狀態(tài)。而楊仁敬忽視了主人公的思想狀況,只將原作直接譯成 “花了整個春天”“從三月到六月”絲毫不能體現(xiàn)某某先生的拖延和茜麗的焦急之情。另外,原文的take me也耐人尋味,雖然是結(jié)婚,但原作者并未使用marry一詞,而是take,因?yàn)樵谥魅斯琨愃幍臅r代,男性和女性地位極度不平等,而是一種征服、支配以及壓迫的狀態(tài),所以他們的結(jié)合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結(jié)婚,女性譯者陶潔注意到原文這一細(xì)節(jié),所以翻成“要我”,而楊譯的“娶我”則將男女地位平等化,并不符合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 在這一點(diǎn)上女性作家和男性譯者看起來有些距離,而女性譯者陶潔更好地再現(xiàn)了作者的立場和觀點(diǎn)。
三、結(jié)語
通過對比陶潔和楊仁敬的譯作,譯者的性別身份無一例外地凸顯出來。尤其是在翻譯女性主義作品《紫色》過程中,由于性別色彩較濃,女性譯者在性別身份上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更能貼近原作。性別差異、性別角色給原作打上了性別標(biāo)簽,那么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性別差異而來的性別身份無疑會給譯作打上不同的性別標(biāo)簽。在翻譯性別色彩較濃的作品時,性別角色性要被翻譯到什么程度?性別身份在翻譯中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在翻譯女性主義作
品時,男性譯者和女性譯者又該如何恰當(dāng)?shù)剡\(yùn)用自己的性別身份?對性別身份的研究還有待深入,但它無疑給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xiàn):
[1]Gentzler,E.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2]艾麗斯·沃克.紫顏色[M].陶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3]艾麗斯·沃克.紫色[M].楊仁敬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
[4]劉軍平.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中的中西話語[J].中國翻譯,2004(4).
[5]馬悅,穆雷.譯者性別身份流動性: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新視角[J].解放軍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10(11).
[6]穆雷.翻譯研究中的性別視角[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8.
[7]田德蓓.論譯者的身份[J].中國翻譯,2000(6):20-24.
[8]王東風(fēng).翻譯與身份——兼評董樂山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J].中國翻譯,2014(5).
責(zé)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