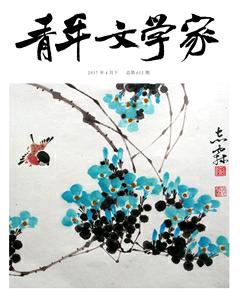心靈煎熬中品味生命的孤獨(dú)
摘 要:白先勇的小說總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于人物的心靈之中,表達(dá)對(duì)生命的感受而人物的感受也就是作家自身感受的藝術(shù)再造。白先勇多次提到過,“之所以寫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的痛苦轉(zhuǎn)化成文字。”[1]持續(xù)表現(xiàn)生命個(gè)體的消極思想似乎已經(jīng)成為了白先勇創(chuàng)作的思維慣性,他的關(guān)注范圍總是聚焦在人物心靈的痛苦上,這樣的創(chuàng)作宗旨在白先勇小說創(chuàng)作伊始,就已經(jīng)有所顯現(xiàn)。本文主要圍繞白先勇的第一部作品集《寂寞的十七歲》探討對(duì)孤獨(dú)的感受。
關(guān)鍵詞:整合的方式;人物心靈;孤獨(dú)
作者簡介:趙佳玫,女,漢族,遼寧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7)-12-0-02
白先勇的第一部作品集《寂寞的十七歲》以《芝加哥之死》作為分界線,在此之前作品中的人物,白先勇專注于對(duì)他們封閉精神世界的呈現(xiàn)和精神孤獨(dú)。他們的孤獨(dú)感主要源自身心的病態(tài)。一是生理的病態(tài),如《我們看菊花去》里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被家人隔離,被送往精神病院獨(dú)自生活。小說中的姐姐形象是白先勇以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白先明為原型塑造的。他回憶道,“有時(shí)整天在外,忙到深夜才返家,家里人多已安息,全屋黯然,但往往只有明姐還未入寢,她一個(gè)人坐在房中,孤燈獨(dú)坐。”[2]二是心理的病態(tài)所造成的孤獨(dú)。在前期作品《那晚的月光》與《黑虹》中,可以看到主人公遭遇理想挫折,精神無所寄托而感到孤獨(dú)的表象,作品中的人物對(duì)現(xiàn)實(shí)毫無眷戀,感到極度厭惡。畢業(yè)在即的李飛云將心中的困惑茫然都希望借助記憶中那晚美麗的月光消除,可是卻發(fā)現(xiàn)是徒勞的。色衰愛弛,物是人非,青春年少僅存的浪漫被生活的重壓消磨殆盡。已為人母的耿素棠執(zhí)著于初戀留下的純真,曾經(jīng)那份感情與現(xiàn)實(shí)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耿素棠最后孤獨(dú)地抱著對(duì)初戀的懷念,在水潭永遠(yuǎn)的黑暗里抓住了彩虹最后的光芒。在這些作品中,他們都具有叛逆,自我的性格特征,常常思想與現(xiàn)實(shí)脫節(jié)。他們的孤獨(dú)感主要源自輕微的自戀病態(tài)心理傾向,這是一種在自卑、自憐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自我依戀。具有自戀心態(tài)的人由于愛惜自己,達(dá)到病態(tài)的程度,無法與外界更好地締結(jié)人際關(guān)系,很容易陷入孤獨(dú)之中,自戀與孤獨(dú),經(jīng)常如影隨形地伴隨在一起。李飛云自認(rèn)為滿腹才學(xué),應(yīng)該有更好的前景,盡管妻子在家中待產(chǎn),他卻不愿意承擔(dān)家庭責(zé)任和義務(wù),是他只愛自己,自私自利的表現(xiàn)。耿素棠自認(rèn)為應(yīng)該要有更加優(yōu)越浪漫的生活,她并不享受家庭,吵鬧的孩子,乏味的丈夫,令她對(duì)沉悶卑瑣的現(xiàn)實(shí)厭倦至極。他們傾向于極端的自我專注。這種為我獨(dú)尊的狹隘心理致使他們面對(duì)瑣碎平淡的生活時(shí),只愿意一味逃避現(xiàn)實(shí),沉迷在理想的虛幻中自我陶醉。他們沒有撕毀現(xiàn)實(shí)與理想差距的力量,只能一廂情愿地編織著情與美,企盼著與幻想中的夢(mèng)境對(duì)話。白先勇本身也是一個(gè)完美主義者,這些人物對(duì)美好理想的追求,也有白先勇本人思想的投影,是自我表現(xiàn)的區(qū)間。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時(shí),白先勇尚未經(jīng)歷人生的挫折,尚在年輕氣盛的時(shí)期,完美主義與青年時(shí)代特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結(jié)使他塑造出了這樣一批孤獨(dú)者形象。
白先勇到美國之后,繼《芝加哥之死》,他相繼發(fā)表了《寂寞的十七歲》、《香港一九六O》等作品。寂寞荒涼的生活日常中潛伏著楊云峰乖張的熱情,隨時(shí)都可能像巖漿決口一樣噴發(fā)出來。在末世般香港的郁熱浮躁里流動(dòng)著余麗卿內(nèi)心絕望的死寂。這些人同樣是孤獨(dú)的,但是與白先勇旅美之前塑造的自我封閉的孤獨(dú)形象略有不同。他們心靈的痛苦往往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接軌,孤獨(dú)感形成的社會(huì)因素成為了白先勇作品中一個(gè)更加值得思考的現(xiàn)象。
《寂寞的十七歲》中,盡管楊云峰自敘的語氣平靜得近乎淡漠,但是他制造自己給自己寫信、打電話佯裝有人關(guān)心的假象,用一種病態(tài)的堅(jiān)持執(zhí)拗地與冷漠的世界作出對(duì)抗。一味關(guān)注學(xué)習(xí)成績而忽視了子女心靈成長的父母與學(xué)習(xí)成績不佳卻心理成熟的楊云峰,雙方之間的立場構(gòu)成了錯(cuò)位,冰冷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彌散在楊云峰的成長環(huán)境中。關(guān)愛的落空致使楊云峰倍感孤獨(dú)而與家庭漸行漸遠(yuǎn)。在學(xué)校里,對(duì)唯一給予他關(guān)懷的同學(xué)魏伯飏產(chǎn)生糾纏式的依賴,因不堪忍受同學(xué)之間的言論而放棄。對(duì)于唐愛麗虛情假意的示好還以真誠的回報(bào)。最終得到的卻只是對(duì)方肆意的譏笑和輕浮的玩弄。與生俱來的敏感和孤僻是楊云峰被孤立的根源,而后天成長環(huán)境中家庭與社會(huì)關(guān)愛的雙向缺失成為了這種孤獨(dú)感的催化劑。愈是被忽視嘲笑,愈是恐懼逃避,愈是產(chǎn)生孤獨(dú)感,楊云峰就在這樣閃避游離的惡性循環(huán)里苦苦掙扎。在臺(tái)北新公園一個(gè)陌生的男人那里獲得了短暫的庇護(hù)。反而使他內(nèi)心的孤獨(dú)感加劇膨脹,這里同性戀傾向的隱晦表現(xiàn)似乎暗示著這種異端情感和社會(huì)的偏見也是導(dǎo)致楊云峰孤獨(dú)的原因之一。最終他絕望地喊著,“你不曉得我的內(nèi)心的悲哀有多深。”[3]因?yàn)樗冀K都是無處安放的孤獨(dú)靈魂。“在《寂寞的十七歲》中,白先勇對(duì)楊云峰情感世界的呈現(xiàn),揭示了白先勇對(duì)產(chǎn)生楊云峰這種情感寂寞和墮落行為的社會(huì)根源的思考。《寂寞的十七歲》是白先勇第一次正面地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對(duì)邊緣少年的內(nèi)心世界進(jìn)行挖掘和剖白。” [4]
白先勇曾經(jīng)在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在香港生活過兩年,他對(duì)香港并不陌生。1960年的香港,聚集了大量的移民,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和惡劣的自然條件等等,使當(dāng)時(shí)的香港整個(gè)陷入一片混亂,遭受著種種危機(jī)。人類在天災(zāi)面前聽天由命,更加速了自然環(huán)境的惡化。《香港一九六O》使用了意識(shí)流手法,余麗卿紛亂的意識(shí)在妹妹云卿的哀求和毒品罪犯的無賴言論和自己混沌的思想中不停地變換,焦灼郁熱的情緒使得港民已經(jīng)伴隨著整個(gè)香港島而疲軟,個(gè)體嚴(yán)酷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與絕望頹廢的生存情緒與整個(gè)香港聯(lián)系在了一起,余麗卿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使被拋式的孤獨(dú)危機(jī)擴(kuò)大到了每一個(gè)角落。而余麗卿的內(nèi)心已經(jīng)空虛麻木,甘愿選擇沉淪,最終屈從了毒品罪犯的話,任由孤獨(dú)的靈魂在毒品和情欲的深淵里繼續(xù)墮落。這個(gè)階段小說里人物的孤獨(dú)感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外部世界的遭遇和他們內(nèi)心之間的對(duì)峙,人物的我行我素,自我封閉等性格因素已經(jīng)被弱化,與社會(huì)的割裂成為孤獨(dú)感的主要誘因。楊云峰缺乏家庭與社會(huì)的關(guān)愛,余麗卿在師長罹難之后只身流落到了香港,此時(shí)的香港因極度干旱缺水陷入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孤單無助的她只能選擇和吸食毒品的罪犯生活。此時(shí)的白先勇,已經(jīng)獨(dú)自在異國漂泊,歷經(jīng)家庭諸多變故,處在青春心理成熟時(shí)期,對(duì)自己異于他人的性取向有所察覺,曾經(jīng)在臺(tái)大學(xué)習(xí)期間受到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觀念影響等諸多原因促成了他自覺的危機(jī)意識(shí)和求存意識(shí),孤獨(dú)不再是個(gè)人的精神癥候,而是成為人類與社會(huì)背離處烙印的傷痕。但無論是哪一類的孤獨(dú)者,他們都有一個(gè)共同點(diǎn),盡管他們都曾經(jīng)為擺脫孤獨(dú)而努力掙扎,但是由于白先勇悲觀天性的作用,也似乎始終沒有看到光明的出路。
參考文獻(xiàn):
[1]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廣州:花城出版社 2000年 第544頁.
[2]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紀(jì)念三姐先明以及我們的童年》[A].《白先勇文集》第四卷 廣州:花城出版社 第48頁.
[3]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A].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
[4]王亞麗,《論白先勇小說中的少年意象》[J].華文文學(xué) 2009年.
[5]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