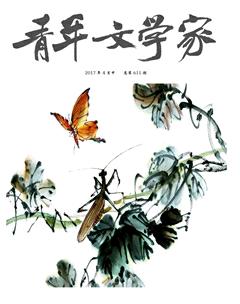生與死之隨想
作者簡介:康婧(1987-),女,漢族,河北石家莊人,碩士,河北醫科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助教,研究方向:對外漢語教學、語言學、文學、跨文化交際。
生與死,這是所有人都會面對的兩件事。人,哪一個不是由生到死。可是我之前并沒有覺得這是個讓人花時間思考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人總是求生的,有誰會甘愿求死。所以無論遇到什么事,什么樣的困難,人都應該好好活著。只有活著,才能去解決自己遇到的一切事情。但是直到最近,我自己為人母后,突然意識到我的父母漸漸在老去,真正靜下心來思考生與死的問題,我才發現,原來我一直在回避這個問題,并沒有認真思考過“死”。為何會這樣?因為我覺得,也許許多人也是這么覺得,“死”,似乎是一個遙遠的話題。
其實,“死”從來未遠離我的身邊,只是我一直沒有去認真思考過它。可能是因為我還年輕,離這個字還很遠;也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害怕而不愿去想。
忽然記起在我上小學的某一天夜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躺在床上突發奇想:要是人死了會怎樣?是不是就想晚上屋子熄了燈睡覺是那樣黑?是不適合閉上眼一樣看不到任何東西,即使是睜著眼也一樣無異?說來好笑,自己當時不知道為何會想到這些。結果則是結果則是一個十歲女童因太過恐懼而躲如父母懷中直至安眠。從此之后我便在沒有想過這件事。現在仔細想想,也許自己當初太過早熟,讓自己沉入思考海洋,卻忘記了自己的智慧不足,不可能將這個令多少名家大師頭痛的問題琢磨出一個頭緒。不過,正因為這次的思考,讓我不愿再去觸及“死”這個東西。我產生了怕的感覺,我怕自己沉入那漫天的黑暗之中,再也無法重見天日了。
或許是種巧合吧,這件事過了一年多之后,十一歲的我就親眼目睹了死亡。我是我第一次真正經歷親人的離去,而且是自己一直照顧的老人,僅僅分別兩天未見,再次見面卻已天人永隔。老人就是媽媽的奶奶——我的姥姥(在老家,只要是比自己大出兩輩的人,無論男女,都要叫此稱謂)。姥姥患上了淋巴癌,從確診到離世僅僅六個月。這六個月,姥姥住在我家養病,讓我經歷了她人生的最后階段,也讓我面對了一個人由生到死的真實過程。或許姥姥舍不得讓我親眼見她離開人世的場面,也或許不忍讓媽媽也經歷那痛苦的時刻,所以她選擇在我們都不在場的時候離開。直到我見到她的遺容時,我的心反而由悲戚中升起了一種平靜之感。當時的我一滴淚也未流出眼眶,媽媽問我,我答說我哭不出來。現在想想,可能自己覺得姥姥受的苦已經不少了,也許死亡對她來說是最好的解脫吧,我為她感到了一絲欣慰。那次之后,我忽然覺得“死”并不是那么可怕了。因為我覺得,人之死既然令人覺得可怕,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時候“死”也或許是種欣慰,那么對于“死”的擔心是不是就可以扔掉了呢?
其實在我經歷的那六個月里,我也體會到了“生”帶給我的一些感受。姥姥的一輩子在那六個月里濃縮成了她對我訴說的一個個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親眼所見,讓我總結出了一個事實:姥姥的這一生有得有樂,充實且沒有后悔,她做了一切她想做的事,沒有遺憾。而媽媽在姥姥過世后說的一番話,亦讓我感受頗多。媽媽說,她對老人盡孝不會等到老人入土后,年年去墳上燒紙盡孝,而是在老人生前盡其所能,讓老人滿足她的愿望,讓其踏踏實實的離去,不留一絲遺憾。這些事令我心潮涌動。“生”對我來說應該就是踏踏實實過好自己的日子,不妄自菲薄,不留給自己一絲遺憾。而最重要的就是要珍惜“生”,勿輕言“死”。
雖然人人都會走到“死”這一終點上,但是若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是絕對要不得的。不可否認,天災會奪人性命,我們不可逆轉;但許多事故多為人禍所致,而人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除去這些及因病或因年齡過大走到終點的,無論是何問題纏身,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是要不得的。我總是覺得,這樣的人真的很傻,難道他們不知道只有活著才能看到前方朝陽,死了則只剩滿目黑暗及家人悲痛之淚,而問題卻仍在那里未曾消減一分一毫。我有時真想問問那些人,你可會后悔?不過沒有回答會到我的耳中,這只是我一廂情愿罷了。
在我看來,過好自己“生”的每一天,珍惜它,充實它,享受它,這樣無論“死”在哪一天來接我,我都不會覺得怕了,因為我過得很好。當然了,如果能平安到老,沒有天災人禍讓我提前走到終點,那就更好了。誰不怕“死”,但是只要看透它所具有的必定性質,那么就在它到來之前,讓自己的“生”充滿光彩。永遠不要輕易放棄“生”,它所帶給人的東西會讓人更能了解“死”之意義。“生”與“死”就和“光”與“暗”般如影隨形,互相依托。只要我過好“生”就如同讓“光”保持明亮耀眼,當“死”帶來“暗”時,我會迎上前去,欣然接受。因為我已經經歷了那“生”的光亮,是時候去體會“死”的黑暗了。縱使仍有不舍,但我“生”的光亮不會被這即將到來的“死”之黑暗完全淹沒至毫無點點亮,它會留在懷念我的人心中。
很喜歡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都走在長長的路上。路有無數的分支岔道,亦充滿了無數的未知。說不上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的哪一時哪一分哪一秒,和我們同行的人,甚至是我們自己都會走上另一條路,離開我們熟識的一切。當這件事發生時,可能他人已做好準備,也可能沒有,但都不會妨礙我們去看另一條路的風景。我們或許會獨自旅行一段時間,因為之前走的那條路是那樣充實熱鬧,是時候自己平靜地四處走走了。但我們不會永遠這樣,因為,總有一天,我們會和他們重逢在同一條路上。我們,總有和他們重逢的一天。(選自海藍《最佳女配角》)